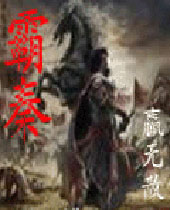霸秦-第1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哪知申不害却是不卑不亢,直言答道:“正是!申不害空有一身本事,却苦无施展之地,识君有鸿鹄之志,方才来西秦谋不世之功业。”
无敌却是不动声色道:“先生心急了?”
申不害正色道:“若申某所料不差,君上颁布简兵令,意在实行变法。只是不知君上所行变法,将以何人之策为本?”
卫鞅也见机道:“申兄所言,正是卫鞅所思。”
见申不害点出问题核心。无敌自然也不能再给两人打马虎眼,当即微笑不语上前两不。跟随在无底身后地白雪等人一见便知无敌有话想要单独对申不害和卫鞅两人说,便会意避走。
“二位先生皆心有鸿鹄之志,本公怎能不知。”无敌默默整理好思路,本来此次待他们来咸阳也是准备向他们摊牌,只不过时机却是被两人给拿去,眼下形势有些被动而已。不过无敌却是胸有成竹,对于这两个牛逼人物的安排早就谋划好了:“申兄精于吏治,而卫兄精于法治。以本公之见。两位先生所出之策都不是当政强国、变法强秦的长策。因此,本公将要实行的变法。既不用申兄之策,也不会用卫兄之策。”
申不害一听当即面色巨变,而卫鞅却是淡然一笑道:“敢问君上,既不用我与申兄之策,君上将要以何策变法强秦?”
听着卫鞅口中语气,无敌反问:“卫兄有策,申兄亦有策,本公可否有策?”
申不害当即一脸讥讽道:“君上之意,是要独力变法?既如此,申某留秦何用?”
申不害言下之意,不外是尽管你嬴无敌牛逼,可你始终都是一个屠户出身的半瓶水,怎么能和他这样的人对比。既然你要自己变法,用不上咱,我申不害留下也没意义了。
“申兄、卫兄,本公有一问,望二位先生恳答之!”无敌知道一旦摊牌,以两人地脾性一定会闹着要走,自然早就准备好了说辞:“个人功名利禄与天下黎民福祉,何为贵?何为轻?”
昔日稷下学宫论战,申不害自然记忆犹新,当即正色答道:“当然是以天下黎民福祉为贵,个人功名利禄为轻。”
至于卫鞅,自然也不可能对此回答抱有反对意见。
“好!申兄既然识得何为贵何为轻,本公不妨对二位直言。二位若是愿意留在秦国出仕,本公必将根据两位所长,委以重任,让两位一展抱负。若二位只是一意孤行想要施展心中所谓长策,谋高位食厚禄,以个人功名利禄为重,将天下黎民福祉弃之脑后,则本公也不便勉强,是去是留,悉随尊便!”
第一【第170章】 廉政公署
大秦嬴无敌二年四月
此时,位于咸阳城外的宗山半腰上,一场关系着大秦国运的大戏正在火爆上演。
对于无敌来说,不论是卫鞅还是申不害,都不是他心中合适的主持变法人选,即便是背黑锅,无敌也觉得没有必要让两人来为他背上这个有可能流芳万古的骂名。因此,对于这两个在原本的历史轨迹当中牛逼得一塌糊涂的任务,只能是量才而用,绝不能将之放在可以左右变法核心位置碍手碍脚。
无敌的一番激将之语,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毕竟这两人都是有着高傲的人格境界,如不能将之折服,一旦放他们走脱怎么说也是大秦的损失不是。
听了无敌的说辞,申不害的面色自然十分难看,无敌话中之意无疑是说:留下,便是为天下黎民的福祉;离开,就是贪图个人的功名利禄。
当即申不害狡辩道:“申某岂是贪图功名利禄之辈?”言毕申不害大袖一甩,就要作势欲走。也在这时,卫鞅却是不怒反笑,面露笑意的一把拉住他道:“申兄且慢!”
而后卫鞅将目光投向无敌,淡然道:“敢问君上,若卫鞅和申兄愿意仕秦,不知君上以何职受之?”
看卫鞅的表现,无敌知道激将计已被他看破,当即也不再拖沓,直言道:“卫兄长于法治,本公将要律法司之上组建大秦最高法院。此院直属国君,专司审理、核定、鉴别、补充、增修我大秦律法,卫兄以为如何?”
“大秦最高法院?”卫鞅听这新奇名词,立时会过意来:“既是最高,应有别院。”
无敌答道:“我大秦各县,日后都将设县属法院,县令主管县内政务,不再兼顾司法审判之职。但凡各类案件将由县属法院初审。所得裁定将由最高法院核定,如案件是有蹊跷,最高法院可驳回重审,或由高院做出最终审判。且高院还需审核各地案件,去伪存真,务使冤假错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务求使我大秦律法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好。好一个公正、公平、公开。”不待卫鞅开口评价。申不害却是出言称赞道:“君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当正名而责实之。”
无敌却是笑道:“申兄长于吏治。则本公将在大秦最高法院之侧。建大秦廉政公署。此署亦直属国君。专司核查我大秦官吏是否贪墨、谋私、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私相授受。并且拥有秘密侦测官吏行为举止。调查取证之权。廉政公署与最高法院不分伯仲高下。互不统属。实乃左膀右臂。”
哪知申不害听闻之后。却是没头一皱道:“名为廉政……实为督吏。君上不怕官吏心有戚然么?”
以申不害眼界。自然看出这是一个从明至暗。有系统监督官员地机构。以春秋战国时代地政治哲学而言。君若用臣。便不能疑臣。也就是疑而不用。用而不疑这一套。并且。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做官地人。没有不以权谋私和私相授受地。只是大家都很客气。将这个程度控制在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程度。
战国时代地官吏俸禄是很少地。而官吏本身也不靠着那点俸禄吃饭。多是依靠封地地各种租赋。便说上大夫甘龙一年地俸禄便才有粟米百担。可上次栎阳之围他便一气献出了相当于他十年俸禄地千担粮食作为军粮。由此可见。若是让申不害去监察这些官吏。让他们不能用手中地权利搞点外快。还不叫他们饿死。
哪知却是无敌笑答道:“官若不廉。便是狗官。政若不廉。便是苛政。国若苛政。民不聊生。国若廉政。安居乐业。本公自然知道其中道理。因此我大秦将要实行高薪养廉制度。”
哪知卫鞅却是反问道:“高薪或可养廉?”
无敌笑道:“若高薪当真可以养廉,要廉政公署何用?”
就无敌所知,后世的高薪养廉说法最初并不是由香港提出。
香港的公务员也确实实行高薪制度。因而许多人以为“高薪养廉”是海外传到香港的舶来品。实际上这一政策并非出于海外。而恰恰源出于我们中国。从18世纪初直到20世纪初,满清政府对官员一直实行“高薪养廉”的制度。只是高薪并未收到“养廉”的效果。
从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起,为了纠治官场腐败,雍正皇帝决定给官员们发放巨额地“养廉银”。在此之前,清代官员的俸禄不算很高。当时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年收入大约为10两银子。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约为76两银子,大约是普通劳动者的8倍。一个知府的俸禄约为18两银子,大约是普通劳动者的1倍。一个巡抚的俸禄约为256两银子,大约是普通劳动者的2倍,而一个总督地俸禄约为308两银子,大约是普通劳动者的3倍。
清政府给官员们发放的“养廉银”出自百姓征收地附加税,其数量高达官员们俸禄的10多倍至数十倍。同一品级的官员在不同地区将领取不同标准的“养廉银”,在这里仅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知县的“养廉银”分别为1000至1800银子,为俸禄的13倍至24倍;知府的“养廉银”是2000至3000两,为俸禄的11至15倍;巡抚的“养廉银”为12000两银子,为俸禄地47倍;两江总督的“养廉银”为18000两银子,是其俸禄的60倍。
满清政府实施了这巨额的高薪养廉的政策后,有没有起到预期的廉政效果。起初满清官员收到这笔巨额的“养廉银”时有些官员感激涕零,还表示要除去日常开支后,“养廉银”若有节余,可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不过没有多久,官员们视“养廉银”为理所当然的收入。他们贪心未改,又在原来的附加税外再加收各种税,并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灰色收入。
依据见存地资料对各地官员的灰色收入进行估算,可知在1世纪平均一个知县每年地灰色收入约为3万两银子。是“养廉银”的20倍;一个知府的灰色收入约为525万两银子,也是“养廉银”的20倍;一个总督或巡抚的灰色收入约为18万两银子,是“养廉银”的10至15倍。由于当时地官员们几乎都有这样地灰色收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只要不在这基础上再收刮民脂民膏,当时则不称之贪官。于是民间有流传至今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这表明当时一个知府在三年间敛财10万两银子。仍算是个“清廉”的官员,而当时一个知府地俸禄和“养廉银”还不足1万两银子。
所以,无敌知道单单高薪养廉是绝对不可行,还需要廉贞公署作为狗头铡在侧虎视眈眈。
以卫鞅和申不害两人的智慧当然不需要无敌将什么都说明白,仅仅是点到为止便已经让两人大为叹服这个高薪养廉和廉政公署的绝配。当即申不害二话不说,一振衣衫,一个长揖拜下,表示自己愿意出仕。而卫鞅却是不为所动,眼珠一转。开口再道:“敢问君上,秦国将用何种律法治之。”
卫鞅的问题,无敌也是准备了许久。根据无敌的记忆。卫鞅地施政纲领主要归结为四个字,那便是:“专制集权”。
在后世所编录的《商君书》中,“壹”,是被反复讨论的命题。其提出“壹”地概念,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立意将整个社会控制在来自上方的专制的权力之下。《赏刑篇》曰:“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又曰:“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言篇》云:“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是为其证。
“壹”,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思想的统一,再者就是政令的统一。理论言谈统一于上,不得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必导致盲目服从于君主,《战法篇》即曰:“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又曰:“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思想的高度统一,正是为维护君主地权威服务的。《靳令篇》曰:“利出一孔者,其国无乱。”《弱民篇》曰:“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守一则治。”《农战篇》曰:“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又曰:“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以战者。民不勇。”《壹言篇》曰:“治国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
在这种强调上下一致的思路下,必然形成专制、威权的政治结构。《算地篇》曰:“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修权篇》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算地篇》曰:“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壹言篇》又云:“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所以,君主所有的举措,都是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考虑;而百姓的兴作,也不得不依违于其间。《君臣篇》曰:“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
第一【第171章】 亘古之变
正因为无敌知道卫鞅的理政思维是以专制集权为主,独裁愚民为辅,因此在用其担任最高法院长任职上当然有所深入思量。
当即,无敌道:“我大秦既然变法,在富民强国之路上虽要循序渐进,但在律法方面却跳出六国定势。因此,本公决意废除我大秦惯来之肉刑律法,日后我大秦将只有鞭刑、杖刑、劳役、死刑。”
卫鞅不耻下问道:“既要废除肉刑,鞭杖之刑岂能不着肉乎?”
无敌笑道:“鞭刑用于民,杖刑用于军,是以小惩大诫也!而百姓犯法,除叛乱、谋反、叛国、通敌、戮亲诸罪之外,一律以劳役刑之。”
无敌话中的意思就说日后秦国的律法只有三个档次,轻微犯罪将施以鞭挞杖责,中等犯罪将会判罚劳役,而严重的犯罪才会判处死刑。而不是依序秦国和山东六国的刑法以名目繁多的各种肉刑作为惩处标准。战国时代,刑罚的名目正因为诸如卫鞅、申不害以及李悝这种名士而层出不穷,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卫鞅在秦国搞出了凿额、抽胁、镬烹等多种花样。据《前汉记》记载:“秦用商鞅。起连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为凿额抽胁镬烹之刑。而法禁等酷矣。”
凿额既是用石匠常用的凿子从额头上凿下,犯人立死无疑。抽胁则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取下犯人的数条肋骨,运气好的或可苟活,运气差的不久便会因为感染而亡。至于镬烹便是架起大锅将人活活煮死,且肉、汤还让民众分食,那是相当强大。而所谓的连坐制度,既一户犯法,十户连坐,若其罪当斩首,便十户同斩。若其罪该砍手、斩足,便也是十户同刑,结果到最后他自己在逃难的时候因为商户畏惧连坐,被拒之门外,惹出了遗臭万年的“作法自毙”之典故,最后被嬴渠梁的儿子用他列为秦国正式刑罚的“车裂”执行死刑。五马分尸而死。
当即,卫鞅听闻无敌之言,竟是出题考校道:“试论,某甲与某乙因琐事私斗,某甲失手将其杀害,当如何判罚?”
卫鞅出这道题目地意思就是你既然说百姓犯法,除叛乱、谋反、叛国、通敌、戮亲这几项罪名可以判处死刑,其他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