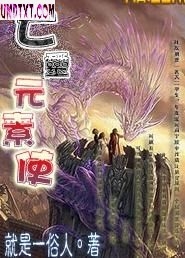以爱为名_素熙-第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多少人?一个或是两个?”
Ricky摇了摇头,“很多个,我也记不得了。”
艾庭露出一副“早就知道是这样”的表情,光是这样也看得聿律一把火,整个辩护席仿佛都烧起来了。
“这些和你发生过性关系的人,你都还有和他们联络?”
“有的有,有的没有,大多数都没有。”
“你是否确知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和身分?”
“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大多数都不知道,因为大都只是一夜情。”
“到底有多少是知道的?”艾庭问。
Ricky犹豫了一下,“……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那么那个人有感染过任何性病吗?”
“怎么可能!”聿律再一次拍桌了,这回三个法官都惊吓得往辩护席这边看,聿律要收手已经来不及了。老法官还开口问他,“辩护人,请问有任何意见吗?”聿律觉得自己脸烫得都要烧起来了。
“不,我很确定他没有。”Ricky接口答道。
“除了他之外,你并不知道其他人身上,究竟有没有感染任何疾病了?”
“异议!”
聿律再次拍桌了,“检察官不当设计问题,既然是假设证人不知道,证人又怎么会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问句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谬误,证人怎么可能回答得出来?”
聿律看纪岚用指腹压住唇,似乎笑了一声。艾庭则终于受不了了,“这个问题只是前一个问题的延伸,和问证人知不知道那些人姓名和身分是一样的问句。”
“不一样!每个人都会有姓名和身分,这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姓名和身分的人,因此询问证人‘你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吗?’是可行的,就像问一个人你今天吃饭了没一样。”
聿律珠连炮似地说著。
“但是否染病是另一回事,这世上并非每个人都会感染性病,这世界上存在染病和没染病的人,因此证人的性伴侣们染病与否都是个问题,对未染病的人而言,询问证人‘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否染病?’并没有任何意义。检察官这样问,只会让人产生与证人性交的人好像都染有性病那样的错觉,是很卑劣的文字游戏,任何逻辑清楚一点的人都应该发现得到才对。”
艾庭怔在那里,连Ricky都转过头来,看向聿律的眼神满是诧异与复杂。
他听见席上的张法官抿唇笑了一声,温和而不失诙谐地开口了, “辩护人说的没错,以逻辑来论的话。检察官,你愿意修改一下问题吗?”
艾庭瞪著聿律的脸,好像第一次认识他这个人一样。只是聿律还处在‘你敢欺负我家小孩我就要你好看!’的情绪中,对艾庭的瞪视丝毫不觉压迫,反而有样学样地瞪了回去。
“你对你的性交对象,大多数都一无所知。”
艾庭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改口,气势整个馁下去,“这样说对吧?”
Ricky这回点下了头,眼神有些愧咎,聿律发现他瞄了自己一眼。
“……是的。”
聿律听见旁听席上又嘈杂起来,隐约还有讪笑的声音,要不是对旁听席不能异议,聿律真想把这些嘲笑Ricky的人通通盖布袋赶出去。
“既然你对这段期间的性交对象全部一无所知。”
艾庭似乎总算抓回一点讯问的节奏,他逼到了证人席前,“你又怎么能确定你的病,一定是那个叫陆行的男人感染给你的?”
“异议!”
聿律又一次举起了手,这回连纪岚都看向他。“检察官不当胁迫证人!”
“我哪里胁迫他了?”艾庭似乎终于受不了,转过头来骴牙咧嘴地问。
聿律不客气地回敬,“你身高是他的两倍、年纪是他的四倍,又靠那么近,还用这种口气问证人问题,再加上你的脸!证人不被你闷死都被你吓死。”
“什么叫再加上我的脸?我的脸本来就是这样子!”艾庭终于也火了。
“那也是你的问题,你没看证人吓得脸色都苍白了,这不是胁迫是什么?”
艾庭瞪圆了眼,席上的两个陪席似乎都在憋笑,只有老法官不动如山。聿律本来期待他说一句‘异议驳回,检察官的脸并非他所能掌控,不能让他为自己的脸负责。’之类的。但艾庭也不再等法官裁决,他走回检方席,一掌压在了桌上。
“总而言之。”
艾庭脸上明显写满了“不爽”两个字,他用手一撩额发。
“这位证人的性交对象并非单一,按照证人刚才的证述,他也无法一一确认那些人是不是感染性病。爱滋的空窗期可能从三个月到十年都有可能,目前的筛检技术也无法精确到知道哪年哪月哪日遭到感染,证人也自承是一个月前才确认感染情事。”
他加重声调,“由此推论,证人根本不可能确定是谁将病毒传染给他,更遑论指控那位叫陆行的人是以刻意传染疾病为目的而犯下本案,这根本是无迹之谈。”
纪岚似乎开口想讲什么,但聿律先他而走出辩护席,一口气走到法庭中央。
“爱滋的感染率并没有外界想像得那么高,只要有安全的防护措施,即使伴侣的一方遭到感染,另一方也可能安然无虞。以证人的性交习惯,他一定都会提醒对方使用保险套,唯一不会用保险套的就是他的前男友,所以不是他传染给他的是谁?”
“为什么辩护人会知道证人一定会提醒对方使用保险套?”艾庭挑眉。
“因为……”聿律一下子词穷下来,但他怎么都不愿意输在这种地方,“你又怎么知道他一定不会使用保险套?就说你预设立场你还不信,不然你问问证人!”
“两位,请冷静一下。”张法官终于出言制止,聿律看她脸色十分微妙。
“……我能够确定。”
这时证人席上却忽然传来细弱的嗓音。聿律和艾庭都回过头去,Ricky不知何时抬起了头,左手抓著右手,眼神坚定地望著法官席。
“我……我就是可以确定,我知道就是他传染给我的。”
Ricky又重覆了一次,仿佛要坚定自己的想法。
“很难用说的说出来,但这是一种……感觉。比如有一次,那个人在床上要求我吻他,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接吻过,那是他的规矩,他说真正相爱的情人之间才接吻,不接吻是为了我好,以免彼此以后沉溺太深,分开的时候也麻烦。”
聿律听著,刚才盛怒的情绪一下子消气下来,觉得自己心脏被戳了个洞,像气球一样咻地一声飞到了体外。
“但那天他很反常,他问我:Ricky,我可以吻你吗?一次就好。我那时候觉得奇怪,但也没有特别反对,我想我那时候是有点喜欢他吧,就让他亲了一下。他吻完之后就忽然问我:你觉得我恶心吗,Ricky?”
“那时我以为他是在问吻的感觉,就回答他:怎么会呢?感觉很好啊。毕竟是在床上,我不可能会说太煞风景的话。然后他又问我: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你都不会觉得我恶心吗?我那时候已经觉得很怪了,但我还来不及多问什么,他就主动放开我睡了。”
Ricky深深吸了口气,法庭里再次鸦雀无声。
“其实我也懂那种感觉,知道自己被感染之后,我曾经有一度非常不甘心。我痛恨那个传染给我的人、痛恨这个世界,甚至痛恨每一个健健康康活著的人。”
Ricky忽然转过头,聿律怔了下,Ricky的眼神像是在看远方,但聿律却知道他这番话传达的对象。
“我一度也像那个叫陆行的人一样,想要把病再传染给第二个人,传染给一个……曾经很照顾我的人,这种想法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觉得自己很可怕,但当下真的无法放弃这样的念头,像是著魔一样。”
“与其说是希望拉一个人当垫背,不如说是害怕吧!我很害怕,白天的时候还能够笑著谈论这件事,但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看著筛检报告,会忽然恐惧到不知如何是好,那种浑身都坏掉了、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死去的恐惧感。”
他低下头,“而比这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喜欢过自己的人……对自己会有什么想法的揣测。”
Ricky单手抱住了臂。
“想知道对方的想法、想确认对方的感觉……为此明知道不可以,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接近对方、试探对方。我还是可以被爱的人吗?我还是被爱著吗?……明知道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还是会不停地想证明这件事。”
Ricky的话声回荡在法庭里。聿律立在辩护席前,只觉得法庭的地板一瞬间从脚底下消失了,而他正在往下坠落,摸不到底也看不著光。直到证人席上的Ricky再次吸了口气,聿律才蓦然回到法庭上。
“所以如果问我为什么知道,我只能跟你说,我就是知道。因为我和那个人,曾经是一模一样的人。”
法庭上的气氛停留在诡谲的沉默中,Ricky说完这番话就低下了头,没有再做任何陈述。
中间的老法官转向了艾庭,“检察官还有问题要询问这位证人吗?”
聿律看艾庭站在检方席上,好像开口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撇了下唇。聿律总觉得艾庭脸上有一丝难以读取的落寞。
“没有其他问题了。”艾庭难得低调地说:“谢谢庭上。”
Ricky在法警陪同下走回证人准备室,聿律目送他的背影好一会儿,但Ricky全然没有回过头来看他,迳自消失在门的那一端。
聿律只得走回辩护席上坐了下来,刚才法庭上残留的亢奋感还留在身体里,他见纪岚朝他凑过来。
“真不愧是前辈,太精彩了。”他用感慨至极的声音说,表情有些复杂。
聿律还有点飘飘的,说实在刚才那十分钟讲那一串话,几乎都是在脑袋一热的状态下说的,具体来讲他和艾庭说了些什么,聿律现在竟回想不太起来。
总之他的少年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至少不是哭著离去的。
那样就好了,聿律多少就感到安心了。
“就算证明被告的同事确实曾有这样恶劣的行迳,又怎么样?”
艾庭从检方席上站了起来,取代Ricky走到房间中央。
“辩方该不会忘记了吧?也容我提醒一下庭上,本案和被害男童唯一有交集的人,就只有被告而已,监视录影器显示案发的那个时段,只有他们二人同时待在厕所里。而被害人身上沾有的精液,也清楚地验出被告的DNA型别,这两点是不可动摇的。”
他哼了一声,“至于陆行,除了辩方提出那些不充分的证据外,和那个男童的交集点几乎是零,辩方至今无法证明他们曾经碰过面、有过接触,案发的厕所也没有留下任何陆行到过的痕迹,更遑论证明这个人就是本案的凶手。”
纪岚开口像要说些什么,但艾庭抢在他之前打断了。
“还有一点。”他定定地说,“本次依照现场的案发状况,凶手性侵害男童,是属于一次性的、而且是出于某种冲动,临时起意的性质相当浓厚。”
艾庭严厉地说著。
“这和辩方试图证明的,那种以感染疾病为目的,计画性的、需要长期铺陈才有办法成立的犯罪,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就算陆行这个人真有辩方所说的那种恶劣行迳,那也仅止于过去对那些少年,在本案情况完全不适用。如果辩方不能有效说明这一点,刚才一切也都只是空谈罢了。”
法庭上安静下来,几个法官在低声讨论著。聿律看纪岚从辩护席上站了起来,慎重地理了理西装衣领。
“检察官在这个案子最开始的时候,曾经叙述了一个故事,并以那个故事做为检方起诉被告有罪的基础。”
纪岚一如往常,礼貌而优雅地分别点头致意。经过包扎和休息,聿律听纪岚的声调稳定许多。
“因此在这里,敬爱的庭上,在检视了如此多证据之后,辩方想提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纪岚说著拿起了投影摇控器,把安置在法庭角落的萤幕重新打开,那间聿律看过许多次、造成这一连串事件的厕所出现在众人眼前。
“本案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间西栋二楼厕所里头发生,而厕所是密闭空间,这间厕所又鬼使神差地没什么人使用。因此在欠缺有力的目击证人、被害人本身又无法作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所有的一切,赌在厕所门口那唯一的眼睛,也就是检方提出的那架监视录影机上。而这也成为本案最大的盲点。”
“所以辩方,现在想试著跳脱这只眼睛的束缚,让我们从另外一双眼睛、另一个角度,重新检视一下这个事件。”
他缓缓说著,艾庭不满地哼了声,但终究没有插口。纪岚便用说故事一般的语气开口了。
“事情发生在今年的七月十五日星期三,小学正值暑假,因为事故不幸坐上轮椅的吴太太,带著中午提早放学的男孩,一起到青年活动中心参加扶轮社活动。”
“吴太太是妇女扶轮社的主办人,事务十分繁忙,男孩到了活动中心之后,就自行带著跳绳,到他平常熟悉的二楼中庭平台去练习。”
纪岚的声音温和而富有磁性,法庭上多数人都安静下来,静静地听著纪岚的描述。
“就在同一天的上午,本案的被告叶常,以及和他感情很好的同事陆行,两人负责周三上午的值勤,陆行是因为本来就是周三上班,而叶常则是因为想和陆行同天值班,所以刻意和原本负责当天周三上午的李芾换班。”
“到了中午十二点,叶常和陆行两人结束值班,两个人吃了饭、聊过天之后,陆行就向叶常表示该走了,从警卫室离开。”
“而仿佛命运一般,午后二点左右,天空降起了令所有人毫无防备的大雨。”
聿律一怔,同样的话,艾庭在最初陈述起诉内容时也说过。只是现在,仿佛电影切换场景,同一场雨,电影的男主角却换人了。
“陆行之所以离开警卫室,是因为他每天中午固定会去中庭巡逻,这点从他的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