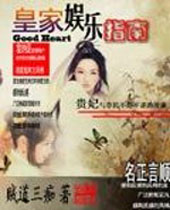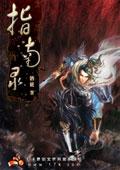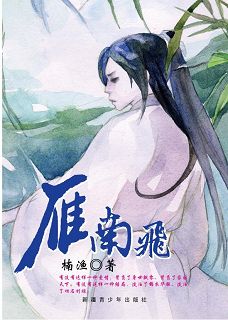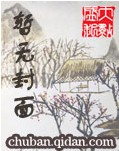闻道_南山孟姜-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闻道》作者:南山孟姜
文案
是谁说过,中华这几千年的历史,就像一辆滚滚前行的马车,坎坷多于平坦,来到伴随离去,有人操纵方向,有人守卫四壁,有人安居中央,还有人将这一把肌骨填付沟壑,垫起继续前行的路途。
他已经老了,忘记了很多事情,但终究还记得,他在找一个人,找了大半辈子,大半个中华。他想那人最后应该是明白了,他们保护着那些弱者,而那些弱者也在坚强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与文化的根。
他看见天边最亮的星消匿在夜幕中,他知道那是太白:昏名长庚,晓曰启明。他突然想起了一切。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么也的确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长庚已经落下,而启明,终究要在黎明前升起。
★ 本文为架空设定,人物、地点、事件均属虚构 ★
纯剧情非典型谍战文 | 全文完结 | 外太空故事请勿对号入座 | 欢迎勾搭欢迎提意见
内容标签: 民国旧影 制服情缘 业界精英
搜索关键字:主角:赵启明、赵长庚 ┃ 配角:老板、陈勖、冈村贤之助、北井茂三、老生、田中留吉 ┃ 其它:谍战、史学、民国
首发链接:http://jjwxc。/onebook。php?novelid=2703918
始篇
第1章 〇 楔子
赵长庚活了很久,久的哪怕下一瞬即刻离去,也会觉得够本了。
他生在两千多年来最后一个帝国老死之日,那一年,中华历史中第一个名义上的新政府在長河下游宣布成立。彼时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尚未开始,夷狄船炮环伺着这片古老的大地,本土传统与西方新学碰撞,知识分子与贩夫走卒毗邻,有志者疾于国难,投机者蝇营狗苟,庸贱者得过且过,社会在剧烈地激荡交会,一个时代漫长的阵痛已经初现端倪。
后来人慑于它的动荡,惊于它的遽变,感于它的气质与落魄,用太多或褒或贬的词汇来形容它。但于当事人而言,又哪有那么多新奇可言,富贵也好,贫贱也罢,谁还不是挣着一口气、一条命。有人活下来,更多的人死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膏润了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是谁说过,中华这几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一辆滚滚前行的马车,坎坷多于平坦,来到伴随离去,有人操纵方向,有人守卫四壁,有人安居中央,还有人将这一把肌骨填付沟壑,垫起继续前行的路途。
赵长庚已经记不得他从哪里听到这句话了。他经过炮火连天的年月,见过普天同庆的欢乐,走过手足相残的争斗,趟过愚昧懦弱的狂潮……他曾迎来新的政权,也曾送走旧的世纪。他从不是什么高尚或者伟大的人,他只是一直活着,快要成为一段百年来的活历史。岁月消磨了他的躯壳与精力,一点点蚕食且剥离着他的记忆。他忘记了很多事情,当他鬓发生白的孙儿们、带着学生的学生们来看他时,他颤巍巍地拍着那些同样褶皱的手背,却屡屡无法从脑海里搜索出丝毫相应的痕迹。
可他还记得一件事:他在找一个人,找了大半辈子,大半个中华。其实他心里早已不奢望还能见到那人,只想着哪怕远远听个消息,知道他是生是死、老于何处、息于何地,也总归是好的。然而都没有。寻找,成为这漫长光阴中的一个念想,甚至于他已经不记得那个人的相貌,也不记得那个曾经就挂在嘴边的名字。他只记得,他在找一个人,有生之年,他不能再放弃那个血脉相连的亲人。
那是近八十年的分离呵,超过许多人终其一生的长度。
赵长庚很老了,当他盖着毛毯仰在躺椅上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出神。就像此刻,他正将涣散的目光长久投向窗外一片苍茫,夜幕已经落下,有一颗极亮的星在西天升起。赵长庚很久没有看见这么晴朗的夜空,他望着那仅次于月光的明星,渐渐就挪不开眼了。有破碎的片段渐次从记忆深处浮现,他突然颤抖着手向周身摸索,一遍又一遍,终于在上衣靠近心脏的兜里摸到一个坚硬的圆形物件。
那是一个老式怀表,表壳被养护得光可鉴人,却横着一条触目惊心的弹痕。表早在十年前就停止走动,它经历过无数次修修补补,直到附近最后一家修表铺关门,再没人愿意花费时间在这些复杂的擒纵装置上,于是这老朽的物件也慢慢在时光里僵死。
赵长庚还记得,那一天,总计六百余万字的《中华通史述论稿》交付印刷,大家都说,赵先生五十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了,可只有他知道,到底是谁的执念尘埃落定。怀表背面有两个字,昏花的眼神已经看不清那阴刻的痕迹,但松弛的皮肤还是将触感忠实地传回大脑。表背上用小篆刻着,启明。
就是那颗星啊!赵长庚浑浊已久的双目一瞬间闪出光亮。《诗》小雅·大东篇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毛传注曰:“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
他想起那个人叫什么了:启明,赵启明。
正篇
第2章 Ⅰ 长庚第一
中华二十七年,三月,上珧。
清明初过,天气已然暖和起来。路上行人渐多,连四处拉活的黄包车也比往日添了几成。四个月前,东日军队攻破江头门户津口,年底又连下常化、临兴,直抵姑州,距离此地亦不过五百里。相较隔着报纸都嗅得到的炮火味,这早春里的上珧城,着实宁静得有些不像话了。
其实上至名流绅士,下至巷口乞儿,谁人不知,旧都去年就挂上了东日的膏药旗,新政府接连几场会战惨败,无力抵挡敌军破竹之势,早迁去了川内渝阳。学院礼堂上唐明皇西逃的剧本排了又排,已让人看得腻歪。沿江驻守的军队里倒还有些血性汉子,可敌人照样拿下了江口枢纽,连周边几座新城也没放过。所幸上珧虽是沿江显眼的城市,却以学术文化见称,一时得以苟安。只是这偷来的安逸,也不知能留到几时。
街头有报童高喊着号外跑过,一路上颇引来几个长衫马褂亦或西装革履的闲人注目,心道这时事动荡里又是哪一座城市在炮火下沦陷了。年前常化失守,听闻已死了几十万人;紧接着临兴一夜之间陷落,许多人闭眼时还是青天白日,再开门就换了弹丸膏药。自那以后,各色报刊号外频出,连带着忙煞一干记者编辑。
这种惊心动魄的消息听得多了,民众大多也麻木起来,只要打不到自家门口,能得一天安逸都算赚的。何况临江市镇中,但凡胆子小点儿又有条件的,早随着年初一波外逃风潮跑远了。如今尚留在城里这些,除了驻军和留守政府人员,便多是北边南下或东边西走滞留下来的行客,以及底层苦于营生、奔逃无门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真要到了枪炮砸进来的时候,谁还能比谁好上多少?
街头邮局拐角转出一辆搭灰油布顶棚的黄包车。车里坐着个穿西装戴礼帽的中年男子,锃亮的皮包横搁在腿上,打眼一看便知这十有八/九是某个厂子被资产拖住的企业家。前头拉车的是个一身短打的黑脸后生,车拉得倒是老道,步子不大,又快又稳,却不是朝向交通局或者西场区,而是一路奔上珧第二国立大学去了。
上珧的公立私立大学总共十九所,去年已有三所于假期召回学生,举校搬往南申,另有津口、常化迁出过路的八/九所院校,连同本地装箱待运的校资,一并积压在铁道中转处,颇有些人心惶惶的架势。学校这面忙着转移,偏生这些受西方新学影响的学生们却不领情,一腔冲动的热情无处发泄,硬是在年底津口会战期间,自发集会抗议政府溃逃,呼喊着要参军抗敌、保家卫国。
闹得凶时,当地警察局也抓了几十个牵头的学生,可又不好真怎么地,关了两天便陆续释放出来。正赶上前方损失惨重,上面又下令安抚学生,现成的人力不用白不用,地方索性组织了一批专业相关的志愿生,送去前线,真要能留下帮忙更好,吓破胆的请早打发回去,跟着内迁院校撤离,也省得再闹腾。
如今上珧本地院校多半已着手外迁,余下的除了教会大学和零星几所私立学校,只有第二国立大学还如常开课。不过也有消息称该校一概物资具完成装运,随时准备撤走。倒是其所属医学院还在东面沦陷区里照常招生,引来不少揣测。只是这乱世里的消息,真假参半,一时半刻也无人说得清楚了。
西装男人在距离院区一街之隔的金梁桥边下了车。桥边有报童叫卖已经不再及时的早报,男人买下最后一份报纸,挑着大字标题看了两眼,便卷在手里,绕过院墙走入学校。许是赶着上课时间,校园里行人不多,偶尔几个抱着书本、身穿学生服的年轻面孔,也仅是在周匝柳树新抽出的嫩条间一晃,便匆匆往教学楼赶去。
楼间小树林里倒是聚了三五堆晨读的学生,兼有着长袍马褂的老先生彼此看书闲聊。西装男人打眼望去,目光落于稍远离人群处一位穿青灰长衫、挂金边眼镜的年轻教师身上,只见他坐在临近花圃的长椅一端,手里拿本日文手抄的「財閥経済」看着,末几页里夹有一张国语报纸,露出半拉《国民日报》的题头。
西装男人低下头,似百无聊赖般地略瞅了瞅自己在阳光下拉长的影子,然后慢步踱到长椅边,站稳身,冲长衫男子打个文明礼:“赵先生别来无恙?”长衫男子此刻方才抬眼,不动声色地就势将露出一角的报纸夹回书里,起身客气道:“劳您惦记,一切安好。李老板百忙之下前来,是厂里运转有些情况?”
自前朝被迫开埠起,国内资本家投资创办的新式工厂就逐渐在沿江兴盛起来,只是苦于缺乏相应理论知识,在行业里颇为吃亏。于是一些眼光长远的创办者便自发去附近经济院校听课,甚至竞相聘请教授学者作为顾问,一度成为风尚。起初校园里的学生们还当个新鲜,后来见得多了也就熟视无睹,多一眼都懒得去瞧。
西装男人颇为自觉地在长椅另一侧坐下,目光从眼角往四周一扫,却压低声音,调转话头:“喜蛛死了。”长衫男子眼皮一抬,没有做声,只听那边继续说道,“城外林区发现的,服毒,身上有刑讯痕迹。”喜蛛是代号名称,其人原为津常一带的情报科长,三个多月前突然失去联系。站里于是紧急将星君从其在津口的卧底环境下调出,启用在上珧国大挂名的第二套身份,接替喜蛛工作,甄别并联络其线上人员,确保津常情报网络正常运转。同时其撤离前的工作由新期特训班代号纸鸢的情报员接替。
“是老生出手了。”长衫男子说着,不动声色地皱眉,“二区各组联络正常,我撤出前做过鉴别,喜蛛应该没有变节——早知如此,我就不该走。”眼下前方战事吃紧,督统局好容易在沦陷区楔下三十一颗钉子,陆续传出敌军内部消息,这才让几乎被打蒙了头的军方稍稍有些准备。星君本是当中一条线上的联络组长,如今骤然换人,免不得耗费时间重新磨合——这倒还是小事——只怕期间误了消息,亦或出了岔子,就不知明里暗里要赔进多少人了。
西装男子侧目失笑:“怎么,你这二道贩子还做上瘾了?”说罢见那头没有反应,又跟上一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津口都搞什么营生,没点儿大好处那北井中佐能巴巴跟一日侨报社的‘小さい記者’称兄道弟?”
他的日语并不标准,音节生硬含混,一听就是口音极重的外乡人。长衫男子嘴角一抽,似生生忍下揶揄的话语,片刻方道:“东日大营都是些人精,一个不仔细,自己死了事儿小,平白连累旁人。别说他一七期学员了,谁去我都不放心!何况照这架势,上珧也撑不了两天,就我这身份早晚还是个麻烦事!”
“应星啊,你跟我也六七年了吧,脾气一点儿没改。这话也就在我跟前儿说说算了,要叫人传出去,看不先把你发回渝川定个扰乱军心的罪名!”西装男子说着,见对方欲言又止,情知他未必听得进去,当下也不多给机会,径直吩咐道,“行了,别不识抬举,这些不是你该管的。我过来就一件事儿:你马上传信喜蛛的直接联络人,让他们做出回应,一旦发觉异常,即刻切断联系,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清理。”
长衫男子神情肃穆:“我知道。”稍稍停顿了一刻,又问道,“老生现在和纸鸢单线联系,那小子确定靠谱?”脚下柳条阴影软软地摇动了两下。那人声音随着微风,刚好送到耳边:“放心吧,他不是普通班混出来的,是我亲自挑着带的。”
津常站当家代号老板,在担任站长前曾兼任督统局特训班教导,由他带出的前三期学员如今已遍布国内八大特别市,甚至不乏有人做到小站站长。只是这样的人物也仅仅带了三期便撒手走人,余下几任教导虽也小有建树,但相形之下到底乏善可陈,带出的人也自然不比起先出众。眼下他能为了一个学员再次出山,也的确是不容易了。
刹那间的念头闪过脑海,激得长衫男子眼皮一跳。而今战时,训练班的学期不会太长,通常都是半年班或季度班。后来人员消耗逐渐增大,上方也放宽要求,新收的学员往往只集中训练上三个月,便发往全国各站。纸鸢号称七期学员,入训时间绝不会早于津口会战前期,而那时,老板就在上珧,也参与协助当地警察局处理大学生集会抗议的风潮。
纸鸢的卧底身份是驻津口日侨报社的特约记者,专门负责对东日军队在华作战情况进行采访报道,所需的日语功底必然不是训练几个月可以达到的——这个人是谁,几乎呼之欲出!长衫男子振衣起身,眸中是许久未见的震惊与愤怒:“我只求过你这一次,我求你救他,不是让你把他往火坑里带!他还是个学生!”
西装男人端坐在长椅上,岿然不动:“这两批送去志愿支援前线的,哪个不是学生?你十九岁在我眼前宣的誓,我十六的时候都扛枪了。他今年二十,不小了。”柳条还在眼前摇晃,长衫男子不等他说完,已猝然打断道:“这不一样,我们是军人,他只是平民!”
“国难当头,凡我中华民众,皆有救国之义务。你也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