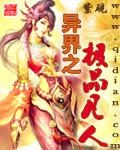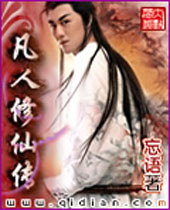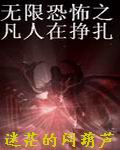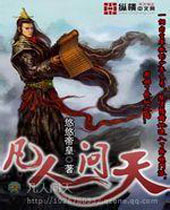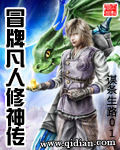凡人凡事-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没好气地拍了拍边想的花袄子衣襟说,“你也是,跟个女生逞凶斗狠的?要脸不要?输了赢了你都不光彩。而且真引来了老师,你真当这学校不抓早恋不叫家长?闹大了谁能讨着好处?”
他在一旁看得清楚,已经有人怕出事,跑去喊老师了,这事态要闹开来了,边想跟翁琳都不会多好看。都已经分手好几个月来,还因为早恋问题被喊家长,这话说出去能把人给笑到沟里去!
边想自然也知道这事自己办得难看,但那会他是真的烦她们。
背后指点什么他能眼不见为净,但不能他越不理她们就越觉得是他理亏啊!林海琼不分青红皂白冷嘲热讽他不止,居然连王志超也杠上,他能不发火吗?
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就非得是一方的错吗?是不是非得这样才能凸显出另一方的情操伟大奉献惊人?
他越想越委屈,想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死了,更可怜的是于锦乐居然还不替自己说话不安慰自己,这算什么事儿啊!
于锦乐三言两语把其他围观的人打发走,这才看到边想用一种像极了小白饿得狠了没食物吃的小可怜儿眼神巴巴地看着自己。
这人就是个花架子,性格看着挺好其实只是个表面,平常大事小事他不往心里去那就基本能一笑而过,偶尔会犯轴来那可是不管不顾。对他可千万别尝试无止境试探,这人底线有限,容忍度也绝对不高,容得了你一时那是他懒得追究,一再挑衅的话就是今天林海琼这个下场,真把他癫狂的一面直接给逼出来,不但发作,还带咬人。
他叹气,把袖子挽起来朝着边想嘴边一递。
边想瞪着横在自己眼前那截因包裹得严实度过了完整春冬而显得特别白皙的小臂,“干什么?”
于锦乐:“这不是给你送肉么?看你一副想生吃人肉的熊样。”
边想委屈巴巴,“有你这样安慰人的吗?”
连他都没发现自己现在的状态就相当于一只扒拉着粉爪撒娇着要亲亲要抱抱要举高高的小白。
于锦乐身为小白的半个主人,早对这种故作可怜的娇憨快要免疫了,简直懒得理他,利落地放下手:“不咬对吧?不咬那我收起了。”
“吃吃吃!我吃我吃!”
就在于锦乐刚把手收起来时,边想突然掐着兰花指扑了上去,那架势结合了充满了玄幻的娇羞与饿虎扑食的豪放,活生生让于锦乐又条件反射地举起拳头想一拳招呼上去。
后来边想偶尔回想起这一幕,都会和自己从沈家出来时的那种孤立无助结合对比起来,他想,如果那时于锦乐就站在楼门外头,逮着刚逞完凶斗完狠的混账自己来上一记爆栗把他敲醒,又或者是一顿冷嘲热讽也好,那至少他就不会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落寞了吧?
事情就这样有惊无险地揭过,虽然结束得略显突兀,但好歹没惹出什么意外来,只不过经过这次,边想跟翁琳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闹僵了。
或许两个当事人并未预料两人分手的事情会闹得如此沸沸扬扬,但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喜怒无常。愤怒与沉默对应了失望与疏离。或许翁琳不正面出面的本意在于利用舆论给边想施压造就罪恶感,却不料适得其反引来反弹,最后一直到她完成学校申请到出国前的那段时间,他俩就没再发生过交集。
文化节结束后不久就是期中考,所有人几乎是兵荒马乱地抱起了佛脚。
第38章 于锦乐其人
这学期结束之后面临高二,很快高三也在紧接其后,从李益华这个语文科任嘴里蹦出来的四舍五入论来说,他们已经约等于毕业班了。
一日不落的叨念了能化为实质,那股从隔了至少四层楼远的高三级渗出来的毕业班升学压力,在他们面前抽成千丝万缕的丝缕,开始与每个人的日后轨迹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
鮀中这种重点学校对学生危机意识的培养,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高一下学期刚过半,从一模开始,高三的紧张步调就开始带快了其他年级的节奏。
年级长兼政治科老师在讲台上语重心长,“同学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知识要靠积累,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抱得到的!”
底下的学生在数物化的理科奴役中早已疯魔,本就指望着这节用脑有限的文科课来休整休整,他们全部左耳进右耳出,智商集体下线,支棱着耳朵愣是没领悟出政治科知识要如何怎么积累,是每天对着课本背一遍还是天天追着年级长要练习卷做?
这种日复一日的无趣与时刻悬在头顶的高考压力推着他们踉跄前进。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学习之余他们,就是事业之余大人,在睁眼学习闭眼考试的纯学习年代,学习与高考所带来的压力之苦已经凌驾于人生其他各方各面。
三年高中苦短,人生悲喜举足若重,皆系于那纸轻飘飘的成绩单。
教育体系年年喊着改革减负,却从未能在真正意义上摆脱高考政策重压之下带来的成绩为重。
李益华每次班会课都会给所有人画一块大饼,描述那提熬过三年苦读最后高中魁首的光明人生,仿佛高考就是天雷滚滚的大劫,大家渡过了就能得道成仙一样。
他们就像一群拖着重重累赘的驴子,在眼前吊着的胡萝卜和身后鞭子的鞭挞下,咬紧牙关围着同一座石磨一圈圈永无止境地打转。
他们苦不堪言,却又无能为力。
当然,他们现在还无法预见未来。在很久以后,当他们都进了社会真正走上自己的人生轨迹,再次回首,才会蓦地惊觉:原来那看似压力千山重的高中时光,其实是他们少年时期最为珍贵的韶华。
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
五月份的时候于锦乐过了个莫名其妙的生日。
为什么说莫名其妙呢?这还得从期中考后边想被李益华传召接见去了办公室处理学生档案,在于锦乐的那一页上看到了他的生日日期说起。
于家小孩多,父母一来顾着店里生意忙,二来他们也不是什么文化人,对生日这种日子从没当做一回事过——连一碗面一个鸡蛋都没有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不重视。
但边想不一样,他家就他一个独子,生母虽去世得早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闺秀,他的生日自小被当做是家里的一大节日来过,也不是说要摆桌设宴地多张扬,就是在态度上的一个重视,习惯形成后就没那么容易改掉,他妈去世后,在沈昀佳还没出现的那段时间里,他爸不管再忙都会抽出时间陪他这个独子吃个饭,唠个嗑,跟个老领导似的总结一下过去的不足,再寄望一下未来。
所以当边想发现了于锦乐的生日还有那一两天的时间之后,就一脸神经兮兮地逼近他说,“请我吃什么?”
于锦乐一脸黑人问号,“什么请你吃什么?”
边想,“你生日啊,别告诉你跟我家一样都是自家人吃个饭没有请同学的习惯啊?”
于锦乐没有get到他的重点,“自家人吃饭一天三餐还吃不够?还非得分生日不生日?”
“不是,你不过生日的吗?我看你快生日了啊!五月十日嘛!”
于锦乐一脸无奈,“少爷,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生日过的啊,我不过生日子的。”
他当然是和见识过所谓的生日宴的——郑曼曼没出国之前,她的生日宴是于锦乐见过的最夸张的一类。她爸每年都在酒楼包下大厅摆上二十几桌,连同自己生意上的朋友和郑曼曼自己的同学朋友在内一次性请了个高朋满座。
然而在于家,别说不可能有这种规格的聚餐,他父母就连他生日是在哪一天都不会放心上。
平民凡家,尚且为了三餐奔波不止,那有精力去折腾这些?
“哇靠,你过得比我还糙嘛!”
于锦乐听得直翻白眼。
不过生日就糙?那多的是人糙了去了,他大少爷没见着而已!
越、临、杏三江顺着起伏和缓连绵不断的低矮山丘,蜿蜒曲折千里迢迢地穿越一整片历史悠远的古朴东南大地,一路呕心沥血地滋养了一方肥沃水土及一方别致人情,最后相会于鮀城这个位于东南沿海的海滨城市,奔涌入海。
这个城市不大,其优越的海港条件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成为国内第一批享有经济特权的城市之一,这里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自成一派的民俗风情,也有着蓬勃生机的商业王国和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渔业捕捞行当。
文艺与传统,商贸与行当,几分和谐中夹杂着几分突兀。有人说这个城市热情,也有人说这个城市排外,一个古老的小城,文化与新兴政策的矛盾无处不在。
于家是这个小城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男主外女主内式家庭。男主人在外打拼赚钱,女主人在家主持家当开枝散叶。他们有着当地人生生不息为了生活拼搏奋斗的坚持不懈,也有着连类似于计划生育这类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无视的传统封建。有人说外地女子远嫁而来,就意味着与封建残余家长制度的终身不可分割。
当然于家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个体户家庭,不可避免地打从骨子里刻画进了以上的条条种种。
开枝散叶开枝散叶,先“开”后“散”,正是因为这个理,于锦乐下面还有个弟弟和妹妹,虽然比起农村地区这不算什么,但在同龄一些已经受到政策限制的同学家中,他家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户。
于爸自小从农村出来打拼,从一穷二白的农村穷小子奋斗到如今也算是家有所成——虽然比上不足,但是能找到关系砸下几万块把自家儿子送进鮀中,也已是比一般无权无势的普通工薪家庭要好上几分了。
于妈妈虽然自小家境不错还是城里人,但是他们这一代深受□□影响,由于家里成份问题,初中就缀学下乡去了。
这种的家庭,对于一贯以来在学校读书成绩中上的大儿子,是必然抱着极大的期许的。
于爸爸生意辛苦,于妈妈看在眼底,对着自家大儿子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以后要好好读书当个坐办公室的,舒舒服服地坐着赚钱,可千万不要像他爸一样为了养家糊口起早摸黑灰头土脸忙出忙入三餐都顾不上。
当然他们的起点是为自家孩子好的——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这样想。
就像大部分国人家长一样,他们把期望都寄托在几个孩子身上,因为年幼年轻时读书受阻形成的残念怨念,造就了他们对文人对读书形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憧憬,这种憧憬促使他们进一步走上了□□家长的习惯之路:让自家孩子替自己完成儿时梦想。
但所受教育和眼界所限,他们对教育方法一知半解,又要为家里稍微上轨道的那盘小生意操心操劳,所能分配给家庭的时间实在不多,于是只能以自己匮乏的知识与有限的脑力去强行构造出一种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恰恰正是时下众多家庭信奉的“打击教育”方式。
由于这种“打击教育”具有惊人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常年存在于各式各样的家庭之中,由普及性引发了弊端的隐秘性,以致于他们都理所当然地把这一种教育方式归结于“自谦”与“激励”相结合的“理想方式”,甚至奉为教条,世代相传。
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种“打击教育”跟“棍棒教育”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一个从心理层面给予孩子打击,另一个从身体方面给予伤害。
于锦乐自小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打击与否定如影随形,必须时刻听从父母指挥——
听话了,表现得好,没有夸奖,最多就是一句淡淡的“不要骄傲”;表现不好,那一顿打骂是绝对少不了的。
不听话,得了好结果,那也就赚来一句“下次就没这个好运了”;结果不理想,那便是一顿冷嘲热讽与全盘否定。
“我们那么爱你,养你长大,供你读书,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就必须顺着我们的意愿来。”
父母以“对你好”为挟持,绑架了小孩儿尚且稚嫩的道德观。
以“为你好”、“怕你自满”为借口,分分钟都牢记着要摁着你、踩着你,生怕一个放松,就会成了“捧杀”。
自家的小孩必须贬低,有个操蛋的词管这叫“自谦”。
以他们的认知程度,最多只能把“打击教育”与“激发血性”和“体现家长威严”联系起来,却远不懂得“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各人性格差异,面对同一种状况会呈现出多样化的反应,或许真有人能适应这种打击教育带来的血性激发,但这人绝对不是于锦乐。
身为长子,他不善言辞,性子沉,善隐匿,极具韧性与犟性,宁可对着日记本一笔一划写下心情所得,也不轻易吐露自己的心声。
他乖巧、随和、懂事,心软不会拒绝人,打骨子里少了那股子爆发型的血性。如果任他再成长几年,这性子未尝不能朝着沉稳可靠的方向发展,但现如今他性格尚未完善、三观塑造并未完整,这种教育作用于这样一个心有千结思虑甚重的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就会形成一种实质性的重压与自卑。
有比较的地方就有自卑,尤其当这种比较呈现出一种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趋势的时候,自卑成了习惯,习惯压制久了,会衍生出一股发自内心的嫉妒与歹意,他当然知道这样不好,却无法自控,只能故作淡定地将自卑与歹意小心翼翼地藏匿于温吐的性子。
就像于妈妈经常会在他晚上学习后准备睡觉时指着对面某扇还亮着黄晕台灯的窗说:“看啊,对面那孩子还在看书,就你既不聪明还不努力,怎么能学得好?”
所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于锦乐恨死了对面那户不知名的人家那个“勤奋熬夜苦读”的孩子,却又在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忍不住自责自己恐怕是因为不像那人的勤勉才会如此差劲。
歹意与自责让他的性子愈发扭曲。
边想说他有点自卑,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好——这点是真的“慧眼如炬”。
他岂止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他是认定了自己天生废柴。
鮀中这个环境,学霸圈他挤不进,高知家庭他融不去,富家子群他更是隔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