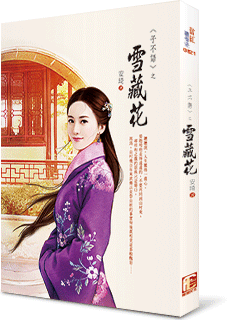子不语之雪藏花(子不语系列)-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回望住他,颔首。
于是他解开了她的腰带和层层束缚的厚重衣裳,当她蜜色的胸脯和腰肢毫无遮掩地呈现在他眼前时,他身下的yu/望便像脱了缰的马,再也无从控制。
一生难得一真心,一生的爱欲也由得自己求。
抚着那全身湿透趴卧在自己身上、气息与自己同步由喘息至平静的男子,鄂多海的唇微微扬起一抹微笑。
一直以来对人无欲无求甚至是无感的她,此时,竟是感到全然的幸福。
从没想过自己可与一名血肉之躯女子获得来自爱欲的欢愉,萨遥青沉沉睡去之后,竟作了个梦,他梦到自己与鄂多海携手坐看云起,直至两人皆白首。
只是,一个妖,怎会有类人的梦境?还白首?
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萨遥青是在一个傻笑中醒来;当他以为伸手就可以搂到鄂多海时,却没想到竟是捞了个空。
倏地,他惊坐起,在望了屋内一圈之后,并没有看见鄂多海,却发现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少了一些。
于是他急急穿好衣物,才提腿要出屋,可才跨了一两步,便又退了回来,他看住地上,不禁狂了。
再往上去不安全,你回去吧,别找我。
以前夜烧过的柴火余炭,鄂多海在地面上留下了简单字句;她怕是只身更往高山上去了,可他却睡死了,而她居然留下他!
像个心被抽走的人般,他冲出屋外;此时屋外竟是一反昨日的好天气,扑面迎来打在身上的,是狂暴的雨和雪。
水和雪交融,那刺骨的寒不消眨眼光景就透进人的身躯,令人难以动作,且寒气扰起了漫天白茫,虽然风大,仍是驱不散那阻人视线的雾气。
在这样的状况下,他无法去想象此刻的鄂多海是不是迷失在这茫茫无边际的雪山某一处,又或者是已经掉到深不见底的山谷里了。
他一点都不敢去想!
“鄂多海——”
对着层迭的高耸雪山,他使劲不断吼着她的名字,而那沉厚如虎啸的叫声,直直穿过数个山巅,去到了此时正陷在一处软雪里的鄂多海耳里。
“萨……”
因为那声音像是会反弹的箭矢,在层层山棱间回荡,令她无从找出他叫声的正确位置,只能随意仰头对住一个方向,聆听着。
他醒了,那个向来贪睡的男人。他……会回去吧?会吧?
仰着脸,却盛住了一脸落雪,鼻子吸进冰寒,她开始不住发着抖,最后不得已,她低下头,将所有感觉收在一个浅笑中,继续抬起那陷在恍若会吸住人腿的雪中的脚,一步一步,极费力气地往眼前那座也许翻过去就能看到吐蕃异地的白头高山走去。
时间就像被冰冻的流,在无尽头的雪暴里,看似变成了无意义,而在不知走了多久多远之后,她总算瞧见前头突出了一块没有覆雪的岩地。
已然像个精力透尽的偶人般,她动作僵硬地朝那块岩石走去;当她站到那块岩石上头时,这才感觉到自己像踏着了地,有了丁点的踏实感。
极目远望,她将头上的兽皮毛帽掩得更低,将身上的衣物拉得更紧,因为现下她连睫毛都因寒冷而结了许多小小冰珠,她思索着是否要继续前行,还是在这岩石上歇会儿等候风雪变小再继续。
就在她凝神之际,一阵不知从何处来的强大阵风忽地吹来,那强力风速就如同有人用力拉扯她一般,令疲惫的她脚下一软,人便跟着跌了去。
“啊——”
在坠落岩石之前,她幸运地攀住了岩石一角,待她努力定下惊慌,便开始挣动着脚下,想往上跃攀。
不过却在她一踩一踏之间,那原本看似平坦的雪地无预警崩了去,雪块急坠而下,在到达不可测的深度后立即崩散成雪末四处飞散。
原来下方不是块能走的地,而是悬崖!
第9章(2)
更新时间:2015…11…20 12:00:03 字数:5217
原就冻僵的手指使尽全力地攀附着突出的岩块,脚下毫无着力点,因此就算她努力晃动身子,极力寻找可以让自己回到岩上的机会,终究仍是徒然,渐渐地,她只觉身子里残存的力气一点点在流失。
然纵使气力在迅速流逝,她脑子里此时却像是被注入狂流似,极速飞掠过许许多多人事物的影像,她想起嬷嬷的面容,想起小豹子,还有……那与她在废屋里紧紧相拥度过寒夜的萨遥青。
眼看她就像一颗悬在岩上、随时会被风吹落的水珠,她脑海里不禁回旋起“难道就这样了?”的想法时,一只强而有力的臂膀忽地探出,稳稳抓住了她。
“别放!”是萨遥青。他抓住她的手臂,牢牢地。
往上仰望,她看住那张浓眉蹙起、满是胡髭的脸,就算前一刻害怕着即将面对死亡,可当望进那对眼眸,转眼间她心里的惧怕竟在瞬间消散无踪。
因为她知道他会救她。
有着无穷强劲力道的萨遥青一捞到她的手臂,即一个拉提将她整个人像拎小物般拉上悬崖。
待她踏上岩石,才下意识地吐了口气,却在下一瞬发觉一支连萨遥青都没警觉到的冰柱从两人所站之处正上方石壁上断裂掉落。
她反应迅速地将萨遥青一推,在他还弄不清楚状况的同时,那支比人腿还要粗的冰柱便极速掉落,从她背后穿刺而过。
“呕!”当她受重伤趴跌在岩石上,并呕出一大口血,那血没进白雪之中,转瞬冻成冰寒,犹如她将逝的生命。
“多海!”萨遥青立即将她抱离那仍可能会有冰柱砸落的位置,退了几步,迫不及待地检查她的伤势。
那根冰柱的锋利如刀斧,由她背后直直没入,虽未从前胸穿出,可胸前却已染红成一片,只是由于太过冰寒,刚流出的血瞬间冻结。
许是太冰寒之故,所以当鄂多海被冰柱伤及的那一刹是剧痛的,然也只是一瞬,她便再无感,只觉体内闷闷然,全身再使不出力气。
“我……会不会死?”这是她第一次知觉到自己有可能就此死去,因为以往受伤之后,并不会有这种魂不附体的感觉。
“别说话!”萨遥青颠着嗓音低嚷。
他为她拭去嘴角断续涌出的鲜血,四处寻找生路,只是,若一直维持着人形,他是万万不可能用极快速度将她带离这处险地的。绝无可能。
这是他自出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心急如焚,那就像是杀他放血一般,让他痛苦难当。
“可我……还想找瑟珠……回去救嬷嬷……”
“你别说话!”她每多说一句话便会耗去一分体力,他情愿她静默着保持生机。
“可我怕……没机会说了。我……真的喜欢你,想跟你在……一起……你呢?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是!我也喜欢你,想跟你在一起。”他毫不迟疑地说。
聆进他的话语,她染着血的唇边忽地漾开一抹微笑,纵使那一直望住他的双眸已缓缓闭上,但那笑却像冻着了似,始终挂在她苍白的脸上。
“多海,不能睡!”见她阖眼,他忍不住低吼,但她却已无响应,且她原就较常人缓慢的心跳,此时已不再跳动。
霎时,一股强烈的椎心刺痛猛击他的心,他知道再没时间犹豫,她的生命已悬在瞬息间。
“吼——”
他起身朝天高吼,而后感觉到一道爆发力量在转眼间窜至身体每一处,那令他浑身彷如重组,全身无一处不窜出深色的野兽披毛,四肢顷刻间伸出锐利兽爪。
紧接着,他原就结实的身躯往地上一卧,化作一头身型高大勇猛、肌肉纠结的猞猁兽,在将鄂多海驮上背之后,一个高跃,迅疾如风地朝不见边际的雪山奔去。
数日后,星家后院,某个厢房内。
被囚禁在同一厢房内的初音和鄂嬷嬷,虽然无法出得房门半步,可连日来因为有星霄的支持,在食物和日常起居上还不至于无以为继。
反倒是头上带伤、另外被拘禁的仲孙焚雁情况不明,那令一贯心情平实、纵使遇着大事也泰然的初音忧心不已。
“多海……”
当初音踱至房门边,附耳听着外头动静的同时,那半躺卧在厢房内床榻上的鄂嬷嬷微弱地喃了一句鄂多海的名。
初音回身看住老人,发现她手上拿着那只锦盒,锦盒半开,她凝视着盒内物,老脸皱成一团,须臾,竟见就算数日来被囚禁也不见愁容的她无声地流下泪水。
初音走回床榻边,落坐后,问:“担心她了?”她掏出帕子,为老人拭泪。
鄂嬷嬷点头,接着说:“这花……从没有这样过。”在走出石屋面对那一群噪动的村民之前,她唯一记得的,就是偷偷带着这锦盒。
这时她将锦盒整个敞开,里头那朵初音曾见过的花,已不见当时的生气盎然,而是似被冰冻过脱了水分、花瓣起了皱痕的半凋萎花朵。
“高山原,原覆雪,雪藏花,花似人,人病花枯,花谢人亡。”初音道。
“初音姑娘,您知道这花?”她虽不知道这花的名字,可这花却正如她所言,见花如见人。鄂嬷嬷讶然。
初音点头,跟着说:“当初我就是为了寻找生长雪藏花的秘境而来。那是个美丽的传说,可传说有时却是真有其事其境。雪藏花秘境,隐于这酷寒高原雪山之中,秘境里终年花开,暖水川流不息,生长在其中的兽禽,没有生命终止的疑虑,食花即活,饮水便能强健体魄,这对人而言无异永生。秘境一日,人间转眼三十年,人求之不可得,就算妖神异界之士也不一定能寻着。”
“您……”初音对雪藏花秘境的侃侃而谈,令鄂嬷嬷大开眼界,更再次证明了她的不俗。
“多海去过秘境,她会没事,而且她身边有萨公子。”
“遥青,他是妖,不是人。”
“嬷嬷,您知道?”其实她并不意外。
“他颈上的印记,和那雪里来的妖如出一辙。”她依稀想起五十多年前,那雪里来的妖。
“他是妖,可您却毫无所惧,还让他跟多海姑娘一起,应是看透了什么?”
“从前,我总以为妖物可怕,但后来才知道,人心比妖更可怕。初音姑娘,您要听我说个故事吗?”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她已知初音非如俗世人般浅薄,所以原本这个她想带进棺材里的往事,于今说出,想来初音应是会信。
初音噙着笑,颔首,鄂嬷嬷于是娓娓道来。
她说着:五十多年前,这山头亦发生了和如今相同的事情,村人没有任何原因便发狂病死,所以那在山里行之有年、以女祭山的说法,便又开始被执行。
当然,当时的村人是信之不疑,从未去怀疑会是有人从中作了手脚,为获利益而设下这样一个大骗局。
当时的她年方十八,虽然身怀六甲即将生产,却还是被当成了祭品送入供屋。会被送入供屋,多是因为当时她与一名来自汉地的教书先生有着情事,且未嫁娶即有孕。
原本她可以与孩子的生父一起逃的,可却被那从小即恋慕着她、她视如亲手足,却因她爱上了外人而由爱生恨的青梅竹马给背叛了。
他说他要助他们逃离,可却是将孩子的父亲先行诱骗囚禁,再将他弃至当时已经大雪纷飞的严寒深山之中。
一名书生,如何能在那样的荒山里存活?必死啊!
“青梅竹马,您是说星老爷?”初音问。
鄂嬷嬷点头。“我挺了个大肚子,他却说不介意,还说等孩子生下,便让渡给他人育养,他仍可娶我为妻,他爱我。可这种爱……我怎能接受?怎能?”说到此处,她微微哽咽。“我拒绝了,因而他眼睁睁看着我被送进供屋。”
在入供屋之前,他仅偷偷塞给了她一把剪子和干净的布料,那……算是最后的仁慈吗?她笑。
“可祭山之女,最终不都是被杀害?”初音思及那些含怨而终的女广魂魄。
“入了供屋的第三日,我生下了个娃儿。就在那天夜里,我见着了妖,真正的妖,可他却带走了我的孩子。”说话的同时,鄂嬷嬷凝注着眼前不明处,恍若那几十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什么妖?”
“不知。但他颈子上有着和遥青一样的印记,因而我知道遥青亦是妖。而我何以不惧怕妖鬼,全是因为在那事情发生后三十年的某个冬夜。”
她之所以被村人视为不祥妖女,且仅能远离村子独自居住,便是因为她理应被祭而亡,可她却活下来了。
而她能苟活至今日,有一半是因为后来似是顿悟了什么的星霄力保。
也许是为了赎罪,他不再积极逼迫她,反倒退到了远处,远远望着,接济她,同时给予她在那一夜昏在雪地受到的冻伤药物医治。
“三十年?秘境一日,人间三十年。那么多海姑娘她……”
“是,她是我的亲生骨血。虽然这几年来她未曾喊我一声娘,但那已不重要了。”再忍不住噙在眼眶里的泪水,鄂嬷嬷将那锦盒紧紧拥在怀中。
那一个冬夜,她在她独居了三十年的小石板屋前,听到了小小婴孩的啜泣声,她还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没想到打开门一看,却真的有个小娃儿被搁置在她门前。
小娃儿睡在一张兽皮里,洪声哭着,手脚挥舞着,小脸蛋儿红扑扑,好有生气,而她身上则置放着锦盒中搁着的这朵雪藏花。
当下她虽是抱起了小女娃,可仍以为定是谁那么狠心将初生的娃儿抛弃;就在她将女娃抱进屋,趋近烛火细看时,她惊愕不已。
女娃头顶有着一枚拇指大的梨形朱砂胎记,那与她三十年前被妖给带走的女儿脑心上的那枚一模一样,且那眸子和嘴儿,就跟她爹一样啊。
甚且,那合该出生就带有她家族的残疾心病,在娃儿身上却不复见;她就像脱胎换骨似,经过了三十年,又回到了她身边,且是健康无恙的!
“那妖……不是抢走我的骨肉,而是带走她,医好了她,又将她还给了我。只是她那么小,而我已然老去,若认了她,她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