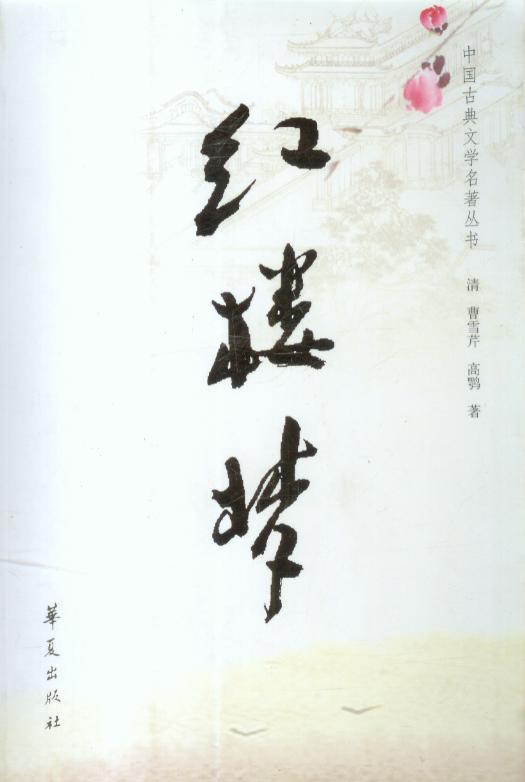红楼之扣连环-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向宠辱不惊八分不动的礼部侍郎林探花林大人都落了一身鸡皮疙瘩,这老货,忒能恶心人。
正要诘口反击,忽听旁侧传来个刚正肃然的嗓音:“启禀皇上,此次惊雷事件连钦天监也未曾提前察觉,坊间俱传乃是天降横祸,将要惊醒我大锦。臣纵观朝野,如今陛下朝乾夕惕,诸大人也宵旰勤劳,天下歌舞升平海晏河清,实乃盛世也,若非要寻一丝不妥——那便是后宫子嗣稀少,文后善妒无德,臣恳请皇上——下旨选秀!”
贡院里一应事务皆被大火烧光,林府正是太平安生,也不必人人皆为放榜伤神劳心。
贾环正坐在送春亭里头,拿着把小银剪子替一盆芍药剪枝,那头莲香领着两个模样周正的小丫头过来,道是北静王爷投来了拜帖,要见他一见。
“倒是稀奇,昨晚才叫人搅了清梦,他不在自己府上毫升待着,上赶着来见我作甚?”贾环扔下剪子,接过双灯递来的布巾擦了擦手,唇角浮起一丝玩味。
若非莲香只差赌咒发誓,贾环倒还真有些不敢认此时厅里负手而立的乃是一向温和卓然的水溶。一身滚银边儿的缎面缁衣,两肩又绣有朱紫四爪腾云蟒,修眉俊目间阴云密布,竟似有些山雨欲来之意。
“昨儿十五怎么你了?瞧你的模样,倒像是要吃人。”想来北静王实在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之人,活到今儿个也不过吊在了龙鳞卫指挥使这一棵歪脖树上,贾环悠然步入厅内,半倚在太师椅上饶有兴趣地打量他。
水溶面上隐隐浮出一丝讥诮,唇角冷冷翘着:“小王可不敢劳驾指挥使大人,不过是白白当了回替身,险险在太后娘娘手上栽了跟头也讨不来他一句好话罢了。”
贾环一扔茶碗,轻笑道:“你何苦一大早儿来我这里拈酸吃醋,有什么话,只管找他说去。昨夜那事也是对不住你,但想来你也未必不是得了好处。”
水溶身形僵立,终是一声长叹,无奈地耸下了肩。
昨夜惊雷时分,整个盛京里只怕有没几个能安寝的,水溶本不过歇了一时片刻倒被闹醒,待安抚府下一众惊慌失措的婆子婢女,也料到了此不眠夜,恐怕多生事端,便披了大衣裳坐在书房里静候宫里传信。
那房门倏然大开,水溶尚来不及细思,直直立在门槛儿上,一身亮地银纱红袍的高挑青年便把他震住了。
雷光雪亮,刑十五脸上白是白,黑是黑,细密的汗珠子沿着鼻梁缓缓流下,双目里的光芒唬的他一时间近乎忘了呼吸。
对方木着脸,浅色的嘴唇一开一合:“北静王,请替皇上解围。”
事后想起,当时的刑十五分明是因力竭而显得狼狈憔悴,怎么自个儿就跟魔怔了一般生生看出几分出尘之美,还迷了心窍子一样任他带自个儿进了宫。
实则替赫连扣犯险本也没有什么,于公,他们是君臣,于私,他们是手足,说句难听的,天下离不了赫连扣,却未必缺得一个北静王。只是若非后来横生枝节,自个儿又被莫名的恼怒嫉恨冲昏了头脑,唐突了刑十五,恐怕也不会站在林家厅子里仿佛个傻子一般自讨没趣。
贾环见不得他这番失落颓然模样,扣了扣茶碗盖:“昨儿陈皇太后去了乾清宫?”
水溶也算稍稍捡起了些理智,啜了口莲香端来的热茶平复了下心情,方缓缓道:“正是。昨夜贡院起火约莫一个时辰,正够十五将我带到宫里上下安排完毕,陈皇太后便携忠顺等一干人等来了。我也不曾料到,她竟是有胆儿直闯禁宫,我纵然身形与皇兄有八分相似,一见面,却是要捅破了大天。万般无奈,只得、只得与十五假意行那苟且之事,才算逼退了她。”
贾环惊得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去,且不提那陈皇太后与忠顺仿佛借了雄心豹子胆,水溶和刑十五这法子实在是“十五他人呢?”
水溶抹了把子脸苦笑道:“今早儿便不见了人影,我到处寻他不到,才来你府上叨扰。”
贾环观他面色,直觉此事恐还有隐情,只是水溶不想说,他也不便多问,略略沉吟一阵,方斟酌道:“我倒是听赫连说过,十五乃是十多年前山东旱灾之时涌入京城的流民之子,只因路途遥远,父母刚沾了京城地界儿便染病亡故了,他便一直在郊外城隍庙讨饭吃。后来也是遇到了时任龙鳞卫北镇抚司副使靳西子方学武识字,他既不在别处,你不妨去碰碰运气。”
水溶的脸上登时显出非同寻常的神彩来,匆匆抱拳,便头也不回地奔将出去。
贾环瞧着他的背影,略摇了摇头,心道这可比不得赫连扣与他,以刑十五那个性子与情商,只怕是好事多磨。
正要回屋去好生哀叹一番大早儿就叫人甩了脸子还得好声好气当回免费红娘,莲香又拿着两张拜帖来了:“哥儿,长平侯世子梁柯并大理寺卿林阳林三公子”
贾环揉了揉眉心,挥手打断她:“罢罢罢,一并叫进来便是,合该我这个早上是安生不得。”
正文 第71章
正是饭点儿,饕楼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老先生听说了吗?那大名鼎鼎的英国公叫皇帝当庭训斥啦!”一个商人模样的绸衣发福人物有滋有味地抿了口杯中物;挤眉弄眼地朝对坐儿一个眉目耷拉着满脸晦气像儿的中年人说道。
中年人举箸夹了片八宝鸭子;不紧不慢塞进嘴里;待细嚼慢咽了才缓缓道:“那并不是甚么新鲜事儿。老兄找我来,想必并不单为这个。”
那人挠了挠头,叹口气:“原也是瞒不住老先生。别看我冷子兴是一介行商,平日瞧着仿佛还有几分薄面儿,实则俱是主子人物赏赐的体面。我那泰水既是夫人家的陪房,大小姐又正是如今宫里的贵妃娘娘;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英国公既提了选秀;家中又有个年方十五鲜花儿般贵重超品的女儿;只怕心里存着的当是些不足外人道的心思。老兄您也省得;我好歹替主子家办趟事儿,这若是砸了。。。。。。唉。。。。。。”
中年人嗤笑一声:“按我说,这王家的女人多能挑事儿,似乎没个安生不能,也亏得有个京营节度使的兄长,否则盛京里但凡谁家瞧得起她?”
冷子兴忙左右四顾,从袖中掏出一细长檀香木盒推过去,急道:“老先生莫提,您家贵重不必平常,说了便也说了,只不敢叫我回去讨了责骂才是。”
那中年人觑他一眼,将盒子施施然拢进袖中,方叹了口气,道:“我也不过是欠你个人情,如今正是多劝你几句。你只单看这贾家如日中天,又投了我们王爷,实则根子里都烂光了。王爷倒是提过,那宝二爷颇有几分才学,可不爱看书,总不是个事儿,还比不得他那解元公的庶弟。你只看此次英国公仿佛一心要把女儿塞进宫里,实则不过是为了使皇帝迁怒,替宋远道脱责罢了,这宋远道既是小杨学士的弟子,又有英国公这一层,只待熬将个三五年,入阁自是不消说的。英国公家人丁凋敝,宋大人年事已高,如今正该另投高枝,好赖一笔写不出两个‘宋’字,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宋大人不过是拼着叫帝王记恨一把向这位小宋大人递了个人情而已。”
冷子兴大为吃惊,他虽是个人精,到底也不是身在官场,乍听到这九曲十八弯般的心计道道儿,一时只觉头晕目眩。
这中年人正是忠顺家里的二管事,颇有几分能耐,若非大管事与忠顺是奶兄弟,只怕如今把持王府的合该是这位才理所应当。忠顺虽日久不上朝堂,消息倒是极灵通,何况正是中立派与皇帝的大冲突,他听闻了,自是乐得找不着北,竟喊来了戏班子治下酒宴邀人来贺。中年人正是此时被冷子兴拉出来,心中未免存着一些不乐意,此刻也不过是架子端够了,又得了些添头,这才愿意出声指点一二。
见冷子兴一副被吓破了胆儿的模样,他难免又有一二得意,摸了摸颔下短须,道:“你只管告诉你家太太,叫她别想那起子无用的。且不提如今皇帝还有几分能耐,断不肯服了宋武阳,只如今皇太后,就决计不愿将皇后之位交给赫连扣做人情,好与中立派苟合。贾妃若是有十分的本事,如今也正该看清了哪位才是她真真儿该讨好的。”
冷子兴眼珠子一错:“你是说。。。。。。”
中年人举起酒杯啜饮一口,笑而不语。
饕楼里的这一番谈话自然避不过贾环的耳朵。
春二月,屋里放了两个炭盆他嫌热,裁了又叫冷,双灯是没辙了,莲香笑骂他一声“德性”,好生准备了躺椅和厚被褥,放在院中一棵已冒了新芽的高大海棠之下。
贾环细长的手指拨弄着手中的信笺,还带着一丝儿未干的墨香,少年唇角抿了抿,轻笑道:“我们的好太太果真是等不及,倒不知有几分心思实实在在落到了宫中的娘娘身上。”
莲香坐在他椅边的杌子上打着个紫红色的璎珞,听得这话,顿了顿手上动作,俏脸上露出几分不屑来。她也不是没在宫里待过,何况贾环与那位的关系她心中俱是门儿清,贾元春豆蔻年华被老子娘送进那不见天日的地方,没白也是可怜。怨只怨如今王氏一心钻在权势富贵里,满心满眼顶多再容下个宝玉,这贾元春,若是手里没点真章,沦落做个筏子也便是了。
”哥儿,咱不提这些糟心坏肚的。您那科考卷子叫天雷烧成了一堆子灰渣,可如何是好?总不能再等三年,平白耽误了工夫?”
贾环笑道:“这你自是不必焦心,想来不过几日朝中便有稳妥之册。六年前周文清大势方去,朝中党羽皆因手握重权而无法剪除,区区两届科举,培养起的人才却是寥寥无几。赫连励精图治又满心抱负,决计不愿空过此次,好叫忠顺钻了空子。”
何况,若是果真处理得当,举子皆心怀感恩,日后必当忠君不二,又是另一桩妙处。
莲香抚了抚胸口,道:“我可算是安心了,哥儿您一心想要出头,合该早早地高中,才能名正言顺逃出那泥沼狼窟来。若多个三年,也不知要凭生出多少祸端。”
贾环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你哪里来这样的自信?范进五十而中举,我如今满打满算也不过十六,师傅尚不如何看好我此次科考,你竟巴巴儿地信我?”
莲香自是不晓得他口中的“范进”是何许人也,只当大抵又是某处异志录入传闻,心说考了四五十年也是本事,书都不知道要读烂了几筐,嘴上却嬉笑道:“这有甚么的。我自是没有姑老爷的才学眼光,只是天下仅有一个哥儿,我瞧着哪处都好,不信您又信谁呢?”
贾环心里一阵熨帖,笑着摇摇头却不作他言。
天雷劈落贡院,恰巧走水烧光了举子考卷一事不过区区半日便天下皆知,一时人心浮动,隐有超出掌控之事。
想来也是如此,寒窗苦读数十载,只为一朝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如今倒好,朝廷监管不力,致使那承载着所有希望的一小叠卷纸灰飞烟灭,安能不叫人愤怒及至怨气滔天。
消息一放出来,苦苦守在贡院口的学子当即昏过去几个,或有泪洒当场或有黯然跪地或有雷霆震怒,发展到最后,数千学子竟分成两拨,白日黑夜轮换着静坐在贡院门口要求一个公道。
贾环端坐在马车上,撩起一册帘子,看着席地而坐满脸憔悴面有戚色的考生们,他最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
“他们这样坐了多久了?”贾环蹙着眉,手指略有些焦躁地摸索着手腕。
林子旭道:“一日半了,坐在这处的多是寒门士子,也有求到我与梁柯处的,只是此事未免牵扯太大,圣意难测,我等毕竟不敢轻易下水。”
“我等?”贾环剧角着这两个字,饶有深意道,“看来并不止你们二人,昨日来我府上,林兄可并非这套说辞。”
林子旭苦笑道:“解元还请见谅则个。实在是如今国子监人心惶惶,林子旭不过是舔着脸承下诸兄殷殷期盼,求一个法子罢了。”
贾环垂下眸子,淡淡道:“你既求到我头上,说不得也是敏锐得很。一贯听闻林兄高义,为人却谨慎老成,这举子闹事到底也不干大理寺卿何事。倒是昨日所见长平侯世子,胆色过人,古道热肠,与贤兄却是互补。”
林子旭默然,手指却死死捏紧,泛起一抹青白来。
贾环这个人,在学子间颇为出名。一来是因其师长乃当今阁老林如海,二来则是其身份与才学大大不妥帖之处。
京中学子多半是家里有些势力的,国子监里一板砖拍下去砸三个人,只怕两个是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往日自负才学过人,谁料偏生杀出个贾环,以庶子身份在京中士子间一枝独秀。
自他乡试一鸣惊人,京中便罕有不关注的,只是此人深居简出,一不入国子监,二不参与各类赏花作诗大会,竟是少有人见过他。这在众人看来,又未免有些假清高,毕竟同科考生乃是旁的不能比的情谊,日后入了朝堂,互相之间关照总要多些,只是贾环仿佛并不愿同他们交好,便果真以为林如海能护他一辈子吗?
除却饕楼那次,林子旭却也没有见过此人,贾家的先珠嫂子李纨和他们林家还有些亲属关系呢,来来回回旁敲侧击竟也打听不出一二,仿佛是早年因事送出府去,后来便不再与他们贾府交好,倒是他年幼时在堂上泣声陈罪状那事李纨还有些印象,言说当是从小便有些不凡之处。
林子旭其人聪颖,打从邸报那时便猜测出贾环很有些来头,有心不去招惹。哪知此次梁柯着了道,急急吼吼应下了国子监一众人精,非要淌进举子闹事的浑水来,他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贾环处撞撞运气。昨日也不见贾环多大反应,不过平平地与他们客套几句,词锋间却是对梁柯的激进愤怒有些不悦,林子旭生怕梁柯口不择言,只得匆忙拉人告辞。
今日再聚,却是贾环相邀,细思来,竟有些鸿门宴的味道。此人真真儿是七窍玲珑的心肝,早从昨日之事看出端倪,矛头直指梁柯,未免叫他有些心寒。
“你也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