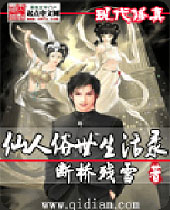�����뻹��-��2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ҩ�������������ˮƯϴ��ɲ�մѪ��������ײ��Ҷ϶�������Ա��ң���æ����һ����ˮ��
���������ձ��Ǵ������£����ڼ����ּҲ�����һ����������Դ��ֱ�������������һ���������Ŀ���֮�⣬�DZ������걻������ŵ��ܽ�����
���������Ե��ϸϸ˵�գ���������һͬ��������Ů�ӵľ�����һ�������˵�Ů�ӣ��������һ����˲ʱɷ�ף�Ҳ����Ů�����ϵ��˾��ò��ᡣ
������ϻ������˵IJ������������������dz�����У����е�������澡�
������ʱ�ꣿ�����������ỽ��һ����
��������ʱ���Ů�������������ۣ��������������Σ�����ʹǣ��ǣ���ǣ�ȴ������Ϸ�ʣ���С����̫ҽ����
�������ҹ�Ȼ���š������ǿ�����ϣ��������������Ȼ������
��������������ͼŲ�����ӣ������Ĵ�ʹȴ����ҧ���гݵ�����˻����ʹ����
����������δ�˼����档��������ת�����ʣ���������ˣ���
����ʱ��Ŭ��Ŭ�죬����֪������
��������ײ�֪�����ǿ��еġ�������˭������ʱ��ƺ���Ϊ��С̫ҽ��������ǹ��е�Ů�ӡ���Ȼ������֮�£�����Υ�����ƵĴ��£��������Ȼ������֡�
����ʱ���ڽ�����֮ʱ������������Ĵ��������Ǿ��кպ�������������ҽ������һ����ԭ�Ǹ���������֮��������ˡ�
�����������˺ü��գ�����������������˿�֮ʱ��ʱ�겻�ɴ�Ȥ������������������ô����
���������ϸϸ��ҩ�������������ݺ���ֱ��ϣ�δ����
�������������������β��˼�����̣�����ʮ���ӣ�����һС��������ʮС��������һŮ�ӡ���ʱ��ʹ�����������ӣ�����������ľ��ң���
������������ޱ���ش������ҽ�����ģ��Ҳ��ܼ������ȡ���
�������DZ����Ǹ��ܻܵ���Ȥ��ʱ��Ʋ��Ʋ�죬��Ī���ǿ��ڽ����������ϣ���
�����ո�˵�գ������ǰһ���������ѱ��˲����ʱ��ʹ��ҧ���гݣ�������Щ��������û��Ůҽ�𣿡�
������Ů��������Ӳ������ݺύ���ĵ��ˣ�����ײ���������ü�����ᴦ����Щ��Ŀ���ĵ��˿ڡ�
�������㡭����ʱ�������������ģ�ȴ��������˶������ã��ߺ���һ��������������������ҽ����μ��ˣ���
��������ҽ�߶��ԣ���ֻ�Dz��ˣ�������Ů֮�֡���������治��ɫ����
����ʱ�겻���ء��ߡ���һ�������Ǹ����������Ů�ӣ������Ŵ��˾�����Σ�ѣ������ձض�������������ţ����Ϊ������֪��ƫ�Ǹ������������ġ�
����ʱ������ÿ������ҽ�ݣ�ȴҲ�ܴӽ��������֪��Щ����֮�¡���������Ϯ�����ѹ������գ�����Ȼ������Ӱ�٣�����ƽ�����գ���������Щ�ݺ��˿ڵ�Ҳ��ֵ�ˡ�
�����������Ѿ������������������������ι��Щ��Ŵ��ʳ��������ǰ���ղ�ˮ��������������������ʳ�ʱ�겻�������á�
�������벻���㾹Ȼ���Խ��������������ȥ�ɺã����������ʡ�
����ʱ��ҡҡͷ��������Ϯ��ȴ����ø�ı�淸�ϵ��������ɼ�����֮�г��˼�ϸ���Ҵ˷���ȥ������û�������ˡ���
����ʱ�꼸��δ����������Щѣ�θУ��Է�֮ʱ��մ��һ��һ��������Ҫ����������ȴ��������ռ���ȡ�
����������Ц���Խ����������Ĵ��ǣ�����Ҫ��ΰ��㣿��
������֪ʱ�����һ˫���ӿ��������������֣��ɻ������������Щҽ�ߣ���Ů���˶�������������ô����
���������еġ����ǡ���ָ˭�������������ӣ��������������ǡ���
����������Ϊ�Ρ�������δ���꣬������糾���Ͷ������������������������ߣ�����һ㶡�
����������������������˴���Ӧ�������������
����ʱ�����Ž�����ֳ�ҽ�䣬���Ǵ�������������ɺ��棬�����������ˣ���
�������š����������
������ż��������������δ���ü������ѣ���������ʱ��ķ��䣬���ֵ������Ǹ����Ů�ӣ���������������������ȥ�ơ���
�������������Dz���Ů��ô����ʱ�겻����Ц�������Ǻδ������Ŵ���ö�����������
������������ε��������ǵ����ʺ����ң����ҡ���
���������ң���ʱ��������������ж�������������е�Ů������
������һ���ڣ�����Ȼ������������ʱ���ڹ��У����������ر�����̫��ϴ�������������������������ߵ�̫���������������ԣ�̫��ϴ���Թ����İ�Ľ֮��ʤ���Ž�����������������˶����ó���
�������Ǵ�ѧʿ����ף�����̫��ϴ������������ʱ����ʱ����Ц�ݣ�һ���������쳣��
����ʱ����Ȼ����������ƽʱȴ����Ц�ֹ�̬֮����δ�й�����������ɫ�������ҡͷ�����Ҳ���������֮�£�Ҳ���ϵ�ʲô�����ˡ�����ȥ����һλ�������еķ��ˡ���
�����������ʱ�����һ�ۣ����ղ�����
��������Ů����ʲô���֣���ʱ�꼱�е���������������ģ�����Dz��ǰ��ò�������ݸ߹�ʱ�꼱�����������˫��һ����Ҫˤ����
����������һ�������������ڻ��е�������ĪҪ�������������˵����
�����������������ʱ��ȴ��������������
�������ǹ������£���Ϊʲô�Ỽ���ۼ������������������������ʱ���������������Ȼһ���ؿڴ�ʹ�����������µ���ʳ�����³���
�������������һ�����˲������࣬���������������ۻ࣬ʱ��ȴ����ֹ��ס���ᣬ�͵��³�һ��Ѫ���������ڽ������������ϡ�
�������������ԭ�أ����ô�Ŀ���ġ�����һ�����ҵ�Ů�ӣ�δ����Ϊ��ɼ��ǵĵ��˶����һ���ᣬ��ʱȴ������DZ���
���������������˯�ţ��������Ŀ��������дʵ����������������������۽�������������ᡣ
����
����Ѳ���������
����ʱ�걯�߽��ӣ������ģ�������Ϣ�˼���ʱ������ת��
���������������������ѣ���Ϊ����˱��ˣ�������������ҩ�����Ŵ������������࣬һ��һ��ι�����¡�
����������һ���Ķ��ڹ������ϣ������Լ�ǧ����У�Ҳ���Ὣ���������վ�����ʱ������ۣ������������¾�Ȼ��˺��������������������������
����������㲢����Ϊ������������ȴ����Ϊ���Ĵ��İ�Σ�����������Ȼ����
����ʱ��һ㶣���δ��Ӧ���������Ժ��⡣
������������������������֪���������������ʡ�
����������δ���ֽ���������Ƚ���ʹ����С�ˣ�
�������������Ҵ�ʱ�ж����㣬��Ҫɱ���㣡��ʱ���ݺݵض���������������üϸ�ۣ����ݰ��������¹����Ķ�����ģ����
������������Цһ�������϶�����������������ˡ���
�����Աϣ��˳�����ָ��������С�죬��һ����ҩ�������£����ʱ�겻�ɴ��������
���������ȥ����ʱ���һ��������һ�������ǿ����ˣ������ȥ���ȥ����
�������������һ����ת�����ߣ�ͽ��ʱ�������ֹ��ס�ؿ��ԡ�������������������ͷ��������Ҫ�����������������ܵ�֪�����İ�Σ�������Լ������Ǹ���Ҫ�����չ˵ķ��ˣ�������Ҫ�������
����ʱ����ѵ�Ų�������ӣ����ղ�����齣��Ƚ�������������һ�������ϵ���Ь����Щ����һĨ�ڻ�����ȥ�������о����գ���ҧ�����أ�˫��������ס���أ�����ЪϢƬ�̣����ּ�����ǰŲ����
���������Ǿ�ǿ����ҩ���ڽ�������ߴ���������ֶ��������Ų�Զ��������ǰ��Ů�ӣ�����������üͷ��
����ʱ������������һ��ϲ�õ�̧ͷ����ߴ������Ѿ����ݣ��ò��˶�ñ���������ס�
���������վ�����ã���Ҳ�������á������ķ�����ҩ��������֮ң����ȴ��������һ�����ʱ�䣬һ��һЪ�������������������������¼�ʮ�����ˣ���ƾ����Ҳ���ܲ�ס���ʹ����
�������������ƶ�����ط������������������ǰ���������ɫ���ݣ���Ȼת�������ȥ��
����Ϊ��ƫҪ�������������������ȥӭ����
����ʱ���������������˫�Ȳ�������֪�δ����˿ڱ��ѣ�ֻ�����ϵ����������ʪ��������Ѫ�Ĵ̱�֮����
������֪���ǵڼ���ͣ��ЪϢ�����������һ�����������˹�����Ȼ����һ�ᣬ�����˱�������ر��˺��۱��𣬾�����˲���ƿն�����
���������������������ֽŲ��õ�������
�����������ܣ�����������ƽ�͵�����������ŭ�����죬�������˳����ģ����Ϊ�λ�Ҫ���ˣ���
����ʱ�괹�����ӣ�˫�ֲ��������ؾ�ס�������������ί����������ֻ�롭���ҽ���������ҡ���
��������һ��������������˿ڱ�������������Ѫˮ��������ֻ���ֱ���һ���/ʪ��ĬĬ����ͷ�������������ߵ�����������������ӣ������IJ��̡���
����ʱ��ʹ������ֱ�У�ȴ��Ȼ���ĵ�����С̫ҽ����һ�ű���֮�ģ���
�������Ǹ������������Ů�ӣ���������Ȼ��ȥ������������侲һ������֪����㲻���Լ��İ�Σ����������������֮����Ҳ����Ч���������е�������
������������磬�����ֵ���������ܲ���������Ϊ����������֮�˻����������Ҫ���ˣ�
�������Ե��IJ���ҽ������Ů��˼֢֮ȴ�����ϼ��ѡ�
������������Цһ�����������е�ɵ���������Կ��������Ǻιʣ����ֺγ���֪���������������˭��
�������Ͼ�������г����Ů����ɵ������֪����Ц����Ц���Ҷ�������̤�������ɺ쳾�벽��
��������Цʲô����ʱ����ü��������ɫ���ơ�
����������δ�ش𣬱���������ǰ��ת��ҩ�������ǰ��
��������һ�����Ŷ�������������Ľ���ס�������������ʱ�������ſڣ�һ�����ޱ�������϶���������ȴ�ǶԽ���������������ڴ˴�����
����ʱ��֪��������ѵ����æ���������������£�����һ��Ҫ������������
������һ���Ǵ��һ���Dz��ˣ�§§�����ɺ���ͳ���������Ŀ���ڶ�������ת��һ�ܣ������ڽ��������ϣ�������������ȥ����
��������磬�ҡ�������������δ���ڣ��㱻����״�ϡ�
������Υ�����ƣ��볯Ϊ�ˣ�����û�������IJ�Ф����������ƽ���ﲻ����Ц����ʱ������Ӳ���������˱���������
����������ڨڨ�ر��죬ȴ��Ȼ���˳��˳�ǰ������ͷ���������Ů�ӣ�һ�����Ѿ����ͨ�졣
������������������ʱ�꼱�е���
������������ʱ������������������ݣ�����һ�������ͦ����ͬ����������������һ�����������Ů�ӱ��ƿն�����ȴ�����������ز��ȣ�����ſ�ڵ��ϣ�����������
�������㣡��������������Ц����Ҫ�������ַ�����ȴ����һ˫����ס��������֫��
�����ֳ���ɻ�Ů���ˣ�������Ŀ¶��㵣�ȴ����һ����������У�����ȴ������������������㲻С�ġ���
����ʱ��˲������࣬�����������ڽ������ǰ��������ס����˫�ȵ���������������������һ����ҽ�����ܼ������ȡ���
���������֡����������ɫ�����ںڡ�
���������š���ʱ��ˣ��һ�㡣
���������ͷ����������һ˫�������������ӣ����˲��ܾ̾���
�����������������ش�Ӧ���������Ӧ�������Ѿ���һ��ʱ��֮��
��������ʮ���ӣ�����һС��������ʮС��������ʮŮ�ӣ��������Թ��治�١�ҽ�ߵ���һ���ʰ�֮�ģ���Ӧ��һ��ƽ��֮�ġ�����ҽ����Ů���ߵ�̫�����ؽ���Ϊ�����ƺⱻ���ƶ�������㺡�
�������һ����ҽ����������ʰ���ƽ�ȣ�
�������������ϵ����Ƚ��أ����ץ��һǮ���顣���½������ˣ����ɵ��ǵ����������⼸�չ������ۣ���ȥЪϢƬ�̡���
������Ҳ�á�����������֣��Ų����ݡ���ʱҹɫ���������Ҳ����ȥ�����ġ����������ͣ�������������ҩ�㡣
������ʱ������ɢ������˭֪���ղ��������ģ���������Ů���ķ���������
����������ǰ�������ȴ��Ȼ��ԥ��ת�����ߡ�ֻ�����ڵ�Ů�����ƶ����������Ŀ��ǽ���������
���������ǡ�������
�����������������
��������ո��ƿ��ţ��㱻��ǰ�ľ�������ʱ�겻�����˿�װ�����������ݺύ�����˿���δȬ����ȴ��̻¶�ڿ����С�
����������ɴһ��㸿�����ϣ����������������������ɷ����ң���
��������״���ԭ�أ�����Ů�б𡣡�
�������������Ҵ����˿ڣ�����֪��Ů�б𣿡�ʱ�귴�ʡ�
��������������ҽ�����ǻ������ա����������Ȼ��֪�����˵��ȥ��
����ʱ�걳���������������������Ҽ�ס���������ãã��ڱ����ֹ�������ǰ���־���ɱ���ӣ����ҳǰ��
����������δ���꣬���־���ȥ���������ã��������ܣ���Щ������Щ�쵰�������ʱ����˶٣����߲�������Ȼ���������������¡�
���������Dz�����Ϊ�����������磬Ȼ����������������һ�ɺ�ͯ������������������֮�¡���ʱ������������������Ů�ӣ�������������������ͯ�����Ź�����
����������ԭ�����Բ������ǣ����־�������������ʱ�걳�������������������գ�ֻ��������Ĩ��Ĩ����������������û�У������ݵо�����Щɥ�������Ҹ������װ����ˡ������Լ��������ˣ��Դ����²ŵ���Ȭ������
����ʱ������ϸϸ����ɴ���ã���ס�˿ɲ��ĵ��ˡ���ԭ������ˣ�ƫƫ��˲����ð�ϧ���ӡ�
�������ڽ����ע���²����������������������ұ����Ǹ����ˣ�������ֵһ�ᣬ�������粻������ֻҪ�����ţ��ɰ���ǧ��������ձ���������ϣ������
������ǰ���½��Ȼ���˿��ϣ�ʱ������̧�������������վ������ǰ��ʮָ�����������µ�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