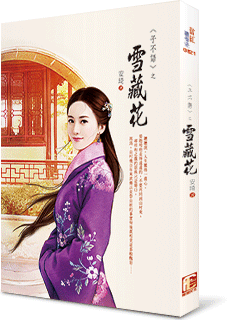铁梨花(萧马 严歌苓)全本-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铁梨花架着骡车跑到董家镇上。镇关外有一所房,写着“杜康仙酒家”。进门穿过店堂,就是个天井。一面女儿墙后面的三间北房都点着灯。这儿是远近的人聚赌的地方。见一个女子进来,所有男人都愣了。酒店的小二这才追在梨花身后进来,一连声说吃饭在前面。
“我不吃饭。”梨花回答小二,又对他说:“看着我干吗?我不能玩玩?”
她眼睛扫了一眼烟雾中的面孔,然后瞅准一张,走了过去。她搬了把凳子,往一桌人边上一坐,掏出烟杆,正要摸火柴,赌桌上一个男人替她点上了烟。
这桌坐的人里,有个名人,叫彭三儿。这儿的人们都知道他靠什么挣钱。这儿的人没一个是从正路挣钱的,但谁都对逃兵老油条彭三儿挣钱的法子很敬重。彭三儿替人顶壮丁,顶一回收三五百大洋。打死就死了,打不死三五百块大洋够他来这里玩一阵。他赌风特坏,别人不敢大赢他,赢急了他会玩命。
这时彭三儿正背运,一块怀表押的钱刚刚输掉。他掏出一把伯朗宁手枪搁在桌上,对一个对家说“那,这个先押给你,你借我三十块吧。”
对家把枪拿在手里,掏出三十块钱,拍在桌上。“三儿,这枪卖给我算了。”
“卖给你我使啥劫道去?”彭三儿笑道。他三十岁的脸膛上长着刀刻似的抬头纹,眉眼鼻梁都还是俊气的。要不是表情里时时透出的歹和赖,他也称得上相貌堂堂。
“三儿老弟,下回再逃跑,多偷两把枪,黑市上卖值钱着呢!”另一个男人说。
“你狗日的吃根灯草,放屁轻巧。”彭三儿说。“你以为跑一回那么容易?壮丁都是绑着送上前沿的,刚学会开枪就叫你打冲锋。一仗下来,脑瓜还在,你才给编到班里。那时候你才能寻摸时机逃跑。老兵们都知道壮丁里有咱这号人,盯得紧着呢,……”
一边说话,彭三儿又输了。彭三儿眼珠子红了,脸也红了。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金戒指。一扭头,见铁梨花坐在他后面。
铁梨花笑笑说:“输了算我的。”
彭三儿打量着这个女人,一时看不出她的岁数、出身,也看不出她属于在场的歹人,还是属于这时已经吹了灯睡觉的好人。
“别看了。我姓铁,叫铁梨花。这个戒指送你玩,将来赢了我要利息。”她半真半假地说。
几分钟之后,彭三儿把戒指也输了。他刚要转头向铁梨花抱歉,一个镯子又搁在他面前。
“梨花大姐,……”彭三儿心虚地笑笑。人们从来没见过彭三儿这种笑法。
“输了算我的。”铁梨花还是刚才那个口气。
彭三儿忽然想到什么,转过脸看着这个年龄难测的美貌女子。“大姐您有事求我?”
“那当然,不然我吃饱撑的?”说完她站起身;“我在隔壁等你。”
隔壁是个让人吃点心、休息、和窑姐讨价还价的所在,还搁置着两扇屏风,上面的绸子全让烟熏变了色,破的地方贴着纸。铁梨花一进来,就打发那个小跑堂把躺椅上的单子抽掉,铺上干净的。小跑堂说干净不干净,就那一张单子。铁梨花说,那就找些报纸垫上。
彭三儿进来的时候,铁梨花靠在垫满报纸的躺椅上,由小跑堂给她捶腿。
“大姐咋知道我在这儿?”
“像你这种人,还能在哪儿?”她指指旁边的椅子,叫他坐下。又掏出两文钱来,递到小跑堂面前。等小跑堂的脚步声远了,她又说:“听说你上回差点没跑掉?”
彭三儿说:“可不是,帽子叫打烂了。不过我可贼,是用扫帚挑着帽子蹲着跑的……您见过蹲着跑的人没?我蹲着跑跑,得比人家直着跑还快。”
“挣的钱又花光了?”
彭三儿马上嬉皮笑脸:“这不,您又送钱来了。”
铁梨花:“你要多少?”
“是您儿子,还是相好?”他嬉皮笑脸地把自己的头凑近她。“要是您儿子,我就少要点。这个数——”他叉开五指。
铁梨花从躺椅上支起身子,一只脚去摸索地上的鞋:“去年不才三百吗?”
“大姐您看我连五百也不值?”
她真看他一眼,说:“值。”她脚尖摸到了第二只鞋,踩着站起身:“可我得有五百块呀。就那点首饰,还让你都输了。”
“要不看您这么仗义,我的价是六百呢!”
梨花在外面打听了,顶个壮丁的确要五六百块。她扯扯衣服,往屏风外面走,却让彭三儿一下扯住了袖子。
“那咱四百五,咋样?顶壮丁是拿小命赌呢!我这命也是老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值那个钱。可我得有哇!”
“你有多少?”
“就三百。”
“三百五。”彭三儿说。
铁梨花还想再杀杀价,彭三儿开始解开他的衣领的纽扣,一边说道:“三百五,您儿子的命就保下了。您儿子的命三十万也不止:他娶上媳妇给您添孙子,给您养老送终!他去当了壮丁,您等于输掉了三十万!您看看,您花了这三百五……”他终于把肩头上一块还没长好的伤疤给扒拉出来,“您儿子就不挨教官的皮鞭了。打枪打不好,刺刀上不好,走步走不好,他鞭子就上来了。伤口再一烂,长不上,就成了这样……”
那块疤要多丑有多丑。
铁梨花眉头一紧,快吐出来了。她说:“行,三百五——让你个狗日的称心一回!”
说完她快步走出了屋子。她知道在一夜间凑出三百五十块钱几乎不可能。答应彭三儿是她想到了张吉安。张吉安也许会帮她,但她因此就欠下了天大的人情。这人情她再用什么去赎?用钱是赎不了的。
夜里一个女人家赶十里路十分不明智,但梨花顾不了了。到了上河镇就跟进了个鬼城似的,所有窗子都黑着。这正说明这个镇上的人正派。远远看见张吉安的房子了,楼上似乎还点着灯。她走上去,心想自己可是送上门来了。她把骡子拴好,再走过来拍门的时候,楼上的灯却熄了。
拍了好一阵,门才开了一卡宽的豁子,一个伙计手上擎个油灯,身子缩在临时披的长衫下面。
“找谁?”见她是个女子,伙计把门开大了些。
“张老板在不在?”
伙计把各种身份往她身上安了一遍,才回答:“张老板在城里。”
铁梨花伸出一个尖利的胳膊肘,把伙计往边上一捣,自己就要往门里走。
“唉,对不住,没请您进呢!……”伙计说。
“那就快请吧。”她说,笑模笑样的。
伙计缠不过她,让她进到厅堂里了。
“你住楼上?”她问,一面打量着厅堂。
“我就住这后头。后院还有仨伙计。”
梨花还是笑模笑样的:“这样吧,我在这儿等着,你骑我的骡子去把张吉安先生找来。”
“这可难死我了——张老板在洛阳、津县都有房,有时他还上北京、下南京,我去哪儿给您找?”
她把十块大洋拍在一个高几上,说:“找不着,我不怪罪你。”
“不中……”
“你要是怕我偷你这店里的破烂,再喊楼上的伙计来看着。”她指着店堂里摆的古董:“这些你送我,我都懒得往家扛。”
“伙计们都住后院。”伙计瞪着这个细高的女子:她可不像在胡扯。
“咱们这块风水宝地,我闭上眼给你指块地方,你只管挖,挖出来的都胜它们十倍。你还别不信……”
“我信!”一个人在楼梯上接她的话茬。
伙计和铁梨花一块儿转过脸。伙计一脸惊诧,铁梨花抿嘴一笑。张吉安身后还跟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
伙计说:“老板您没走?”
张吉安不答他,只看着铁梨花:她知道他在楼上,这点他明白。
“虎子,”张吉安对伙计说:“打上灯笼,把尹医生送回去。”
他转向梨花,指着那个伙计:“你别怪虎子。我本来不打算在这儿过夜,盘弄一批货晚了,兵荒马乱的,怕路上不安全,临时决定住下来。”他转向尹医生指着铁梨花:“这是我二十年前交下的朋友。”
尹医生十分谦谦君子,一点猜测的神情都没有。他向铁梨花打个揖,说:“幸会。那我告辞了。”
伙计和客人出去,张吉安看一眼铁梨花:“看你急的,什么事?咱们上楼谈吧。”他一见她为难,似乎也意识到孤男寡女一块儿上楼的暧昧来,便改口说:“要不咱们就坐这儿谈?我这里的东西值不值钱另说,布置得还不俗吧?”说着他走到椅子前面,手指指对面的椅子。
铁梨花顾不上含蓄,出口便问他能不能借她三百五十块钱。她从随身带的小布包里拿出地契,意思是用她的二十亩田产做借款抵押。
张吉安沉默不语,脑袋侧低着。等他抬起头,她见他似乎受了什么伤害。
“五奶奶……”他说。
“别这么叫我。”
“可您这么见外,让我只敢叫您五奶奶。”他苦楚地说。“我虽然不是腰缠万贯,三四百块钱还拿得出,送得起,用得着抵押什么田产?”
他也不看她的反应,径自上楼去了。他当然知道梨花是感动的,也是窘迫的。他在楼上的保险箱里取了张洛阳某钱庄的银票,是“四百圆”,快步下楼来,往梨花面前一放。“要有节外生枝的事呢?多五十块方便些。”梨花心里又暖又窝囊:受了这么大一份情,怎么就像被人将了一军似的?
“张副官……”
张吉安两道目光刺过来:“您不愿我称您五奶奶,您也别称我张副官。从今往后,我们直呼其名,好不好?那段往事让你我都好不愉快。”
“对不住,叫惯了。”铁梨花说,心里更是又感动又窝囊。你看,拿人家钱,嘴马上软了,人也贱了。“我就叫你吉安大哥吧。”
没来头地,张吉安一下抓住梨花的手。但他感觉到她的不从,马上又放了她。
“还不是时候,是吧?”他看着她说:“我不急。等了二十年了,再等它几年,又有何妨?”
铁梨花没料到自己会如此心乱。
“二十年前,我在饮马河边没等着你,都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还能不能再见到你。”
她想,为一个不知能否再见面的女人,他也是二十年不娶。或许这里面有别的缘故?但不管怎样,这份情还是值得她珍视。
“张副官,您是读了书的人,我这样的乡野女子……”
张吉安笑了笑,表示他心里很苦。“咱们说好直呼其名啊!”
“吉安大哥,您的情义我领了。不过我的性子您也知道一点儿:我无功不受禄。钱一筹齐,我马上还您。”她说着已不容分说地起身向门口走去。
张吉安送她出门,不急不缓地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君子报恩,也该是十年不晚。梨花这么急于报恩,可有点俗了。”
铁梨花头一犟,笑了:“俗咋着?吉安大哥肯定知道我是谁的女儿。盗墓人的后代非得沾人间烟火气,不然便是七分鬼三分人了。人间烟火气,说白了,就是俗气,活人气。”
她这张脸在张吉安打的灯笼光里,确有几分鬼魅的娇俏。
“别送了。”她说。
“你不想免俗,那我就大俗:我要一直把你送回家。”
“我怕谁?”她哈哈大笑起来:“你该嘱咐我路上别劫道、别杀人!”
说着她一跃上了骡子的背,脚一磕,骡子像战马一样跑了出去。秋天的好月亮下,她和骡子还在青灰的石板路上拖出暗幽幽的影子。
路过董家镇时,老远就听见狗咬成一片。梨花赶紧从骡子上跳下来。她把牲口牵进一个榆树林,拴上,又轻手轻脚向镇子里走去。她发现街上有几个背长枪的身影。再走近些,她看见那些背长枪的是日本兵和汉奸兵。董家镇戒严了。无非又是查什么抗日分子。
铁梨花等了好大一会儿,日本兵仍没有撤的意思。她看看月亮和星星,又摸了一下地上的草,露水刚开始下,她知道这是早上三点来钟。离天亮还有一个多钟点。
再不进镇子去找彭三儿,恐怕来不及了。她急得口干舌燥,背上出了一层细汗。
日本兵到天亮才带着他们抓到的几个无业游民撤走。大概是谁把他们当抗日分子供出去的。铁梨花心想,谁说鬼子、汉奸什么好事也不干?他们这不是帮忙清理了几个恶棍。她走进“杜康仙”时,发现鬼子们把这里抄了底朝天,里外已经没一个人了。她正站在天井里发愣,听见一个声音叫她:“大姐!”声音是从树上来的。那棵老槐树一个人抱不过来,也不知彭三儿怎么爬上去的。再一看,树对面有一挂秋千。这个人实在天分太高了,从谁手里都逃得脱。
彭三儿从树上蹦下来,说:“您看,我这人就是守信用,……”
铁梨花不跟他废话,扯着他就往外走。
“大姐还没给钱呢!”他甩开她。
“我能不给你吗?”她飞快地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银票,递给他。
彭三儿拿着银票左看右看:“我不要银票。我要听响的大洋。这银票要是假的,我不是白白送死?”
“这儿不是钱庄的印吗?”
“您知道咱这儿巧手有多少。假古董做得比真古董还真,刻一个银庄的印费啥事?”
“那你想咋着?”
“把钱庄的门敲开,兑现。”
铁梨花手里这时要有刀,一刀就上去了。
他们到了镇上唯一一家钱庄,敲开门,一个伙计说,钱庄哪里会有这么些现大洋过夜?他看看那张银票,担保彭三儿,下午一定给他兑现。彭三儿非要叫醒钱庄老板。老板也担保他,过了晌午就有现钱。铁梨花紧紧咬住牙关,生怕自己冒出什么话激怒彭三儿。这类混子就是挣你着急、绝望的钱。
终于,钱庄老板给彭三儿兑出五十块现洋,又把剩的三百五换了他的银票给了彭三儿。
铁梨花拽住一个赶早的骡车,塞给车主一块银洋。她把自己的骡子系在车旁边,叫它跟着跑,她得押着彭三儿坐在车上。
太阳露出个头顶时,骡车在董家镇通往董村的土路上驶得飞起来。彭三儿想起刚才他没仔细点查那五十块钱,这时解开用他衫子打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