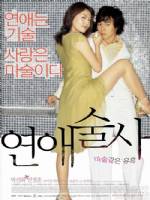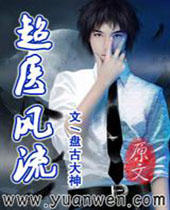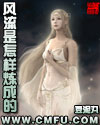三国之最风流-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遇见过几股盗贼,不过好在小人随行人多,没甚损失。”
早前在颍阴的时候,荀贞还可以时不时地听到一些朝廷、远方的新闻,自来亭舍后,往来皆本地里民、轻侠,差不多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这商人从吴郡来,路上必有不少见闻,荀贞有意打听,说道:“足下从吴郡来,不知有没有经过洛阳?”
“小人只是个小商贩,洛阳天下都会,八方辐辏,哪里敢去献丑呢?”
但凡行商的,没有不健谈的,这商人见荀贞颜色和蔼、谈吐文雅,不像是个粗人,便打开了话匣子,说道:“不过,小人虽没进洛阳城,但从附近走过。”啧啧称赞,“洛阳不愧都会,风光人物皆与别地不同!”
荀贞对洛阳的人物、风光没兴趣,直奔主题地问道:“足下路过时,可有听到什么新闻么?”
“新闻?”这商人呆了一呆。
不是每个人都关心国事的,比如眼前这个商人,他所关心的就只是钱财而已,寻思了片刻,勉强找出一则新闻,说道:“亭君可曾听闻过天子建造毕圭、灵昆苑么?”
“略闻一二,不是被司徒杨公谏止了么?”
“对,本来被杨公谏止了,但后来天子又问中常侍乐松。乐松答道:‘昔日周文王的园子有百里之大,人以为小;齐宣王的园子只有五里大小,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对朝政并无损害’。因此,天子又决定筑苑。小人路过时,已经开始动工了。”
司徒杨公,即杨赐。荀贞心道:“杨赐早前上书,劝朝廷收捕太平道,捉拿张角等人;今又谏劝造毕圭、灵昆苑,都是正论。可惜朝廷黑暗,‘天子’昏昧,不能被接受。”举首远望亭外田间的徒附、农奴,他又想道:“灾异不断,疫病接连,天下的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而朝廷不思安顿地方,却大动土木、建造苑林。……,嘿!这天下不乱才怪!”
再问那商人,那商人绞尽脑汁,又想起了两三件新闻,一一说给荀贞。但这几件新闻,要么鸡毛蒜皮,要么实为“旧闻”。
荀贞见打听不出什么了,而这商人的随从在后院还没有打完水,就随口问了句:“足下家在吴郡,不知郡中有何英雄人物?”
“小人乃吴郡富春人,同邑有一人可称少年英杰。”
“何人?”
“孙坚孙文台。”
“……。”
商人见荀贞不说话,问道:“亭长听说过他么?”
荀贞心道:“如果是那个‘孙坚孙文台’,我当然听说过。”他只知道孙坚是南方人,但却不知道是吴郡富春人,因说道:“在下孤陋寡闻,未曾闻此人姓名。不知他有何英雄事迹?”
“九年前,孙文台年方十七,时为县吏,随父乘船去钱塘,途遇海贼在岸上分赃。行旅皆惧,过往的船只不敢近前。孙文台乃与其父说道,‘此贼可击’。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挥,好像是在分派部署人众包围海贼似的。海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尽皆仓皇失措,丢下财货,四散逃走。孙文台急追之,杀一贼,取其首级而还。”
这个故事荀贞倒是听说过,只是不记得当时孙坚的年龄,此时听闻,自言自语地说道:“九年前,年方十七?”
“是啊!孙文台由是声名大振,郡县知之,因被郡府召署为假尉。次年,会稽贼许昌生乱,自称阳明皇帝,孙文台又以郡司马的身份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会同州郡官兵,合力将之击灭。因功被任盐渎县丞。这一年,他也只有十八岁而已。”
曹操二十岁时任洛阳北部尉,悬五色棒,不避豪强,击杀犯禁的人,京师因为之敛迹,从此莫敢有犯者。孙坚十七岁杀海贼,十八岁破叛乱,为一县之丞。
对比他两人的事迹,再想想自己的所为,荀贞茫然若有所失。
他的这种“有所失”,不是因为自觉“比不上他们”。曹操、孙坚,千古人杰,荀贞压根就没有想过与他们相比,他想要的只是能够保全性命於乱世而已,但既穿越到了这个时代,生长在此时,在听到两个“同龄人”的所作所为后,再对比自己的所为,也难免会有些失落。
本书纵横中文网首发,欢迎读者登录。zongheng查看更多优秀作品。
59 慨叹
深秋十月,天高云白,风从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吹过,林木的叶子大多落了,绿油油的原野与稀疏的林木中,隐约几处里聚。早上起来的时候,亭舍内的地面上结了一层冰凉的霜露,行走在上边,沾湿了鞋子,而当太阳高升后,这霜露渐渐地被蒸发不见了。
从吴郡来的商人没有多做停留,打好了水就继续行程,向东边去了。他们人虽去了,留给荀贞的失落却好几天都没消失。这天上午,他正蹲在树下,瞧着那露珠,感叹人生,前院的门外来了两个骑马带刀的县吏:“县君有令,召繁阳亭长荀贞去官寺。”
荀贞自来亭中任职亭长,至今已快两个月了,县令从来没有召见过他,包括“许仲杀人案”时也是杜买去汇报的情况,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亭部中并无大事发生,也没到每年考核政绩的时候,这时候突然遣人相召,却是为何?
荀贞急忙忙收拾停当,牵马出舍,与那个两个县吏一起上了官道,旁敲侧击地打听。
汉时的吏员大致分两类,一种是“县廷属吏”,一种类似“宾客舍人”。前者是通过正规渠道任职或被拔擢上来的,后者是主官“自辟”的,虽都领取俸禄、名在吏册,但与主官的亲近关系不同。前者可称“公吏”,后者可称“私吏”。
眼前这两个吏员都是“私吏”,与县君的关系很亲近。所谓“仕於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如果接连两代都为同一个家族效力,那么对效力者来说,这个家族就是“家主”;如果接连三代都为同一个家族效力,那么对效力者来说,这个家族就不但是“家主”,乃至是“君上”了。
如今这位颍阴县令的家世虽比不上当今的那些名门大族,比如汝南袁氏,远远达不到“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的程度,但也是世代为宦,来给荀贞传令的这两个吏员便都是接连两代都为其家效力的,要论亲近关系,比身为县令心腹的秦干还要亲近,因此口风都很严,不肯泄露县令召他去官寺是为何事,只是笑着说:“荀君放心,是好事,不是坏事。”
既然他们都这样说了,不肯直接回答,荀贞也不再询问,改换话题,与他两人指点途中景色、评说本地风土人情。
他来任职虽还不到两个月,但一则,早将本亭的辖区跑了个遍,对本地的情况很熟悉,二来,自小在颍阴长大,对本县的故事也很熟悉,不管是本亭的、还是外亭的,都是说得头头是道,远至战国、前秦时出生在本地的名人以及一些发生过的典故,皆随口道出、随手拈来。
这两个县吏不是颍阴人,是跟着县令来的,好些事儿并不了解,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已到颍阴县城。县吏观望了下天色,见刚过未时,说道:“紧赶慢赶,总算没有太晚。县君现在应正在寺中相候,荀君,请随我们来吧。”
当先引路,进入城门,带着荀贞往“官寺”行去。
……
汉承秦制,城中的规划井然有序,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闾里”,百姓们居住的地方。
一个是“市井”,也就是市场,买卖东西的所在。
再一个就是“官寺”了。
和“里”外有墙垣一样,“官寺”的外围也有墙垣,并且墙垣更加高大。若将整个颍阴县城称为“大城”,那么“官寺”就是一座“小城”。前汉时,“官寺”在城中的位置不固定,有的在城中,有的在城东,本朝以来,逐渐都迁到了城北,遂成为了一种定制。
为节省人工、材料,很多“官寺”会建在县城的西北角或东北角,这样,利用原先已有的城墙,只需要再分别向外引出两道墙垣就能把“官寺”包围其中了。颍阴县的“官寺”就在城之东北角。
……
荀贞三人,经市井、过闾里,到了城东北,迎面一个石阙,正对着大路。石阙后边即“官寺”的大门。寺门通常南向,取“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颍阴寺门即是如此。——也有的“官寺”门前不立石阙,改为立两个桓表,都是取其庄严显目之用。
门阙或桓表的边儿上,有一个建鼓,悬挂木上。吏民、县中有事,便击打此鼓,以让人知晓。荀贞在前世时虽没见过“建鼓”这玩意儿,但在影视上多有见过,似乎直到清末民国时期,衙门门前还有这东西,所以穿越以后见到此物也不惊奇。
就像亭舍门边有“塾”一样,寺门的两边常也会有一间或几间房,与围墙相连,门往外开。这是供外地来的官吏们更衣用的。如果长官暂时没有空儿见他们,他们也可以在其中歇息。这会儿,“塾”中就有一个刚从外地赶来的小吏,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冠带,准备拜见上官。
荀贞是县令召来的,听那两个县吏的意思,县令也正在等他,自然不必在塾中等候,跟在那两个县吏的后边,恭谨地步入了寺中。
……
寺门口有两个门卒。县君御下甚严,这两个门卒皆持戟,站在门口的两侧,相对直立。若是荀贞独自前来,少不得会被盘问几句,但此时有那两个县吏引导,门卒一句话都没问就放了他们进去。
进入寺门,当面一道土筑的罘罳。罘罳,即是屏风。上边泼墨染绿,画了两株丰盛挺拔的大树,树干粗壮,虬枝盘旋,干为黑色,叶则墨绿。右上题了两行字,写道:“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为一家,则连理生”。儒家提倡仁政,这两句话正合了圣贤的教诲。
那两个县吏久在寺中,对这幅画熟得不能再熟了。荀贞此前出任亭长时,为拿告身文书也曾来过寺中、见过这幅画。三人都没做停留,直接绕过罘罳,来入庭中。
庭院既广且深,正中一个大堂,屋檐飞角,雄伟高壮,这里就是县君升堂办事之所,名为“厅事”,又叫“听事堂”。堂前有台阶,延向院中。——县君并不是每天都升堂办事的,勤快点的两三天一视事,懒一点的四五天一升堂。今天并非县君升堂的日子,堂门紧闭。
两个县吏略微停了下脚,说道:“县君在后边舍中。……,荀君,请你先去‘便坐’里暂坐歇息,等我二人前去通报。”官寺的布局,前边办公,后边住人。“舍”就是“宿舍”,上到县令、丞、尉,下到普通吏员平时都在舍中居住。
荀贞作揖应道:“是。”
这两个县吏还了一礼,自经过院中的石子路,绕过“听事堂”,往后边“舍”中去了。荀贞目送他们远去,直到身影不见,这才转顾左右。
“便坐”,即“听事堂”左右的厢房,每天都有小吏在内值班,负责处理日常的小事。此时下午,正忙的时候,各个“便坐”里都坐了不少外来的吏员,观其衣着,有乡蔷夫,也有与荀贞一样的亭长,还有里长,间或亦有百姓。吵吵嚷嚷、纷纷闹闹的。
另有两三个小吏可能来得晚了,排队比较靠后,又不耐烦吵闹,所以没在室内等,而是立在庭中的树下。一个扶着树干,低头蹙眉,不知是在思忖公事,还是在想些别的。另外两个一个面对罘罳,跪坐树下,捧着一卷竹简细细观看;一个依树而立,呆呆地看着“官寺”东墙。
看东墙的这位侧对荀贞,看竹简的这位全神贯注,都没注意到荀贞和那两个县吏的进来。蹙眉的那位大概眼角余光看见了他,之前抬头瞧了他们一眼,可能不认识,又低了下头。
“便坐”里都有人,荀贞没有进去,而是沿着罘罳后的走廊,来到西墙边的一棵枣树下站定。谚云:“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晒成干”。早过了枣子成熟的时节,树上空剩黄叶,地上落叶片片。不知怎的,院中尽管热闹,荀贞独立树下,却莫名有些萧瑟之感。
他自嘲一笑,心道:“只是听那商人讲了一点孙坚的故事,我这心情却就能‘失落’好几天。孙坚号称江东之虎,本非我这样的常人可比,又有什么可‘失落’的呢?——设若孙坚是我,如果他能提前知道黄巾将要起事,怕绝不会如我这般惶恐不安,说不得,反倒会跳跃欣喜,以为立功名、名垂后世的机会将要来到。”
想虽如此想,看看自己以“弱冠之龄”,任职亭长后每日忙得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苟苟且且”每日只为“保命”奔忙,如今还不得不在庭中等候县君召见,而那孙坚却早在十七八岁时已杀海贼、剿大寇,名动一郡之地。这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让他心有所动、发出感慨。
他低着头绕树踱步,感慨良久,末了站定,一手按住腰边的环刀,一手拍打枣树,喟叹道:“人生一世,朝露日晞。”随着拍打,几片黄叶飘落,如黄蝶起舞,有的落在了地上,有的落在了他的肩头。
……
一百五十年前,光武皇帝说:“人苦不知足,即平陇,复望蜀”,但正是因为“得陇复望蜀”,所以才有了“光武中兴”,才有了一统天下。荀贞此时的心态与之相似,也是“已平陇,又望蜀”。
如果他现在不是亭长,如果他现在没有结交到许仲、江禽、高素等本地豪杰,如果他没有已组织起百余人的“一屯”里民,就算听到十个孙坚的故事,他也定然不会有此感叹。而正是因为他已将亭长做好,已结交到不少本地轻侠,已从最早的“独身一人”慢慢发展到了现在的“渐有羽翼”,所以才会被孙坚的故事触动,所以才会有此感慨。
他穿越到汉代已有十来年,虽然本质上还是“后世人”,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风尚的影响。
两汉之人无论青年、中年,抑或垂垂老矣的暮年,皆“志大、言大”,有雄强的心态、积极的进取精神,渴望建功立业、光耀声名,便如程偃、陈褒、杜买、黄忠这样的乡野粗人有时也会自称“大丈夫”,何况像荀贞这样读书识字的士子、儒生?
十几年前死去的“名士中的护法”汝南陈蕃,年十五出豪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十五岁就以“大丈夫”自居,而最终他果也以其身殉其志。汝南紧邻颍川,陈蕃的故事,荀贞自穿越后就常有听闻。
经年受这样环境的熏陶,潜移默化,他的性格、志趣自也会与穿越前有所不同了。经过两个月的辛劳,有了一定的“班底”,有了一定的“保命”把握,他开始得陇望蜀。
……
正感慨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