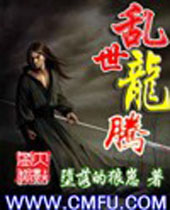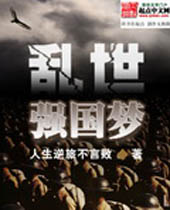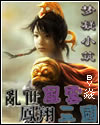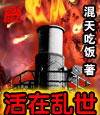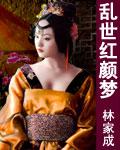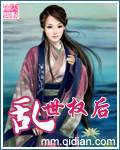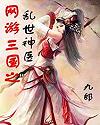乱世栋梁-第1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公,我就担心活捉了他,却无法让他给侯王效力呀。”
“无妨,你们只管把他带到我面前。”王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我只需三言两语,必能说得他心锐诚服,为大王效命。”
见郭元建有些疑惑,王伟解释:“这萧氏自立国以来,一向压制寒人武将,那李笠如此卖命,必然是想着以军功晋升,我只需告诉他现实,他自然就明白了。”
王伟对梁国的制度有些了解,发现一个很可笑的事实:梁国朝廷压制武人,设了重重障碍,避免寒人以军功提升地位,乃至跻身士族。
这个制度,王伟琢磨过,介绍起来:“梁国的将军号,不入官制,自成体系,经三次革新,如今分为三十四班,班多为贵”
“一到七班,为流外军号,等同流外官,是专门给寒人武将设置的。”
“八班以上,等同流内官,有二百三十个将军号。”
郭元建听到这里,惊叹:“二百三十个将军号?萧氏这是要鼓励军功吧?”
“哈哈哈,你也这么认为?”王伟笑起来,笑容有些冷:这就是萧老翁的高明之处,可惜,瞒不过有心人。
“将军号,有重号、杂号将军之称,梁国的将军号,三十班起,才是重号将军,共三十五个。”
“那么,七班到二十九班这流内杂号,有一百九十五个将军号,就是故意多设,糊弄人的。”
“你想想,走台阶上高楼,高低不变的前提下,台阶多了,跨步是不是就多了?”
郭元建点点头,王伟又说:“梁国的士族子弟入仕,起家将军号,最低都是十三班,而寒人呢?”
“他们要从底下的流外将军号开始,不断立军功,才能一级级向上爬,要升到流内十三班的将军号,之间隔了一百三十多个台阶。”
“你看,这些人,要立多少次军功,立多大的军功,才能转班转到十三班军号的位置?他们有这个命来博么?”
“这还不算,门第更高的士族子弟,起家的将军号更高,譬如二十三班的宁远将军。”
“宁远将军,这军号怎么这么熟悉?”郭元建喃喃着,王伟提示:“采石守将,宁远将军王质。”
“喔,是他,那个不管采石防务,直接逃跑的废物?”
“对,然而他是琅琊王氏子弟,所以将军号不能低,一上来就是二十三班的军号,如何,武德充沛吧?”
“是,是”郭元建笑起来,差点笑岔气,“武德充沛,真是武德充沛呀!”
王伟也笑起来,笑容里带着愤世嫉俗,带着不甘。
“萧老翁把军号设置这么多,看上去是鼓励军功,其实就是增加台阶,要断了寒人以军功改变门第的念想,士族一直是士族,寒族,就永远是寒族!”
“哪怕寒人再能打,也得慢慢爬这军号台阶,两百多个台阶,一辈子都爬不到重号将军的位置,别想把门第升上去!”
“门第升不上去,他们的儿子,起家将军号,还得从台阶底部开始,重新爬一遍!”
“那些士族子弟呢?起家军号,最低也能在台阶的中段,哈哈,这就是萧氏的武德,寒人上战场卖命,除非有权贵提携,否则一辈子也别想出头!”
“他们把寒族武人死死压住,压了几十年,将帅凋零,事到如今,能带兵打硬仗的良将没几个,还有脸给萧老翁谥号武?”
王伟说着说着,脸上满是讥讽。
“等你们把李笠带到我面前,我就让他数一数,军号班位,到底有多少层台阶。”
“让他想一想,这一辈子要立多大的军功,立多少次军功,才能爬上去。”
“然后,他儿子,还得重来一遍!”
“为何会如此?因为在萧氏眼中,他这种出身连寒人都算不上的人,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是贱种,都是被世家高门子弟踩在脚下的草芥!”
“看看,看看萧氏立国四十余载,到现在,有几个良将没有几个,因为许多将帅种子,已经在走台阶的时候,累死了。”
王伟说着说着,有些激动。
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当官看门第、阀阅,一个人若出身微寒,那么即便此人再有才华,也很难有机会当官。
对此,王伟不服,对于那些占据高位的废物,永远都不服。
凭什么那些废物一般的人,明明没什么才学,既无文韬,也无武略,却靠着家世好,轻轻松松做官,舒舒服服过日子。
朝廷在洛阳时是这样,后来迁到邺城,还是这样,那些世家高门子弟,占据高位、尸位素餐,而许多有才学的寒人,却只能当个吏。
所以出身寒族的王伟不服,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丝毫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无论自己的府主是什么人,要做什么事,只要愿意听他的,他就要出谋划策。
南朝的王谢高门,王伟早已闻名,所以,就想等到破城之后,看看这些天生贵种们,匍匐在侯王面前叩拜、一脸谄媚的模样。
而那些出身高贵的名门闺秀,一个个都得给侯王以及将领们做暖床的奴婢。
郭元建听王伟解释梁国的军号制度,大概明白对方要如何劝降李笠。
李笠出身不好,如此拼命表现,大概是想着凭借军功向上爬。
只要王伟让对方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梦,那么,梦醒后的年轻人,会向现实屈服的。
在压制寒人武将的萧氏那里,立功再多,也不过是啃骨头的狗。
而在侯王这里,立功就有赏,功劳越大,奖赏就越多,可以做吃肉的狼。
第五十三章 背水一战
夜,李笠正在帐中召集部下议事,明日就要打仗了,胜败在此一战,所以他要做战前动员,将自己的战术安排,再一次向部将们讲解。
“自东面延陵一路西来,有运渎过句容连接秦淮河,这运渎,按统称破冈渎,不过如今避讳,称为破墩渎。”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军要背水列阵,即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的典故,大伙应该都听过。”李笠说完,见有人茫然,便解释起来。
背水一战,是秦末群雄逐鹿时,汉军和赵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地点,在太行山脉的井陉关前。
汉军士兵多为新兵,主帅是后来的淮阴侯韩信,而赵军多为老兵,比新兵的战斗力强,且人数比汉军多了许多倍。
结果,开战前,韩信违背用兵常识,让一万士兵背靠河流布阵,将士兵“置之死地”,此举犯了兵家大忌。
赵军见了,笑汉军自寻死路,以优势兵力压上,要将汉军吃掉。
结果背水列阵的汉军退无可退,便拼死奋战,硬是扛住赵军的猛攻。
与此同时,预先埋伏在侧翼的汉军骑兵,趁着赵军倾巢而出,端了对方营地。
这突入起来的逆转,让进退不得的赵军混乱起来,很快便溃不成军。
李笠这么一说,便让部将们明白己方明日背水列阵的用意:置之死地而后生。
“但是,仅仅置之死地,不足以获胜,有人照搬,结果打了大败仗,那就是三国时的马谡,大意失街亭的马谡。”
马谡奉命守关中入陇门户街亭,挡住扑来的魏军,至少要挡一阵,为己方主力争取时间。
但是,马谡没有按照诸葛丞相的命令行事,没有在行如山路路口的位置当道立寨,而是要将军队驻扎在旁边山上。
山上没水,宿将王平反对这么做,认为敌人一旦凭借优势兵力围了山,己方会因为断水而崩溃。
但马谡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将士们为了喝水,必然能奋力与敌人厮杀,然后破敌,如同韩信背水一战那样。
结果,魏军果然围了山,山上汉军断水,攻又攻不出去,最后军心大乱,惨败。
李笠说了这个战例,进行总结:“所以,背水一战,核心不在背水列阵,而是要有策应,即一正一奇相结合。”
“背水列阵的军队,拼命挡住正面之敌,而奇兵出其不意,抄对方后路,或者侧击,这才是背水一战能成功的要领。”
“所以,我军明日决战,背水列阵的阵,是要硬扛正面,奇兵才是制胜的根本”
。。。。。。。
秋风中,句容东南,破墩渎畔,梁军背水列阵,其对面,是兵力明显多了许多的侯景军。
两军沐浴着晨曦,即将开始交战。
中军,侯景军主将郭元建看着眼前这支梁军,觉得有些不敢相信:“他们以为学着韩信背水列阵,就能打胜仗?”
前来督战的王伟笑道:“这是纸上谈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背水列阵,只是逼迫阵中将士拼命抵抗,而要制胜,还得奇兵相助,抄敌军后路,或者从侧翼进攻,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郭元建看看四周,只见旷野里没有什么丘陵、树林可供奇兵藏身。
战前,细作探得明白,梁军就一千骑兵,如今悉数列在左右翼,那么,对方还能有何奇兵来个出其不意?
便问王伟:“王公,那西昌侯打了几十年的仗,不至于以为操练月余的新兵,就能打硬仗了?不要说奇兵,就算有,正面挡不住,有奇兵何用?”
王伟回答:“他知不知兵,不重要,梁帝让他带着新兵来打仗,他就得带着,明知道是来送死,也得来。”
“可也不该背水列阵!”郭元建真觉得不可思议,“这些新兵哪里顶事,若依托营垒,好歹能多撑几日,在野地里列阵,我军只要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冲垮!”
“右翼是李字旗,想来材官营新兵在右翼,一垮,中军及左翼也就完了,那萧渊藻打了几十年的仗,哪来的信心,以为能挡住我军冲他右翼?”
王伟笑道:“你若这么想,怕是要吃亏那李字旗下,必然不是新兵列阵。”
郭元建闻言一愣,随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王伟继续说:“操练一个月的兵,根本就打不了仗,这谁都清楚,所以他们故意示弱,让我军以为,这李字旗下,是羸弱新兵。”
“那么,我军必然强攻其右翼,而他们应该是有备而来,在李字体旗下,严阵以待的是老兵,就等我军撞上去。”
郭元建便问:“王公,莫非我军攻其左翼?他们兵力就那么多,新兵不在右翼,那就一定在左翼。”
“未必,你们这么想,万一被他们预料到了呢?或许,右翼真就是新兵,而左翼已经加强,这可为第二层算计。”
“啊?那”郭元建有些犹豫,这种“我知道你所想”,然后确实“你知道我知道你所想”的弯弯绕绕,根本就是无休无止。
王伟笑道:“无妨,正面压上即可,练了一个月的新兵,根本就不顶事,只要一交锋,很快就能看出来哪边是破绽。”
他不紧不慢,说着自己的看法:“军阵慢慢逼近,哪边有连弩发射,哪边必然是新兵,我军可白刃战破之。”
“这些新兵,操练不过月余,没见过血,没杀过人,和寻常百姓无异,端着弩远远射人尚可,近战格斗,一触即溃。”
有将领问:“可他们或许有屏障?”
王伟不以为然:“这些兵,恐怕连号令都听不太懂,阵前后退,极易混乱,我军逼近,他们势必要撤到屏障后,这时,若有人高呼败了,呵呵”
他对此战己方获胜有十足把握,材官将军李笠在建康招募新兵,所以,他之前安排在城中的耳目,有许多混了进去。
现在,西昌侯萧渊藻率军出击,逼近延陵,李笠的材官营随军作战,营中以大量新兵充数。
这样的军队打不了硬仗,其内情又被王伟安插的细作探得清楚,所以,不可能赢的。
两军交战之际,新兵之中,细作必然会伺机行动,只要混乱之中高呼“败了”,那些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听了之后必然崩溃。
届时什么屏障,什么连弩,都没有用。
战斗很快打响,号角声中,侯景军各部向背水列阵的梁军压上,他们守株待兔,等来了奔兔,今日打算一战而下,吃掉这支梁军。
不过,此次专门来督战的王伟,并不是看梁军打败仗,而是为了一个人。
他见战斗开始,不忘再次交代下去:“一会破阵,若抓到材官将军李笠,留下性命。”
第五十四章 鸳鸯剪
战斗开始,侯景军向背水列阵的梁军逼近,双方的阵型都很寻常:矩形的步阵在中间,左右两翼是骑兵。
梁军骑兵较少,左右各有大约五百骑,共一千骑,这和侯景军细作先前所报消息一致,而侯景军左右翼骑兵略多,有明显优势。
双方军阵,中军对中军,左翼对右翼,右翼对左翼,侯景军军阵前列为刀盾兵。
双方距离将近百步时,双方弓箭手前出、抛射箭矢,侯景军一侧,又有刀盾兵走在长矛兵前,以作掩护。
距离拉近到百步以内时,梁军右翼后侧,忽然有骑兵上马。
随后,右翼军阵里许多士兵左右散开,露出一条条通道,骑兵策马而出,简单列队后开始向前小跑。
这突然冒出来的骑兵,让侯景军中诸将错愕:梁军不过一千骑兵,已经探得明明白白,如今分列在左右翼,怎么现在又冒出来许多骑兵了?
王伟在中军,见梁军右翼突然冒出来的骑兵,有些错愕:奇、奇兵!原来奇兵就藏在阵中!
然后觉得后背发凉:先前细作探得连弩的消息,看来是假的,于是己方在军阵前排出的是刀盾兵,根本挡不住骑兵冲击。
马蹄声起,梁军右翼冲出的骑兵渐渐加速,斜着向对角的侯景军右翼步阵冲去,双方军阵距离在百步左右,斜向距离会更长,足够骑兵加速了。
在外围护着侧翼的侯景军右翼骑兵,没来得及反应,右翼步阵仓促应对,前排刀盾兵后退、后排长矛兵前出。
但进退失据,乱成一团,已经来不及结成牢固的长矛阵对敌。
斜冲过来的梁军骑兵,已经完成加速,一个个手握马槊、高举过肩,猛地撞入阵中。
一片惨叫声中,率领骑兵冲锋的梁森,握着马槊,接连刺死、撞翻当面之敌,却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