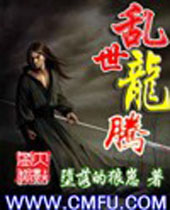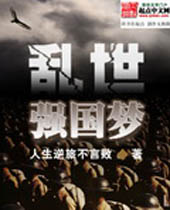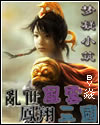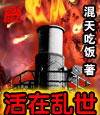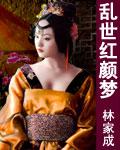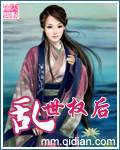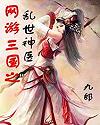乱世栋梁-第4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他们只能挤到路边,伺机发难。
但是,现在这些维持秩序的兵卒,全都面向内,那么,一旦他们要动手,就很有可能被当面或者附近的兵卒提前发现。
如此一来,行刺困难起来。
不过,他们早有准备,准备在这里刺杀皇帝。
因为在这里,他们才有像样的行刺机会:姓李的衣锦还乡,必然要在乡亲面前炫耀,故而有了这隆重的入城仪式、
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近距离动手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在之前的襄阳、江陵、巴丘、临湘等地,根本就没有。
郑远很快路对面的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的几个同伴,而自己左右不远处,也有同伴。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会御驾经过面前,就是他们奋力一搏的时候。
欢呼声忽然在街道南边响起,然后越来越大声,很快便蔓延过来。
郑远听着旁边的人兴奋地欢呼,听这些人喊着晦涩难懂的鄱阳话,不用猜都知道,“目标”要来了。
他和左边不远处的同伴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后也“兴奋“地欢呼着,口中胡乱喊几声。
忽然,有几个少年挤了过来,他们因为个子小,所以猫着腰就能在人群里灵活穿行,仿佛在水草丛中穿梭的鱼儿那样。
有少年挤到郑远身边,还要向前挤,看样子是要到前方看一看皇帝御驾的情形。
郑远却警惕起来:这几个小子,极大可能是偷儿。
趁着人多,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偷别人的钱财。
一般是三人作案,第一个负责打掩护,第二个负责动手。
第三个在稍远的地方接应,一旦失主发现财物丢失,这第三人就要把水搅浑,譬如故意指认旁边一人是贼,误导失主,给自己和同伙逃跑争取时间。
郑远之所以懂得这么多,是因为当年就做过这种勾当。
他小心提防,见那几个少年挤到前排,正要探头出“人墙”,却被组成人墙的兵卒挡住。
那兵卒骂了几句,用脚将少年往后踹。
少年踉跄着向后退,擦着郑远的腿,向后退了几步,勉强站住,没有摔倒。
随后对着那踹他的兵卒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向后跑。
一场小冲突就这么消散,街道上走来大队人马,有骑兵,有步兵,有举着各种仪仗、旗帜的侍卫,让道路两旁围观的百姓看得入神。
不一会,郑远看到一辆大马车在人们的簇拥下缓缓驶来,精神为之一振:来了!
天子驾六,所以马车用六匹马来拉,郑远看得清楚,拉车的每一匹马都戴着眼罩,直接将马眼挡住大半,只露出前方一道缝隙。
如此一来,马就只能看见正前方,而旁人想要射马眼,就会十分困难。
不过,这种情况下,近距离用袖箭射马头,一样能让其失控。
铁矢射中马头,马必然疼痛难耐,不管不顾,奋力向前跑,如此来,围绕在马车周围的侍卫,会有短暂时间无法保护马车。
而马车车厢可能箭射不入,所以,需要有人用子母杖破车厢板。
所谓子母杖,就是一根空心手杖里有一根‘子矛’,空心手杖底部很尖,插入木板后,细细的子矛如蜂刺般刺出,就能刺杀木板后的人。
同时数人以子母杖发难,有较大把握击杀车厢中的人,当然,他们随后会被乱刀砍死。
对于死士而言,只要刺杀成功,自己死也无所谓。
马车越来越近,欢呼声越来越响,郑远跟着振臂欢呼,然后准备发难。
刹那间,他见面前兵卒看向别处,随后将抬起的左臂放平,对准马车前方第一排右边的马。
忽然后背一疼,似乎有一根锥子扎入自己后背。
然后是第二根,第三根。
【看书福利】送你一个现金红包!关注vx公众【】即可领取!
多年的训练,使得郑远即便觉得很疼,也没有叫出声,他收回手,想要摸伤口,却觉得麻辣的感觉从各个伤口扩散开来。
仿佛有什么东西,从伤口处涌入他的身体。
马车走到面前,郑远的意识却开始混乱,眼前场景开始扭曲,而身体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有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其中一人关心的问:“老兄,你怎么了?”
这声音听在郑远耳朵里,只觉有些回音。
皇帝的马车已经驶过眼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瘫倒在对方身上,瞥见不远处人群里,自己的一个同伴也瘫倒了,其身边,同样有两个人,一左一右扶着。
事情不妙啊
郑远心中喃喃着,眼前一黑,再无知觉。
。。。。。。
鄱阳城内某逆旅,二楼一个房间里,刘末躺在榻上,闭目养神。
看上去似乎睡着了,但实际上他正在侧耳倾听,既听窗外街道动静,也听房门外动静。
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人坐在案旁,用小刀削手里一块木头,似乎是在削木偶。
另一个人则在整理一条腰带。
这腰带里,镶嵌着一条细铁链,铁链的末端,是一个棱角分明的小铁块。
刘末和同伴,在鄱阳住了将近四个月,明面上的身份是贩卖瓷器的商贾。
因为皇帝要来鄱阳,所以,官府之前排查可疑人物,对他们不是很注意。
因为这几个月来,他和同伴去了几次新平,正经做了几次瓷器交易,并与几个本地商贾交了朋友,迎来送往,表现十分正常。
但暗地里安置了前不久才赶到鄱阳的其他同伴。
今日,皇帝入城,同伴动手后,无论事情成与不成,必然引来全城大索,他们可以凭借之前的“正常表现”,避免官府对他们的进一步怀疑。
待得风平浪静,他们就会回去复命,顺便将同伴的一束头发带回去,放在衣冠冢里。
吃这碗饭,迟早不得好死,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无怨无悔。
刘末静静听了一会,没听到外面有喧哗,似乎没有大事发生。
难道是没有机会,所以同伴们未能下手?
刘末有些着急,若在鄱阳还是无法动手,恐怕就只能看着那姓李的返回淮阴。
对方住在皇宫里,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接近。
如此一来,任务就无法完成。
忽然,房门外响起脚步声,刘末睁开眼,坐起身,另外两人,也停下手中的活。
脚步声很轻,刘末听得出,外面不止一个人。
仿佛几只猫,蹑手蹑脚接近老鼠,即将发难。
刘末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神,毫不犹豫往窗户冲。
若有人来抓他们,那就是“此地不可久留”,绝不能恋战,否则就跑不掉了。
刘末三人动作很快,几乎是瞬间就来到窗口附近,正要跳窗,却觉得脚下一空。
房间的地板,忽然斜着塌陷,倾斜的方向,是门那一边。
三人站不住,和许多家具一道,摔了下去。
摔得头昏眼花,被一群男子围上来,按手、压脚、往口里塞抹布。
仿佛一眨眼功夫,他们就被人捆起来,想要咬舌自尽都做不到。
鼻青脸肿的刘末,看着不远处那几个丝毫不惊讶的店伙计,再看看眼前这形同机关的“斜坡”,心中悲愤:
怪不得忽然给我们换房间,原来是早有准备!!
第三十七章 士为知己者死
69,最快更新乱世栋梁 !
鄱阳城北郊,一处小山丘上,新落成的坟墓前,李笠带着儿子们,向坟墓叩拜。
他的父母以及两位兄长的棺椁,已经迁到这里下葬,而不是迁到建康。
坟墓没有高大的陵丘,也没有放多少陪葬财物,坟墓大小和寻常大户人家之墓没多少区别。
李笠迁二百户百姓在附近定居,世代免劳役、租赋,作为守墓人,听从陵官的安排,定期洒扫陵墓,清理杂草。
吴氏去世时,李笠将母亲安葬在鄱阳白石村,与李笠的父亲合葬。
此次回家乡,他正好主持迁坟,让父母和两位兄长,在鄱阳城外“定居”。
如此一来,若干年后彭蠡湖水南侵、淹没白石村时,父母兄长的墓就不会沉入水中。
李笠知道,没有不灭的王朝,而彭蠡湖区面积持续扩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仔细考虑后,给父母兄长寻了个安稳的长眠之地。
即便许多年以后,李氏楚国灭亡,位于鄱阳城外的这片墓地,依旧能静静见证时光的流逝。
守陵户的聚落,会变成村庄,一代代延续下去,村民的坟,会让这片地区变得“拥挤”。
届时,即便没有官方来祭祀李氏楚国皇室的祖坟,他父母、兄长坟茔,想来也不会显得孤孤单单。
至于他将来会葬于何处,若干年后会不会有盗墓贼来“摸金”,李笠觉得,无所谓了。
【送红包】阅读福利来啦!你有最高888现金红包待抽取!关注eix公众号【】抽红包!
人免不了一死,死后,什么事都由不得自己,所以没必要纠结太多。
不过,若干年后,自己的“遗骸”会不会被盗墓贼拖出陵墓,散落在野地里?
或者千年后,陵墓被后世的考古学家发掘,他的“遗骸”被人放在博物馆里展览?
想到这个问题,李笠忽然有些感慨。
曹操死后设疑冢,所以其真实陵墓位置千年来无人知晓,直到现代,才被人发现。
难道我死后,也得搞什么“疑冢”?
礼毕,李笠没急着回城,听梁森汇报一起案件。
他入城那天,“有司”抓获了几个刺客,这几个刺客,从江陵开始,一路跟着他,如影随行。
或许是半路上找不到机会下手,所以刺客们在他入鄱阳城之际,在路边发动刺杀。
却被早有准备的“有司”一网打尽。
“还是不招么?”李笠问,梁森回答:“还是不招,知道幕后主使的,只有其头目一人,此人姓刘名末,但这个人很硬,怎么都不招。”
李笠觉得惊讶:“怎么都不招?待客之道,都展示过了?”
梁森肯定的说:“都展示过了,能用的刑都用过了,他就是不招。”
“是个硬汉呐”李笠说完,缓缓向前走,梁森以半个身位的距离,跟在他后面:“看样子,此人,真的是死士。”
“死士?死士”李笠沉吟着,想到了各种上刑的场景。
如果一个人,任何刑罚都对其起不了作用,原因大概有两个:
其一,对方有坚定的信仰,并有了为信仰而献身的觉悟。
其二,其人意志坚定,因为某种执念,宁愿献出生命,也绝不屈服,譬如“士为知己者死”。
第二种人,在古代较多的称呼是“士”,或者是春秋著名刺客类型的人。
被抓的刘末等人,应该是某人蓄养的死士,对方派出死士行刺,自然会提防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选出来的头目,“硬”也是理所当然。
他问梁森:“接下来该怎么做,你有何建议?”
“陛下,既然是死士,再严刑拷打,恐怕也是浪费时间。”
“那就给他一个痛快吧,幕后主使是谁,无所谓了。”李笠轻轻笑起来,“杀了个刘末,还有陈末、黄末。”
“我动了世家大族的根基,必然有许多人恨不得我早死,刺客一拨拨的来,其后主使,必然各有不同。”
“那此事是否声张?还是暗中处置?”梁森问,李笠想了一下,回答:“不声张的话,如何犒赏立功人员?”
梁森明白李笠的意思,不再多问,李笠看着远处的鄱阳城,畅想起来:“也不知下一次回来,是何年何月。”
“毕竟回来一次,耗资不菲,劳师动众,说直接点就是扰民,对家乡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梁森建议:“陛下可以定期派皇子回来扫墓,正好当做锻炼。”
“轮流回来扫墓倒是可以,锻炼就不现实了。”李笠摇摇头,看着不远处的儿子们,长叹一声:“他们只会被阿谀奉承环绕,哪里能锻炼什么。”
。。。。。。
傍晚,夕阳余晖洒在田野里,将一座庄园染上金黄色。
这里,是曾经的李家庄园,如今成了行宫,位于鄱阳城东、南北鄱水之间。
李笠时隔十余年,再次回到家乡,白石村自然是要走一转的,而这座属于自己、但之前一天也没住过的庄园,也是要住一住的。
他站在阁楼三楼,举目远眺,看着夕阳西下之际,四处一片金黄的原野,只觉心旷神怡。
如果这个时代是个太平盛世,没有天灾,那么他有了这样的庄园,可以做个地头蛇,悠哉悠哉的度过一生。
可惜不能。
李昉登楼,李笠便和儿子聊起来。
刺客行刺未遂一事,李昉已经知道了,李笠接下来要和儿子说的事,和这件事有关。
“世家大族,被我们检籍、检地,被迫缴纳租赋,依附名下的劳动力,也被我们挖走大半,这仇算是结下了,不死不休。”
“他们现在只敢搞小动作,派刺客行刺,虽然成本相对较低,但效果或者说威胁还是存在的。”
李笠看着儿子,语重心长:“前朝旧事历历在目,父亲要是出了意外,你可得挑起大梁。”
李昉觉得这话有些晦气,想开口说话,李笠又说:“现在说这种话,不是晦不晦气的问题,有备才能无患。”
“父亲不怕那些所谓的死士,但有些事情,现在就得提醒你。”
“那些世家高门,乃至许多士族,就如同鸩酒,看上去似乎喝了便能解渴,可喝了之后,就是自寻死路。”
“饮鸩止渴不可取,宋、齐、梁三代更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我们若不想重蹈覆辙,得在没有渴死之前,想办法寻找新水源。”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想要一个群体,对你、对王朝有较多的忠心,那么,你就要成为他们的知己。”
“这样的群体,就是数量众多的庶族,论一家一姓的财富,他们比不上士族,论学问,他们也比不上士族,但论生机,他们比士族充满活力。”
“士族,是垂垂老朽,庶族,则是弱冠青年,国家要有朝气,就得依靠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