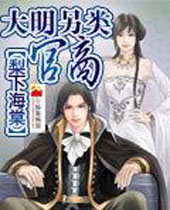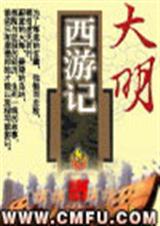大明王冠-第29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孙隽才会直接进入正题,而没有试探。
要不然你以为孙隽这种封疆大吏,会如此尊重一个区区五品指挥?
做梦。
须知五品和从二品,有着巨大的鸿沟。
黄昏笑了,“太子如何说?”
孙隽沉默了一阵,“地方卫所不在我辖权之内,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州府的兵丁可以调动,不过黄指挥应该清楚,州府兵丁的战斗力,在锦衣卫提前和地方卫所的士卒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黄昏摇头,“州府兵丁,其实只是个牌面而已,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孙布政使您这个浙江承宣布政使的官职。”
从二品,这个官职非常够分量。
孙隽何尝不知,不过这一次不一样,叹道:“问题在于,锦衣卫是可以越过我们承宣布政使司,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我这个布政使恐怕压不住。”
知道了孙隽的态度,黄昏放心了许多,“无妨,北镇抚司的缇骑,有南镇抚司来接招,孙布政使您的作用,还是威慑江浙这边的地方卫所。”
孙隽意味深长,“如果对方真不管不顾怎么办?”
布政使没有军政大权。
如果地方卫所铁了心要动手,他真压不住,最多就是掺和其中,把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大,最后不可收场而已。
而这就是他的作用:用这个不可收场来压慑地方卫所。
黄昏端起酒杯,“不管怎么说,孙布政使有心出手,我替陛下在此敬您一杯。”
孙隽接了这礼。
他当然知道这里面的曲折,太子来信中提到过一句:狗儿公公亲临东宫,说了一些事,太子于是不得不为之。
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太子其实也是在顺着陛下的意思入场。
简单一点。
孙隽看似是在为太子办事,其实是在给陛下办事,所以他才毫无顾忌的选择了站在太子一边,提前等待黄昏的到来。
也没提前多久,太子密信是飞鸽传书,昨夜抵达。
只比黄昏早了十二个时辰。
黄昏作为晚辈,下属,在孙隽一饮而尽后,又为他斟满酒,再给自己也满上,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因为此事涉及到陛下的宏图大业,又牵扯明教,当下的局面,要破局其实有很多种办法,不过我有个想法,我想把事情闹得更大一些。”
孙隽不解,“如何更大?”
黄昏意味深长的问了一句,“孙布政使可否能联系上浙江这边的明教高层,不比唐青山地位差的那种?”
孙隽震惊得口瞪目呆。
第六百零六章 扬州瘦马
孙隽没有回答,他隐约猜到了黄昏的意图。
兹事体大,需要斟酌。
许久,才试探着道:“没有其他办法了么,比如,我带着浙江布政使的要员去往于家埭,地方卫所的将领,多少会给我们面子。”
黄昏摇头,“一句捉拿明教逆贼,孙布政使如何应付?”
孙隽语结。
若是地方卫所拿出这个理由,确实没法辩驳。
偏生这次事件的中心人物唐青山,确实是明教高层。
无奈的叹了口气,说了个人名。
黄昏问道:“杭州府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他?”
孙隽苦笑,“我也不知道他藏匿在何处,甚至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不过早些时候得到的线索,唐青山似乎在西湖和他会晤过。”
根基和藏身之所应该就在西湖。
黄昏没有为难孙隽,确实如此,如果明教高层那么容易就被官府抓住了动态,又凭什么心存野望的在民间活动。
继续喝酒。
酒过半巡,黄昏起身,“孙布政使还是早些去于家埭,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这边,不妨多去几位,府城和地方州府兵丁,能调用的也都调过去罢,人多,总能壮壮底气。”
孙隽颔首。
在黄昏走了几步后,孙隽忍不住问道:“此事之后,陛下会怎么对待明教?”
黄昏侧首,回身,看向孙隽,“我等勠力同心,若是此事完美破局,明教在陛下的运作下,将不再是对大明安定存在威胁的隐患,而会是大明开疆拓土的又一支雄师。”
想了想,补充道:“那一天,漠北草原上,驰骋的铁骑之中,有明教身影,亦力把里的沙漠戈壁之中,有明教的圣火熊熊,更远的西域,明教会带着他们的新教义,形成宗教反噬的文明同化作用,而在海外,明教也会带着我大明文化春风化雨沐浴山河。”
笑道:“孙布政使,您说,得明教而得数万兵马,还有一个巨大的宗教文化,为何不招安,为何要将它们斩尽杀绝?”
孙隽懂了。
陛下用心良苦啊。
他哪里知道,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是眼前这个刚及冠的青年。
黄昏笑眯眯的道:“这策略是我建策陛下,我既然提出来了,那么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要笃定这个策略的施行,所以这一次,我必保唐青山。”
孙隽也笑了,“水乡。”
黄昏愣住。
孙隽只好补充道:“唐青山和杭州府那位明教高层的会晤地址,几经周转,骗过了很多人,但遗憾的是,我孙隽在布政司任职多年,总归有点自己的眼线,所以整个浙江的官场,包括北镇抚司的地方卫所在内,只有我知晓,唐青山和那位明教高层几经周转后,会晤场所是在西湖上面的一座花船上。”
花船名叫水乡。
孙隽其实有话没有说话,若说对浙江境内明教教众的掌控力,他一点不比锦衣卫差,甚至更好,毕竟他在浙江经营了这么多年。
洪武年间,孙隽就在浙江了。
黄昏愕然。
旋即醒悟,孙隽虽然是从二品大臣,但却是一步一步从地方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坦白点,就是一点点实力加上一点点运气。
是正儿八经从基层走上来的高官。
他了解民间疾苦。
也知道明教的人要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绝对不会造反,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不愿意对明教动手,直到确定了自己和朱棣对明教并无杀念后,才说出有用的信息。
孙隽,也想看见明教从一个“邪教”变身成对大明有利的力量。
转身,正身。
对孙隽做揖,一揖到底,“下官在此,替明教数万教众,替大明天下百姓,谢过孙布政使的一片仁心,大明有汝等君子,甚好。”
大明由此臣子,何愁不兴。
孙隽回礼,“也听闻过黄指挥的种种事迹,甚是钦佩,黄指挥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却给天下读书人以身作则,我等楷模也。”
商业互捧了。
黄昏哈哈大笑离去。
人间如此,很好。
我喜欢这样的大明。
出了孙府,带着乌尔莎等七个女子直奔西湖,来到断桥畔,看着湖面上的游龙花船,鼻子里闻着淡淡的石榴花味道和浓郁的脂粉味,很有些靡靡之风。
曾经的大宋,杭州叫临安。
有诗曰: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可想而知当年杭州的颓靡。
经历过南宋的发展,杭州西湖在明朝时期,也是繁华重镇,甚至不输给应天多少,毕竟富庶江南,又是水乡故里。
但黄昏还知道一些事。
比如对于男人而言,杭州最大的风景不是西湖,是西湖上的船娘。
明清时期,其实一直有一个说法。
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人间青楼四大极品。
反倒是秦淮女伎,并不在列。
男人之间口口流传。
当然,也在明清的书籍中详细记载,后人才知道明清时期的各种变态和黑暗。
何谓“扬州瘦马”,扬州瘦马其实某些团体打造出来的,给富贵人家准备的二奶群体,肤若膏脂,纤态盈盈,行若翩鸿,卧如娇莺。
很旖旎?
但对象却是一个可怜的群体——扬州雏妓。
亦指扬州瘦马。
瘦马是怎么来的?自然是饥寒交迫的穷苦人家,生下来无力养打,只能卖给“瘦马”贩子换些米吃,也让孩子有个活路。
所以都是万恶的旧社会。
同样是瘦马,被分为三六九等,清代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有过描述。
一等资质的女孩,将被教授“弹琴吹箫,吟诗写字,画画围棋,打双陆,抹骨牌,百般淫巧”,以及精细的化妆技巧和形体训练。
这就是标准的金丝雀,天王嫂那种。
二等资质的女孩,也能识些字、弹点曲,但主要则是被培养成财会人才,懂得记账管事,以便辅助商人,成为一个好助理。
这种稍微次一点,算工具人。
三等资质的女孩则不让识字,只是习些女红、裁剪,或是“油炸蒸酥,做炉食、摆果品、各有手艺”,被培养成合格的主妇。
这是纯粹的工具人了。
可以看出,瘦马已经缺失了作为人的尊严。
彻底沦为一种商品。
何其悲哀。
第六百零七章 欲把船娘游西湖
扬州瘦马以瘦为美,有的天生瘦弱,有的则是被迫生生饿瘦的,为的是衬托男人雄风刚健。然而,大同婆姨的风格却迥然不同,专以丰腴、床第媚功高人一等而声名远播。
明代一本小书,《五杂俎》里面写到:“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皆边塞之所无者。”
还说“大同婆娘”和“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并列叫做“三绝”。
看看,看看。
这是明代一些文人的德行。
连女伎都成了三绝。
这是时代的悲哀。
大家恐怕很难想象,不过二三百年前,媒都这座城市,竟然以白嫩嫩的姑娘而闻名。
据传,大同婆姨从岁开始,天天坐在酒缸上练习女性媚功,经过长期训练使她们的骨盆可以随心所欲的摇摆,深获中老年男人的青睐。
这是市场销售策略,紧紧抓住目标消费人群。
所以这玩意儿还真是让人无语。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这句话真心不无道理。
明清时期,大同一带流传着“大同三宝,婆姨、火锅、皮毛”的俗语。
传说就连正德皇帝朱厚照,坐拥豹房这种高级娱乐场所,也忍不住要跑到大同去散心,遇到千娇百媚的李凤姐姊妹,当场上演了一出《游龙戏凤》,黄梅戏里的故事罢。
这还算好的了。
毕竟封建时代,大多时候青楼并不违法。
不过到了清朝,制服诱惑又来了。
作为尼姑娼妓群体的代表,泰山姑子大约出现于清代乾嘉年间,当然,历史泰山上的尼姑并非都是女伎,更不可与今日类比。
当时的尼姑庵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像《红楼梦》所描写的那样,尼姑庵堂的主持需要交结权贵,庵堂的大权便渐渐落入那些社会阅历复杂、善于应酬敛钱的人手中,她们有的原先就是女伎。
她们让三十岁以下的尼姑蓄发,着俗家装束,佩带华丽妆饰,教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使她们具有大家风度
由于这些尼姑既有出家人的庄重,又有俏丽文雅的风度,如同岛国的护士、教师一类制服诱惑,深得香客垂涎。
《清稗类钞》记载:“泰山姑子,着称于同、光间。姑子者,尼也,亦天足,而好自修饰,冶游者争趋之。顶礼泰山之人,下山时亦必一往,谓之‘开荤’。盖朝时皆持斋,至此则享山珍海错之奉。客至,主庵之老尼先出,妙龄者以次入侍。酒阑,亦可择一以下榻。”
被尼姑抢了皮肉生意,原先位于山下绮窗曲户间的俗间娼妓,自然眼红不已,于是争相效仿,纷纷把青楼改成了道观。
倚门拉客的妓女摇身一变,成为庄重素色的尼姑,上演了一出出真假难辨的尘缘“美谈”。而如戏剧舞台出现的《秋江》(又名《妙常与必正》)、《玉蜻蜓》、《桃花庵》就是此间情事的描画。
这是典型的卖家影响买家市场。
再说西湖船娘。
有一首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有美景的地方,总少不了美人,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湖水滑,那西湖船娘更是生得千娇百媚,脆嫩欲滴。
西湖船娘始于唐代,在四大女伎群体中,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千百年以来,不知有多少风流名士为其写诗注载。
据考证,从白居易、元稹宦游杭州,西湖船娘便开始名闻天下,并盛极于宋,秦观称其“西湖水滑多娇娘”,一直延续到明清、民国。
西湖船娘各有住船,世称“花船”。花船一般分上下两层,上层是住宿或留宿客人的地方,下层是接待客人的客厅。
陈设时髦,可供达官富商设宴请客、聚睹。
达官贵人、巨商富子们除了在这里满足私欲,还是他们进行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秘密交易、贿赂的社交场所。
西湖船娘受南方水乡的润泽,多半娇小玲珑、秀丽温顺,擅长琴棋书画。
除了供客人狎宿,还可陪客人“荡舟”于西湖碧波之上,所谓“一叶扁舟浮行水面,一位船娘相伴游湖”,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
尤其南宋时期,杭州作为京畿,名为临安,西湖船娘的发展怎一个迅猛了得。
清朝覆灭后,闭关锁国的局势被打破,西湖船娘紧跟时代潮流,也留起了短发与留海,穿上旗袍与粗白线袜,恍若一枚枚纯洁可爱的学堂女生,招揽顾客,无往而不利。
其实所谓扬州瘦马、西湖船娘、大同婆姨、泰山姑子,都是一本旧社会女子的血泪史。
细品之下,真是一把辛酸,满纸荒唐。
但置身于历史之中,黄昏还是要适应时代。
在傍晚来到西湖,看着湖间游荡着的花船,黄昏岂能没点想法。
因为西湖船娘也是杭州税收的一部分。
宵禁这方面要宽松一些。
黄昏沉默许久,如果明教那位高层藏身在这西湖上面的花船之中,那么西湖这遍地星河的花船里,肯定有不少明教的人。
随便找人问便是。
恰好有个汉子站在断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