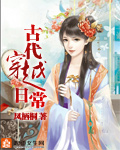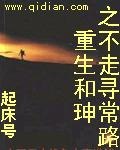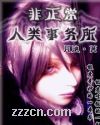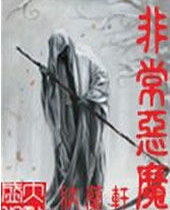�������ճ�-��102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ı��
���������˻������������������֮�ӡ�Ȼ�����ϸ��ӣ��ض��ɶ��ơ��������Ҹ������ˣ��ݽ������˸��ҡ������ܲ��ɡ�
��������Ѧ�һʱ�Ļ����ҡ�����£��˼���ͻ���
��������ֻ���ܲ��Ե������������¡���
����������������Ѧ㩼�æӦŵ��
�������������ٳ���Ԭ����ۡ��
������������꣧�����ҡ�Ԭ���콫����ͼı�������г���
�����������⡭������꣧һʱ�����岻����
�����������������������Ԭ����֪���ʡ�
������������ȥ���ף�����һ������꣧��Ի�������ҹ��ɣ��������ա������Ҳ������꣧ʵ����档
��������Ԭ�����У�����һ���������������ǡ��������������ı֮��Ҳ����
����������Ŷ������꣧æ�ʣ���Ԭ������֪������
����������ȻҲ����Ԭ����㽫��ǰ����Ԭ����ı��֪���������������1113����������ͼ��������˵����ǰ��ı������������֮�ơ�Ϊ�ӺϷʺ��թ������������Я֮�ɽ���˵�����裬����Ԭ���ء����乥ȡ���ϡ�Ȼ��ʱ�����գ�ȴҪ��Ϸ������
����������֪����ǰ�����顣��꣧�������
��������֪������С�ˡ�Ԭ�����Ե��������³ɣ�ijԸ��������Ϊ����������
���������Ŵ��ԣ���꣧��Ȼ�Ķ�����������Ϊ�������������ֵ����غδ���������֮�⣬��Ԭ����������������Ͼ������á�
����������������Ԭ����Ի����ij��������һ����ȡ֮����
������������ˣ����¸Ҳ�����������꣧�г��Ե�������Ѭ�ģ�����֮ͽ��һ�����ࡣ
�����������ơ���Ԭ��Ц�ޡ�
������������꣧������ȥ�����ұ������ˡ�
��������Ԭ����ţ�������£Ц�⡣
��������ȡ��ƽ�̰��ϡ�����˼�������һ�����͡�������ī����ȡ���ϵ´�����Ͳ�����з�档
�������������ˡ���
�����������ڡ���������ʿ���������ڡ�
��������Ԭ����ȡ���ƣ����ڻ��ˣ���Я�����ȥ�綼��Ͷ��������������
������������������ʿ������ȥ��
��������������Ȼ�պϡ�Ԭ����ȡһ��������֡�
�����������������۲ܰ�����ij��������֮����
����������خ�������Ρ�
����������ǰ��ʿ�Ʊ����ֵܣ����˺��֡����桢�Ϻ�̫�أ��������Σ��ɽ�ֺ���࣬Ǩ������š���Ԭ��ЯȺ�۹�����ƽ�����������콻�������ֽ����Σ���Ǩ��خ��
�������������ۣ����۳ǣ������������ˮ����ʱ�����Ծ���֮�⡣
����������꣧����������ͣ�㣬�����ݼ���
��������Ԭ����������ֶ���������������λ������֮�С�����Ԭ�ϣ���������������Ͷ������ν��ü������λ��Ȩ�ء�
���������Ž�������꣧��ǧ���������۳�������
������������˼����Ԭ�������Ȼ�����츮����������������ӭ��
����������꣧�ܳ�������
������������������������
��������Ԭ�ܾӸ�Ц�ʣ����������Ϊ��������
�������������������ҡ�����꣧С��Ϊ�ϡ�
��������Ԭ�������ƶ��������ҽ����ĸ����������˵������
����������꣧ҧ���Ե�������ǰ��Ԭ��������븮���Լ�����֮�¡����ʴ���֪��
��������������ȡ�ش�����������Ԭ��Ц�ʡ�
�������������ǡ�����꣧æ����
����������ȷ�д��¡���Ԭ��Ц�ݲ�������������������¡����ӱ������͡���
�����������Ҳ�����������꣧��ϲ��
�����������Ԭ�ܴ����ϯ����Ϊ��꣧�ӷ磬��Ϊ��׳�С�
��������Ԭ�ܺš��������ۡ������˴�����з��ǡ�ϯ�����サ������꣧�������������ɺ������ơ�����������
��������ʿΪ֪��������������ǰ��㡣
��1��151��һʱ֮��
����������ǰ���ԡ����������뽭����һ��֮�䡣
������������䣬�г����������ԣ���Ԭ�����������ۣ�������ʿ����֪�˶��������������Ժ�������������Ԭ������ò�����ݣ���ʿ������������̨˾���������飬���������۽ڣ�Ī��������ͥ��ʿ�������֮����������ƣ����ܣ�����֮�۶����ܾ��ˣ��������ã�����
��������λ������֮�С���ƾ��ʿ�������֮������֪Ԭ�ܣ���������֮�磬���������ۡ������������ԣ���Ԭ��һʱ֮�ܡ���
�����������롣��Ԭ�ܴ˵�������
������������꣧��㣬����ç�����ܲ���Ϊ���á����ӻ���ʹ��硣Ԭ�ܿڳ����������£��������͡�����Ŀ��֮�£������ʳ�Զ��ʡ�
����������꣧�Բ���������
�������������ѣ�������ȥ��
���������綼���������ܲٸ���
��������Ԭ����ʿ����ǰͶ�̡���ԡ���£��������������
�����������������ܲ���ȡԬ������һ�ۡ�
���������������棬�漴���д���Ԭ��·֮�⣬ij�Ѿ�֪�����ٹ顣��
����������������Ԭ����ʿ���������ˡ�
���������������������ˡ����ϵ³�������ѧ����ٽ�ţ���ɦͷŪ�ˣ������������������㵸�������ٳ���
��������νϲ�����Σ�Ī����˹��
����������Ԭ��·��Ԭ��·����һ�����գ�������ȡԬ�������հ�����棬������Ҳ����
������������֮�飬�����Ա���
�������������ŵ��ˣ������븮�����ϵ��ѻָ������
����������Ԭ���мơ����յ�Dz�ĸ���ʿ���̳����衣���ܲ��Ե������ٵ£����������¡���
��������������������������ϲɫ���������ˣ������ʵ������������ֵ���Σ���
���������������߽e���������أ���֪Ҳ�ա����ܲ��иж�����
�������������������ŷ�����ȥ��
���������Ժ���ִ�ʣ������ϵ��ϱ�����������裬˽�ش����������в���֮�ġ�
����������ǰ������������Dzʹ����������Ȱ����֮�����촫ϭ���£������ۺ�������ʱ�����˽�֪����������������������֮�֡�ȴ����֤�ݡ�
��������Ȼ��������������������¡������������������У�����ǿȡ��Ψ�����ճ��������������ˡ����Ӽ�������Ȩ֮������������������հ��������ܳ�����Ȱ�����⡱��Ȼ���о��������룬����Ϊ���˵��ա��ټ����������������۳���̫����
���������ü���Զ������Ī�������ϵ¹����ϱ���
���������������ӣ������ٹ١���������װ�����ơ�������ר�����飬����Ⱥ����
�������������������࣬����ʵ֤�����������ӣ��Ӹ����ʡ�
���������������£�������ҥ�����¡�����̫�����ԣ�������ԡ�
�������������顤���ߴ������أ����������飬��Dz��ʹ����������ҥ�����¡���ν��ҥ�����¡������Ƿ������¡�
�����������������ϱ���˹����ʳ̸֮������ʵ֤Ҳ����̫�ͷ��꣬�������ࡣν�����Ҹ��֪���⡱�����ϵ´�ʱ�ϱ������������ʵ��Ϊ����̫ʦ�����������չ�����������Ҳ��������֪��������������ϸ�����Ը��
����������ʷ��ة���������̽��Ե�������ǰ���������֣�������𡣴���������ʧ�ڱ��ҡ�������²����ȡ�ھ�������֮ս��ΪԬ�����ã��Ϸʺ���˺����������㲻֪����
����������������֮�⡣�Ժ�Ԭ���������Դ�������Ϊ�ʣ�������谵����Լ���û��Ծݻ��ϡ����Dz���Ӱ��δ����ƾʵ�ݡ�Ȼ���ɷ��ϣ���������������䣬�ѹ齭����
������������������ף�������������Ϊ���常���ԡ���
�������������ǡ����������̶��ա�
��������̫��˾ֱ���ţ��������ࣺ����ǰ������������Dzʹ��Ȱ��������������ϭ���£��������������£��˾���֪��������������Ѩ���硯��������Ϊ������������������������д˴��治��������֮�¡���
�����������ϳ����顣����̫���쵳��׳�����ơ�
�������������ȸ��顣��
�����������������١���֪��������֮��Ҫ���ҳ��������д�־������ǰ����������࣬���������о��ţ���������֮�ʣ���گ���յܼ�����λ��������㦡����������踨����Ȼ��گ�������������㱻����䣬˺�١�������������ǰ��̫������ɱ��ʥ��ڡ�
��������������ˣ������裬��Ϊ�ȵ����ɡ�Ϊ���Ա��������뻴��������������Լ����ϧ���������ء����ı��ġ���������֪��ۣ���·���������в��ҷ���������Ȱ������֮�١�
������������֮��������Դ�������ʼ����Ǵ���ͳ�����ο���ֶ���ˡ�
�����������Ǻ���Ȱ��������ˮ�����ɡ�Ȼ����������������֮�£��������ף����к��˿ɼ��δ�ͳ��
�����������ǡ��������顱���ô�������֮�����裬���ɡ�
���������������ӣ����иж��������������������Źº�����
��������̫�����ԣ��������������Բ�������������Խ������ʮһ�ˣ���Ů��ʮ�ˣ���Ů��ʮ���ˣ��������С����������£��Ը��������ң�Ϥ�����
���������������ӣ�һ����̾�����ޣ��Ѿ�֪����
���������ٹ���������ǰ�����£����ǽ��ɡ������ҵȿɲ������С�
�����������ꡣ�����������������裬˽�ش�������֮�£��ֵ���Σ���
��������ν��˵�����ģ��������⡱������Ⱥ�����������š������������Ħʥ�⡣���з���֮�������ӿڳ���˽�ش���������֮�䣬����ʵ������֮�
���������ʺ��䡰�ֵ���Ρ���
��������������������Ҳ��
�����������вܵ�����ʿ������
��������̫��˾ֱ���ţ��������ࣺ�������£���گ�������裬�ٽ�������������赹��硣�������ӣ���ϭ�ֻء���
��������ν���������������ӣ�������ס��ֺ�Ц���ʣ���̫ʦ����Ϊ��Σ���
�����������ϳ������顣������������ԡ�
���������Ŵ��ԡ�����������Ϥ�����������پ���������
����������̫ʦ�˴����������������п�̾������ɫ���䣺���ơ���
��������������������������������
��1��152�����ϲ���
�������������������������Լ���������Գ����裬������հ�����ϵ��������Ǽ٣�����������档���³��������꣬��������̫ʦ���������ԣ���̫ʦ�����ԡ�����
����������̫ʦ����פ�㣺���������ԣ���������Ȼ��������ȷ�в���֮�ġ���
����������̫ʦ���������������꣬���Ե�������������Ϊ���¹���������������������������л���Ԭ������Ϊ��Ԯ��������̫������������תͶ�������綼Σ�ӡ���
����������̫ʦ��Ի�����������࣬�������ӣ��ز����ڴˡ���
�����������չ飬���ɲ��������������꣬�����в��ʡ�
�����������������ԣ��Ϸ��Ѿ�֪�����գ����ʵdz���ȥ��
����������ٹٹ���̫ʦ����Զȥ���������꣬������ɫ����
���������������Ȱ��������������ԣ��¹���ǿʿ�£����ϵ±ز���������С���
�������������ϵ��ؼ�թ����Ϊ����������ʵΪ��̫ʦ����Ҳ�������������ĸ�֮����档
����������Ī�ǣ���Ϊ��С�������ȡ����ż�������������������
����������ȻҲ��������������̫ʦ���棬���������֮�������������������������������������ϵ���������������������������ࡣ��
����������������ܲ�������������Ե��������������ţ�Ϊ���ϵ����������������⡣�ؾٹ�����������������������룬�ݲ��ϵ��˱��ַ����¹�����ٰܡ���
������������֮�⣬���ܹ��Ƴ¹�����������������ܵó�����ȣ����������ͼ����֮��֤��
�����������������֮���������������꣬�����Ե�����Ǩ���ڼ������˶����¶ˡ����ϵ����£����������ŵ��ˣ��Զ��ǡ�����ʱ�������Ȩ�����Ҳ�������
����������ԭ����ˡ�������������������ǣ��Dz��ϵ��˱����¡����Ǽٷ���֮��������Dz���������綼Ҫ��������Ǩ֮·��Ψ�����²��ܣ������ϸ�����֪��
��������ʤȯ���ա���һ�²�����һ�¡�
��������ν���Ƕ��������Ѱ��֮�����ݻ�Ȼδ�������ڹ������֪���������ţ��������������
���������ؼ��ǣ��Լ��ˣ�֪�Լ��¡�
��������ν���۸��ֵ͡�����־����衱��ı�����ã���Ǩ֮�£���ֽ��̸������δ�ܸ���ʵʩ��������Ρ���˵�����ӡ����ݳ����У�����ζ�����ϵ����岽һ�ڣ�ʮ��һ�ڣ��ӳ��綼�������˦�����������������������֣��������ߡ�
����������֪���綼�����������
�����������ӽ��£��ض�Ҫ�ء������Ծ����������龫���ǣ�Ϊ��������ȫ��ֻ���������������һʧ���ο������л��л������ɽ���Խ���粽���롣
���������������꣬������ʿ�����ڵ��棬����ʤ�㡣�����Ϸ����أ����м������ȫ��
��������������̫ʦ���ԡ����Ӳ����������ѳɡ�
��������Ψ��ҹ���ζࡣ�����ϵ¿��ơ������з紵�ݶ����ط�����ণ���ľ�Ա���
�������������ϵ£����С���ݾ��ߡ��ٵ���뽡�֮�ơ��������ӡ�
��������ֻ���ޱ�Ȩ���ա�
�����������գ���������گ���������ﴫ���¹�����������裬�ٳʴ���������Dzʹ�綼����������пɼ������̡�������������Υ��������������ʦ���棬���ơ�
������������گ�飬�����Դǡ������裬���Ҵ��⡣�쿪���顣���ֶԲߡ�
����������������Ի�������������������Ż��˶�������dz�������֮�£����������������ߣ�����Ҳ�����������濡���ԣ��������������ֳɻ��ˡ������ϳ��綼������������������˵��پ�����
��������������������������ڷ��������ʼ��壬�������ӡ������濡���÷���֮˵��Ȱ�ɳ����裬������ϡ�����˳�������������������پ���
���������������豾�⣬������Ϊ�ۡ��κ�հǰ�˺���ԥδ��������ԭ�������İ��꣬��������δ�����������ߡ��������������������Ҳ���ƻʳƵ��ߣ��������ڡ�Ȼ���������𣬲������ա�ǰ���߹�֮�ң����������֡��ݺ������ף����Ѷ����������ο��¹�����һ��֮�ء�
��������ν���������л�ͷ��������˵�����ϲ��ϣ��������ҡ���
�������������������˺�հǰ����Ѱ��·Ҳ��
�����������ٹ�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