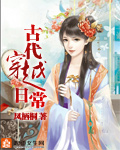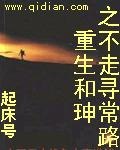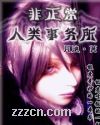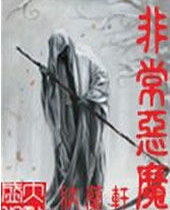�������ճ�-��117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ұ����ԣ���ة���ܣ��Ա�������������Ϊ��������Ҳ��������Զ���ɶ��ݡ�
������������Զ���ء���ʮ�긺�أ�һ�����ͣ���ڼ�������ɡ�
�������������к��ѣ�����ʮ�ء�������Զ���ʡ�
������������Ϊ��ı����Ϊ��ҩ����Ϊ�������ڼ��ʵ����
����������ʱ�������빬���磬�����ж�����ڼ��ָ��Ϊ�ģ���Ҫ������ס���Ϥ֪���飬��������ͯ��֮�У�����������֡���̫�ʣ�Ϊ����������ȡ���෴������С��硰ͯ���ꡱ�����ꡱ֮���⣬��ʮ����֧֮�š����Դ�Ϊƾ��������Ϊ�������ӡ�ʵ��Ȼ��ͯ�����������ʱ���ж��ۡ����ȵ��������˹��ӡ�
��������Ȼ������������ʧ��λ��
����������˵���Ͼ��ֳ���������ʱ�����������̫ҽ����ԣ����Ӳ���������̫�ͷ�נ�����������ս�֮�ࡣ
���������Ժ������ҡ���̫�ʣ�Ϊ��������ȫ�����л�������ᡣ
����������ʱ��ᣬ���������������֮�С���ʱ�������������ա����������������̫�ʡ�Ȼ�������������ա�
���������ܸ���ة��ڼ����ڼ������ᣬ���в�ѯ���ֹ��¡�֪��̫�ʳ������ˣ�ҹ��ƫ����������ڼ�����϶���
������������̫�ʣ����û����ͼޣ���Ͷ������Я�������گ���������µۡ����ϱ��κ����ء���ڼ�������Թۡ�
��������ν��ı�����ˣ��������족��
���������κ��ѡ�����������������������ӣ��ǻ�Ϊ�ۡ�
��������������������������Զ�������˱���
����������
��1��191����������
�����������������ɵ
������������̫�ʣ�����λ֮�ġ�������һ���еġ�
�����������Ҷ�������֪֮������̫����д��ʡ�
��������������Ի��ʱ��̫���й¡�����ͯ�ӣ��������桭����
��������ʱ���������٣������뾩�������������̫�ʣ�����Į����������
���������±ϣ��������硣
����������̫��Dz���ͯ��������衣��ϣ��������ж��ˣ������棬��ǰ���ơ�
��������������������ᡣ���б���һ�ˣ��������˹��ӡ�
���������Ҷ�ͯ�ӣ���ֹ���졣����һ�ˣ������������жȡ���һ�ˣ�ȴ��ʱ͵������Ϊ�鶯��ϸ������ò�����������Ȼ���ء����ǹ������ɡ�
��������������͵����������̫�ʺ���������Ψ�ּ�������ᡣ��֪�˾٣��������⡣
��������ʵ��̫�ʶ��ǡ��������ܲ�֪���⡣��ȡ�������壬�͵���һ�ˡ�
����������̫�����д�ʯ��ء�������ͯ�ӣ����²��ᣨ����������ġ�1��103������˷���롷����
�����������Ҷ���ͺ��ˣ�����̫�����ʡ�
��������������ͯ���ꡣ������������ˡ�
����������ͯ����ʣ���γơ��顯������̫����д��ɡ�
��������������Ի����Ŀ��Ҳ��������֮�⣬���ʶ��۹��鶯����������Σ��ʼ������裬ϸ����ò��
�����������룬���ƺ����ҡ������붭̫�����˽���ȡ�ζ����գ���������֮�����ֽ����������ڡ���ʱͯ����������£���������͵������֪���
���������ο���������ͯ����������壬���������ӣ����۵ü�����������١�
�����������֤����ʱ��̫�ʣ�������Ŀ������֮�⡣
���������κΣ������������У�Ϊ�����ߡ�����Ϊ��̫����֤���������֮�ӡ�
��������Ȼ��������̫���档ĸ�Զ�̫�ʹ۸У���λ���ơ�
�����������Ҷ���������Ϊ����ν��֪��Ī��ĸ������̫����д��ʡ�
������������ֱ����棺��������Ƹ���š���
�����������Ҷ���������ı��������̫��Ŀ����䣡�
�������������ǡ������������°ݡ�
�����������������ˣ��ֵ���Σ�����̫���ÿɷ�
�������������Ӽ�λ�����������ӡ���ĸ��֮�䣬����̸��������֪���������������ɡ�����̫�ʱ���ҩ�������ι�����帹������������ȣ�������ǧ���������گ�����Ȼ��������֮�IJ������������ͣ��������ǡ�����ȫ��ĸ����μ����ӡ���
���������ż���һϯ�θ�֮�ԡ���̫�������ᡣ
����������Ŀ��ԡ�ĸ���ԣ����ơ���
���������綼��˾�ո���
��������ϸ���ӱ��ϱ�������һ���˵ȣ���Ŀ�ɿڴ���
������������Ϊ�������Ϊα�ۡ����ϣ��ǵ��������ҡ����Ǽ���Ѫ�á��˼����ھ��ӡ�
�������������������ӡ�����ʷ��ة������һ���еġ����������£����Ա���֮�������˳ϲ����ҡ���������ӱ���ض��������£��س�һ�塣��������ż�����ʮ����������˾�ռ���Ⱥ�ۣ�ָ�տɴ����������֣�������¸��롣Ʃ����ĩ������֮����Ψһ��ͬ�����Ժ蹵�ݷ֡����Գ������С�
���������������ߣ�������ڽ�ɽ���������϶�����������ʮ�ۣ�����֧������ˮ½���С����г�����ǵ���Ϸʺ����ѵ��������Χ֮�ơ�
����������ֶ֮������Ϊ�ֵ���ᡣ�Զ�̫�ʼƣ������������ӣ��Ϸʺ�֮��Ҳ��
��������˾�ո��飬�����տڲ��ԣ���˼���졣һʱ������š�
��������Ψ��������ֱ�����ܡ�
����������˾�գ�һ����̾����������������
�����������Ŵ��Ե���������������̫��˽ͨ������
��������������˽ͨ������˾����֪���飺�����������Ϊ����ܽ����ˡ���
��������������������֪֮�����������ʡ�
�����������˻�������ᣬǰ���ܸ档����˾���Ե����Զ���̲ܣ�ˮ��ʯ���������ס�ʷ�����������С�ʷ��ϣ���Ϊ��������˾�գ�����ɱ�ġ�ʷ���˳����ң�������¾�������ʵ�˶�̫���������Ҷ����������֮�ġ��ʲ�˾�գ���������ɱ�ġ�
��������ǰ�վ�������������������ᣬ�������ڵ�ǰ��
�����������м䡣��������棺�����˼�������Ҳ��
����������˾������������Ȼ���Ѵ�롣
�����������ϸ�����ɡ���ᣬ�콫��̫������֮�£������г�������������ޡ�1��21��������֮�ӡ���_������ȷ������⣩��
������������Ե���ū������ϣ�������ʶ��������ò�����̫�����ɣ�Ȼ��������ʱ���ա�
�����������룬����������硣�پ������о�ֹ���������¡����ŷ������Ȯ���������ܴ�����
���������ҳ����ڼ��������������ڼ�ף�ʮ�겻�ϡ�������ܲ���������֪��
���������������������涾֮�£��綼�ٹ٣����ж��š�����Ϊ���������࣬��δϸ����������ξ��Σ��ֺα����֪������
����������������ϸ����
���������������ԣ������գ��������г�������������ٰ�����
����������˾�գ�������������������������Ҳ����
���������綼�����й�ƫ�
������������������ᣬ�������ڣ�������ǰ��
����������������һ�������ƺ��ڡ���
�������������ºγ����ԣ������ϲ���������������ᡣ
������������˾�գ���߱��������Ҳ��һ㶡�
������������Ҳ����Ҳ������������룬�����״Σ�����̫���ϱ������³������ӣ���
�����������ޣ���������������æ�ʡ�
�����������ˡ������Q��ҭ�����������Ի�����˼���Ѫ�ã�������Ҳ����
�����������ޣ��˼���֮�ӣ������������Ը��ӡ�
�������������ǡ���������ߵ�ף�������ֹ��
������������ľȻ������һʱ�������⡣
�������������������������ֹ��������ԣ����ٹ����빬����
�������������������������ȥ��
���������������������䣬��������żã�������ʥ��
���������������䡣���������ϳɡ���ǰ�ѱ�����֮�ģ�ֻ����һ�����㸰��Ȫ�����ϣ���̩����������档�Ķദ�䲻����
����������˾�ա���
�������������ڡ�����˾�ճ��̳��С�
����������������λ�ڼ��������磿��
��1��192��̫�ϻʵ�
������������һ����Ⱥ�����塣
������������һ�������������������ˡ������⣬�ҹ����£�Ψ�Ҷ��𡣹ض����ң����Թ��ӡ�
��������ν����ʱ��ͬ���ա�����ʱ�������Ŀ���ס�������֮�£��Ծݴ�λ�����ǿɼٴ��壬��ΪȨ�����ϡ�һ�����ѣ���˾�վ�����ɱ�ġ�
�����������ң�����̫�ӱ��ϱ����϶����뼻���š�һҹ֮�䣬����֮��
����������˾�գ�ǫ�����𣺡���������Ϊ�����ɡ���
���������������ӣ���Ե�ɡ����϶����ֻ�һ�ˣ�����˾ͽ����
�������������¡���������̶��գ������������ϡ�
����������˾ͽ�����ԡ���
�����������ϳ�������Ϊ���˵��ӳ������飩����
������������ÿɷ��ֵ����£���̫ξ����Ϊ��Σ���
�����������������顣��������ԡ�
������������������żã������������
�������������ڡ����ż�����������
���������������
����������������ı���費���ס������˱��¼��£�ijΪ�˳�����Ҷ��ԡ����ż�֮�ã��˼�������������ȳ��������ţ���Ȼմ�״��ʡ��żõ��ɣ��������Ծӡ�������ǰ��ʷ��ϣ��¾����롣���ò����˾�գ������Ժ͡����Ŷ����˼������ӣ��żú����İ�������壬�����������С��������ӣ�����Ϊ�綼Ⱥ����Ю������֮��ʷ��ϣ��ż�תͶ�綼���Ϊ���������ʵ������λ�����Dz�˾�գ��ܳ������ܵ����Գ��ã������֮λ��������̩ɽ��
�����������������������Ҳ��������Ӹ߸���������䣬���������������λ�ڣ���������
����������������������һ����Ⱥ�����������������
��������������ס��Ϣ�����������������ѭ���ƣ������λ����
����������˾ͽ�����������������£�ѭ���ƣ���������̫�ϻʡ������ĸ����������Ϊ����̫�ϻʺ������ĸ����̫��Ϊ����̫��̫����
����������ǰ��֪��̫�ϻʣ��׳�ʼ�ʵۡ����棬�����丸����̫�ϻʺ���Ϊ������������
����������������ĸΪ������ˣ���̫�ϻ��������ϣ�Ϊ̫�ϻʺ�ʱ���ڣ������ߵ����꣬������ĸΪ������ʺ�ѭ���ƣ�̫�ϻ���������������̫�ϻʺ���̫�ϻʱ����Խ��ڣ���ijƻ�̫��̫������ټ��ֺš�
����������������̫�ϻʡ����ﳤ�㣬����̫�ϻʺ���̫������̫��̫��
������������֮�ף�����ĸ���ֵ���Σ���������д��ʡ�
������������Ⱥ�������Ҹ��֪���⡣������Ϊ����̫�ʲ���Ҳ��
������������˾ͽ���ԡ�������żã�������ԣ�����������Ϊ������̫�ϻʣ�����λ����
������������֮�⡣��̫���������Ƕ����ܾ���������������ʧ���������к��ˣ�����߱����Ȼ����������ɱ��̫�ʣ���л���¡����Ƕ����Ϊ���ӣ�������ΪҲ��
�������������������ֵ���Σ����������ʡ�
�����������������Ͻ�����������˾ͽ���ٽ�������
������������̫�ϻʵۡ����졮���Ͻ��������ɺ������������ж��ơ�
�����������⡭������˾�չ����ң�ȴ����������
��������Ⱥ����Ĭ��ѻȸ������
��������ν�����ܱ��������������֮�ڡ����������������ҹ����£�˭�Ҷ��ԡ�
����������̫�ϻʵۡ��롰̫�ϻʡ���һ��֮��������ࡣ̫�ϻʣ����������������ȵ����丸ΪТ�ʻʡ�����ҫ������Ȼ����Ȩ����̫�ϻʵۣ�ȴ������Ȩ���������������������������ӡ������ָٳ�֮�ϡ�̫�ϻʵۣ�ǰΪ������Ϊ�����������ӣ�ǰΪ������Ϊ�ӡ�����Ϊ�˾���Ϊ�˸��������������������£��ڼ��ڹ������������
����������������磿������Ӹ����ʡ�
����������������گ�������²���Ϊ����˾�շ���ߵ�ף���Ϊ���ȡ�
�������������ȣ���گ�����������䣬���ͬ����
������������t��Ⱥ������Ի����������֮����売���Ϊ���ʳƻʡ����ԣ���������ȳƻʵۣ����丸Ϊ̫�ϻʣ�����ͳ���¡������׳壬���������������֮���������̫�ϻʵۣ������Ͻ�������ժ�ԣ���κ�顤�ۼ͡�������
�������������ԣ����ɡ���
��������ͨƪ��һ��δ�ᡰ������Ȼ����̫����룬������żã�˫˫��ʹ���������½�֪���綼���ӣ��������ӡ�
�������������ĸ֮�ģ�گ��ɿ����ߡ�
����������Ȼ���綼Ⱥ������Ϊ������������λ��������ȡ���ñȺ������ʲ����輰ʱ�и�ֹ�𡣴�ʱ�˿̣�����̫�ʼ������������Ǽ���������֮������
�������������ϲ��ϣ��������ҡ����ο��������£������������Ψ����ĸ��ʧ���������ɡ�
����������Ϣ���ء��ٹ�����ȸԾ����������档
������������֮�£������Ѿ�֪������������ʧ����ʱ����Ϊ�˳����������¡������ж�������һ�ߡ�Ψ��������̫ƽʥŮ��ʥŮ��������ʦ���ҹ���֮Ů��������������飬������÷���������У���Ϊ�����ڻ����ˡ������ƻ���ľ�����ж�����ڶ�����
�������������ι�֮�У�
��������Ȼ�������ˣ���Ȩ�����ף�������֪���ʷ���
������������������Ӣ�
�������������ɹ���ϡ��������أ���������¡���̫������ϴ�棬�̻̲������ա��������������ѹ˼���Ψһ������Ƕ��������
���������Ź������ϣ��Ѷ�����ҩ����֮�
����������̫�ʣ��������ң����ʽ��ã������ڣ���
���������̫�ʣ�������Ի����ǰ����������
�����������ι���֮������̫�ʣ����ʡ�
��������������������ӡ�������ܼӺ������̫�ʣ��ö���֮�����������ڡ��Ҳ�˵��δ����ý��Ȣ�����Ƕ������⣬��Ŀ���ã��������ǡ������ɲ������ȥ��
����������̫�ʣ��п���֪�����������ȥ��
��������ת��ȴ���������������߰�����ڡ�
��������������ҩ�����˽�ɱ��Ҳ��
�������������������һ��Ů��վ�������������ڳ�������������̫�ʶ�正�����̫���������ϻ����
����������
��1��193���г��Ҹ�
���������������ʡ�
�����������������̫�ʣ���������֮�£�Ϊ��ֻ��������֮������
����������ν������֮��������ָ����г�������ܼ��顱�����ֳƣ�������֮�ۡ���
����������Ԭ����Խ���顤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