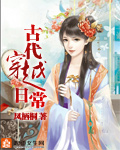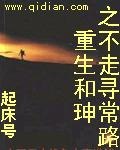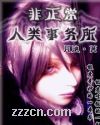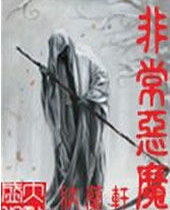刘备的日常-第90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臣,拜见大王。”正是它乾丞杨阜。
“贵使免礼。”胡毗色伽二世,口出精纯西州汉话:“请坐。”
如先前所言。大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后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贵霜承大月氏国,不忘祁连故国。
“谢大王。”杨阜称谢落座。
胡毗色伽二世已知杨阜身份,乃西域都护府雄城,它乾丞。它乾横竖十里,周回四十余里。加四面瓮城,计一百单八衢。高楼广厦,鳞次栉比。八门洞开,川流不息。凡大宗贸易,皆经城中八市往来。辖民百万,日进斗金。首屈一指,西域中枢。
尤其百万巨城,便是安息国都,亦远远不及。
胡毗色伽二世,虽未曾亲见。然往来商旅,歌谣不断。溢美之词,直令人浮想联翩。无有皮鞭,绝无桎梏。男欢女爱,一日三餐。
尤其平民竟可一日三餐。好比丰年多禾,酿酒外贩。何其奢侈。
于贵霜而言。举国三餐,足见殷富。一切皆不谈。道旁牧童问:遥远绿洲,有何神奇?
商贾笑答:一日三餐。
于餐风露宿,一饭难求之人而言。日日三餐,便是可以想象的,一切美好的极限。
更有甚者。西域都护府治下百城,六百万众,皆如此。可想而知。西域来使,贵霜王如何能不持重。
“蓟国今季,稻收几何?”贵霜王先有此问。
“回禀大王,约八亿石。”杨阜答曰。
“无怪一日三餐。”贵霜王慨叹。
“谚日:‘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然自东西商道,南北水路,皆通。鄙国新谷,贩运四海,远至徼外。西域诸国,因得其利。”杨阜对曰。
“西域屯田,可自给乎?”贵霜王又问。
“尚不能自给。”杨阜答曰:“还需陇右并国中输粮。然不出数载,当可自足。”究其原因,西域诸国“地沙卤,少田”。且种田十倍利,经商利百倍。西域各国,亦无心耕种。故若将西域五十五国除外。西域都护府百城,当可自足。
“甚好。”贵霜王笑道:“世人皆言,中夏地薄。贵国却季季大熟,广济天下。蓟王,必有神助也。”
“我主天生。乃为天下三兴。”杨阜毫无遮掩。
“和亲可乎?”贵霜王开门见山。
“未尝不可。”杨阜话锋一转:“然‘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且若知二家和亲,安息必有所备。大事难成矣。”
贵霜王轻轻颔首。若知贵霜与蓟国和亲。安息必生警觉。此时再令北匈奴西遁扰敌,安息必不会倾巢而出,大兵压境。唯有神鬼不知,方能一战功成。
“待事成,和亲可乎?”贵霜王仍不死心。
“待回禀主公,自有定论。”杨阜亦不敢越俎代庖。
“如此,也罢。”贵霜王问出心声:“安息虎踞于背,恐为其所伤。贵使可有良策。”
“大王安心,半载之内,当见分晓。”杨阜虽未明言,却也足可令贵霜王意动。
“莫非,蓟王已有破敌之策。”
“正是。”杨阜答曰。
“半载之期?”贵霜王振聋发聩。
“半载为期。”杨奉掷地有声。
“国书何在?”贵霜王再无疑虑。
“国书在此。”杨奉果有准备。
贵霜王,细看无疑。遂取刀割腕,印血为证。
“烦请贵使,传语蓟王。春夏之交,当起十万铁骑,下攻身毒。”
“下臣,敢不从命。”杨奉肃容下拜,起身后又言道:“我主有命,当奉新谷百万石,以助大王。”
“善。”贵霜王当仁不让。百万石新谷,作价三亿钞。换言之,此乃蓟国所付军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便不取粮谷,折成蓟钞。亦是一笔横财。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更何况,蓟王赫赫威名。贵霜王岂敢阳奉阴违。
事不宜迟。趁雪大封山前,杨奉原路返回。西域长史杜畿不敢怠慢,遂六百里传书国中。告知详情。
万事俱备,只待羌身毒道,凿通。
汉中,南郑行宫。
闻黄门令黄纲密报,史侯面沉如水,一时无言。
史夫人这便言道:“闻,刘益州为太常时,有侍中董扶,私谓之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益州,信其言,遂意属西川。自陛下迁都,巴蜀既定,民心得安。刘益州日渐骄横,年前,‘造作乘舆车具千乘’。今又‘有似子夏在西河,疑(似)圣人之论(注①)’。不可不防。”
1。191 阴图异计
“代汉者,宗王也。”史侯口出谶言。
史夫人言道:“莫非,刘益州,欲求封王乎?”言下之意,刘焉自恃迎史侯入汉中,有从龙大功。区区益州牧,并阳城侯,已不足以彰其功。故先“造作乘舆车具千乘”,今又“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为己造势。逼迫史侯,封王以行安抚。
史夫人之意,史侯焉能不知。然面色如常,不置可否:“天下三分,无有忠良。”
史侯当有此叹。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今汉气数将尽,人心思乱。除我蓟王,再无纯臣。
“刘益州之事,该当如何?”知子莫若(养)母,史夫人求问。
“闻益州亦出《抑兼并令》。州中豪强大姓,可有怨声四起。”史侯不答反问。
“先前,益州反贼,马相、赵祗,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进攻雒县,杀益州刺史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时益州从事贾龙,领兵数百屯犍为,遂纠合吏人攻(马)相,破之,(贾)龙乃遣吏卒迎(刘)焉。(刘)焉到,以(贾)龙为校尉,徙居绵竹。(刘)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抑兼并令》,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士民皆怨。”史夫人答曰:“妾闻,有犍为太守任岐,数次上疏,直谏无果。任岐,恨刘焉不纳忠言,或可为我所用。”
“益州从事贾龙,其人如何?”史侯又问。
“为人豪勇,素怀忠义。”史夫人所言非虚。
“如此,当可为朕所用。”史侯这便定计:“将刘焉‘阴图异计’,枉为人臣之事,暗中告知二人。说其举兵,迎王师入蜀。”
“喏。”史夫人心领神会。
史侯绝非孤家寡人。乃携西州诸将,共入汉中。麾下西凉兵马,重整武备,与五斗米鬼卒力士,共组成军。号“飞熊兵”。战力不容小觑。若得任岐、贾龙,举兵为内应。外合里应,扣关而入,长驱绵竹,兴师问罪。益州旦夕可定。
更有甚者。合肥侯,遣江东大将军袁绍,兵进交州,光复旧郡。刘焉已急令州中精锐,南下驰援。兵力捉襟见肘,乃至郡县守备空虚。内忧外困,恐难保全。
史侯,若将益州收为己用,当可与关东、江左,相抗衡。待觅得良机,迁都洛阳,亦非痴人说梦。
益州,郡十二,邑百一十八,计百五十八万(1582,601)户,七百五十万(7509430)口。黄巾之乱,益州并非重灾区。更加中原大乱,关东流民十万户,避入益州。天府之国,实力不减反增。一州之力,可比关东,江左。
更加史侯奉五斗米。将五斗米徒众,悉数收编入户。其中不乏羌氐诸蛮,更有天下信众举家奔投。与蓟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异曲同工。假神鬼之力,弥合族群鸿沟。
如同双刃之剑。宗教于国,有利有弊。
八月案比。单汉中一郡,便有十余万户,足有五十万众。“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天府之国”。可谓实至名归。
据信,若将巴西、南中等地“益州夷”,悉数编户为民。益州人口,当不下千万之巨。
史侯非我蓟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于“族类”认知,便是所谓“华夷”,当真小器。更加蓟王将南中、荆南、岭南,合称三南。立岭南都护府,蓟王尊号‘三南天王’。三南蛮区,皆归蓟王领护。故史侯亦不敢轻易染指。
多年前,蓟王命治粟都尉朱治,并水衡都尉周晖,疏通内外水路。为诸蛮王,建城邑港津。八月案比,登记造册。三南蛮国,大小种落,计千万口。蓟人震惊。
先前徼外百蛮,估曰八百万众。蓟王笑言,只多不少。
果然如此。
须知。类比西域都护府,领护西域诸国。西域诸国,乃“王治其国”。都护府,虽分门别类,为诸国登记造册。然册中城邑、兵马、人口、田宅等,皆不直属都护府。仍为其国所有。
三南蛮国,亦如此例。蛮国各自独立,却共受岭南都护府,领护。蛮国一切治政,皆出蛮王。然却受都护府监督。治国行事,不可有悖汉蛮大义。若有不尊号令,叛国投敌等重罪。蓟王可传檄声讨,或命都护府出兵讨伐。待治蛮王之罪,再立新王。循旧例,新王多出蛮国侍子。自幼入京,习汉礼汉仪,书汉文汉隶。举手投足,与汉人无异。自当与大汉同心。
深入蛮区,都护府会择战略要地,驻城塞障壁。为都护府所直辖。
如今,西域百城,皆隶属于都护府。凡此城周遭百里之内,诸国兵马皆不可擅入。若有作奸犯科,逃入都护城邑。即便十恶不赦之重罪,国主亦不可派兵入城缉拿。当由大使馆,通报详情,转呈国书。再由都护府下令捉拿。若各国民人,于都护城邑内犯法,则由都护府兵,亲自捉拿归案。各国不得包庇。
凡各国民人,合法依规,落户都护城邑。各国主皆不可强留。同理,若有都护治下民人,迁入各国,都护府亦大开方便之门。
各项律令,西域人尽皆知。
岭南亦如此。
岭南都护府,治融氏县。南醴、南廉二港,并榑木城、九津港,皆为都护府所辖。十万大山,内中百姓,拖家带口,日有百户乃是千户来投。各国主听之任之,乐见其成。
只因种辈众多,山中地少。常为衣食而起争斗,时出人命。不如放走,自谋生路。
单十万大山,便深藏百万之众。可想而知,民生艰难,绝非危言耸听。
万幸。山中颇有谷地,亦多蔬果充饥。终不至饿死。然若比南醴、南廉港中船户,可谓云泥之别。蓟王立司炎馆,分融氏县。将十万大山,包含其中。筑路通渠,营城圩田。再加坐拥内外循坏水路之便。便是百万民众,齐出大山。亦足可自养。
蓟国稻作季季大熟。海外寄田,亦渐止损。何愁缺衣少食。
1。192 夫子之墙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塞北草原,八月飞雪。蓟国虽在关外,十月已落雪大。更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蓟国横亘幽冀,燕山便在国界之北。可想而知,“地僻寒来早,高山月上迟”。
脚下冻土,坚如磐石,不利凿渠。冬季施工,多筑堤锁水,营造楼宇。九横十纵,临乡渠不急施工。先分街衢,再造楼宇。城外多有框架立起。一夜风雪,素裹银装,望之白皑。内中匠人,按部就班,营造不歇。待来年春暖花开,冰雪消融。一座座高楼广厦,已拔地而起。而后再掘环渠,立水门,只等水到渠成。
蓟国营城术,集墨门之大成,其中许多独具匠心之特殊构造,如:柱础浮搁、榫卯连接、斗栱梁柱等,皆是独创。据后世测试,十级地震,大殿仍屹立不倒。尤其砖木结构,木质框架,辅以空心砖墙,硬质瓦当。坚固耐用。空心砖内填充之物,亦历经多代。最初多为白垩灰浆。中期又填充铜铁矿渣,最近悉数改为珍珠釉浆。坚固、保暖二相宜。
汉时楼阁高耸,除去汉人以高为贵,以高为极。亦因林多巨木。木质坚韧,足可支撑。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平地”乃高楼之基。老子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自春秋,“殿基高巨之风”,日益兴盛。及两汉,高台之风鼎盛。除“仙人好楼居”,引人遐想。更有“置酒高会”。一语道尽,汉家风尚。
奈何时过境迁。汉时楼台皆焚毁,片瓦无存。唯剩台基,千年犹在。
元人李好问,曾述亲眼所见:“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何如?”
仅仰望台基,便使人“神志森竦”。可想而知,于其上再建百尺危楼,可仰摘星辰乎?
大衍之都,九十街衢。然蓟王宫,不过一衢。九十衢一,何来僭越。
比照王都,五尹联名上疏,国中雄城,可扩横竖九里乎?
蓟国雄城,多横竖七里。余城郭之外,再四面再各扩一里。不建城墙,只凿郭渠。立郭门(桥头堡)守备。如此,足有九九八十一衢。足纳编户五万余,近四十万口。再加客庸,足有五十万众。
五尹之意,蓟王如何能不知。只需凿穿环渠,郭外一里,濒渠之地,即可辟为港、市。客庸就近栖身,不必居于城内。如此蓟人与客庸,泾渭分明。诸多便利。
一道高墙分内外。如同陇山隔断华夷。心中若起高墙,蓟国兼容并包,和合之风,终将散尽。
于是蓟王将五尹上疏,束之高阁。王曰:再议。待客庸皆为蓟人。城内无法容纳,再外扩不迟。如今东境民人稀少。大通分户远未足够。尤其东境,不毛之地,处处皆需人手。国中不易大兴土木,分散劳力。故蓟王御笔朱批,再议。
五尹相约,鸾栖馆小酌。
恰逢南閤祭酒许攸,并报馆丞陈琳亦在。谚曰:“相请不如偶遇”。众人并席共饮。
席间,五尹求问,王上何意?
许攸笑答,诸君所请,时机未至也。这便将前后诸情,细细道来。五尹这便醒悟。蓟王所虑,乃是“一墙之隔”。
许攸言,一墙之隔,宛若春秋。我主所虑,人情冷暖。
五尹拜服。
许攸又道,诸君联名上此疏,主公当可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