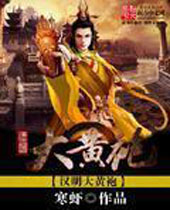汉明-第20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的家风,如果能养出一个不忠之人来,那才叫怪事。
既然已知生死,便能泰然处之。
占领仪真之后,钱家叔侄再不忌惮任何,他们直接率兵从周边富人、百姓处掠夺一切用得到的物资,并对仪真小城进行临时加固。
唯一与鞑子有所区别的是,钱肃典以他的将军印,在一张张白条上盖印,声明战后由庆泰朝廷对其进行补偿。
这种事情,如果换在以前,钱家叔侄是打死不为、不敢为之的。
可现在,他们做得非常决绝。
没有办法,王之仁水师支援他们暂时突破清军江防登陆,已经是极限,除了必须携带的军械,明军所带粮草只够三日,自此之后,没有援军,没有补给。
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将血流干,要么降清。
可钱家叔侄能降吗,敢降吗,愿降吗?
人,都是逼出来的。
一支军队,有什么的主将,就是什么样的做为。
主将身先士卒,欲杀身成仁,部下再差也差不了哪去。
三天的紧张备战,仪真这个小小县城,已经成为了一个堡垒。
血战在第四天午后,暴发了。
吴三桂武举人出身,后以父荫为都督指挥。
可以说他的一生,十之七八都是在战场上渡过的。
打仗,对于他来说,如同人每天要喝水一般从容。
不需要特别的筹划,攻这么一个小县城,在他看来就是举手之劳。
既然决定以这二万明军的血来换自己获得清廷的信任,吴三桂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四面包围,水泄不通。
吴三桂下令,四面同时强攻,欲迅速解决仪真战事,为自己去西北单独领军,奠定扎实的基础。
可仅仅半天时间,吴三桂发现他错了。
这支明军,不是他印象中一战即溃的明军。
战况紧急之时,无数人影从城墙上落下,这其中不仅是明军,还有清军。
敢于抱着清兵跃下城墙、同归于尽的明军还是自己印象中的明军吗?
如果仅仅是个例,这不稀奇,就算是再烂的军队,也找得出几个血性之人。
可每面城墙都出现这种决绝的抵抗,这让吴三桂不得不收起了心中的轻狂,他下令罢战,开始想要郑重筹划接下去的攻势了。
第四百六十四章 干掉了李国翰
树欲静而风不止。
吴三桂虽为主帅,身边却有一个李国翰在。
李国翰,看这名字象是汉人,没错,他是汉人,可他是铁岭卫清河、汉军镶蓝旗人。
打小起他就没认为自己不是旗人。
铁杆子的汉奸,说的,就是这种人。
他的升迁,来自于他的勇猛作战,作战对象自然是明军。
可以说,他能到今日高位,就是用明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
他的官位确实比不上吴三桂,明摆着的嘛,一个是王爵,而李国翰只是个固山额真,一等世职昂邦章京(相当于总兵)。
但李国翰是多尔衮心腹。
仅这一条就足够了。
所谓丞相门房三品官,吴三桂一个降臣,能奈他何?
吴三桂的暂时罢战命令,被李国翰强硬驳回。
说来可笑,一个主帅,且是清廷册封的平西王,他的命令仅被一个固山额真驳回,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可事实就是发生了,而吴三桂竟默认了。
当然,李国翰的在旗身份,足以让他在江北清军中享有特别礼遇,不象吴三桂,他的身份被清军嗤之以鼻。
这不奇怪,无论是明还是清,军中向来尊崇强者,对于降将,向来都是蔑视的。
军令如山,这四个字对降将不适用。
固山额真,是清廷军事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势与地位很高。
就军队而言,他们有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诸贝勒常须与八固山额真商议。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
另外,八固山额真有出师行围之权,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最后八固山额真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弁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
所以,在清军中,李国翰的话还真比吴三桂的命令来得管用。
李国翰倒不是狂妄,只是他临来时,得多尔衮面授机宜,知道多尔衮要三日之内荡平仪真明军的原因。
所以,暂时罢战,这绝对无法容忍。
吴三桂心中要说不气,那肯定不是真的。
虽说默认了李国翰的作为,但吴三桂由此也不再发声,任由李国翰对各部清军发号施令。
其实吴三桂在经之前半日的攻城,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城中明军悍不畏死,加上城中兵力雄厚,速战速决,根本不可能。
这是他下令暂时罢战的主要原因,在吴三桂的想法中,既然仪真已经被四面合围,只要包围半月一月的,待城中粮草消耗殆尽之后,清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复仪真,岂不是美事?
可李国翰的强横无状,让吴三桂袖手旁观。
次日凌晨,血战再起。
依旧是四面同时强攻,彪悍的李国翰在北城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加入先登。
此战惨烈,不仅是明军,清军一样悍不畏死。
这种血腥的肉搏,就算象吴三桂这样身经百战的宿将都为之动容。
此战一直持续到天色将黑。
四处城门都数度易手,尤以北门为最。
北门清军集中了六架攻城车,明军每以火油焚毁一架,便有另一架补充上前。
李国翰身着重甲,率百名先登,三次登上城墙,可每次都被钱翘恭率机动队逼下城来。
说起来李国翰也是幸运,仪真是个小城,城墙不高,每次被明军逼退,从城墙上直接下来,都被下面清军以软物相接,竟无一丝伤痕。
否则换作是苏州或者是镇江城墙,恐怕早就摔个残废,搞不好就一命呜乎了。
可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的。
所谓事不过三嘛。
已经三次登上城墙的李国翰意犹未尽,打算在收兵之前再攻一次。
这就是他命该绝了。
钱翘恭年轻,脑瓜子灵,他从吴争处听过江阴百姓是如何破解清军重甲兵攻城的。
其实从第二次起,钱翘恭就已经在策划破敌重甲兵之法。
可问题是,江阴百姓破解之法很难复制,要引诱重甲兵仰头露出脖子,这很困难,而且一旦被敌人发现自己的图谋,那就彻底失去了机会。
所以,钱翘恭非常谨慎,要么不击,一击必杀。
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天色将暗,李国翰临了还要发动一次进攻,等于给自己挖了个再也跳不起来的坑。
这时的人,大多都有夜盲症,或轻或重罢了。
对于突然出现的光亮,非常敏感。
加上天色将暗,这种突然出现的光这会使人下意识地转头或者仰头去看。
钱翘恭就是抓住这一点,在李国翰再次发动进攻时,点燃了早已备下的烟火。
瞬间绽放的光亮,让清军先登百多人齐齐仰头观望。
而在这一瞬间,交战中的钱翘恭率部同时滚倒在敌人面前,仰面以下刺上,将刀尖扎进了敌人的喉咙,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个简单的滚倒一刺,钱翘恭带着数百人只练了几遍,竟然一招见效。
有近一半的重甲兵,由此倒在血泊中,而李国翰就是其一个。
他是这场攻防战中,清廷折损官位、军职最高的。
一个固山额真死于这场莫名其妙的战斗,这无论是对战争态势还是清朝廷,那都是一种剧烈的震动。
清廷总共就八个固山额真啊。
他的死,同时也使得仪真明军,因此陷入更惨烈的血战。
这是常理,清军必须报复,吴三桂敢阻止吗?
绝对不能,这要是阻止了,他就背上黑锅了,要随江北清军铺天盖地的怒火。
吴三桂虽说因明军杀死了李国翰,重新取得了江北清军的控制权,可吴三桂知道,李国翰的死会让他背上莫须有的罪名,仅一条与明军暗通款曲的猜疑,就能置他于绝境。
第四百六十五章 血战镇江城(一)
ps:感谢书友“无事闲飞”、“凤凰劫”投的月票。
吴三桂必须自证清白,而自证清白最直接的法子,那就是全歼仪真明军。
由此,吴三桂开始全力出手了。
他下令连夜无休止地对仪真城进行猛攻,不死不休!
吴三桂之前就知道这是除围死明军之外,第二个歼灭明军的法子。
如果之前吴三桂尚有一丝未泯的香火之情,那么此时,他已经摒弃“和善”的歼灭明军策略,选择了凶残而简单有效的方法。
拼消耗嘛,毕竟清军数倍于明军。
可这法子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夜晚攻城,双方的伤亡都会增加,可现在吴三桂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死道友不死贫道,只要让他摆脱李国翰战死的阴影,他现在,什么都做得出来。
可就在清军疯狂进攻仪真城的时候,从江心岛传来明军击溃了丹徒守军,占领丹徒的急报。
吴三桂震惊之余,调集二万人连夜登陆江心岛,并下令与江心岛驻防清军会师,急攻丹徒,同时不得不派人向清廷据实奏报战况。
这个军报关系太大了,就算是吴三桂也抗不下。
丹徒是江北清军经江心岛与镇江联系的唯一通道,如果丹徒被占,通道被截断,那么镇江清军就是支孤军。
这恐怕连战前的状态都保不住,镇江城必失。
所以,这个罪责,吴三桂抗不了,也不愿意抗,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的嫡系还在北方待命,自己不过被临时捉差,来打打酱油的,这么重大的干系,自己凭嘛担?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关己屁事?
……。
仪真之战如火如荼。
丹徒更不例外。
江心岛清军虽说不多,但是八千精锐之师。
与吴三桂增派的二万清军会师之后,以铺天盖地辗压之势,扑向丹徒这个小城。
如果说仪真明军还有三天多时间准备防御,那么夏完淳部只有短短的半天。
所以,丹徒之战的明人伤亡,远甚于仪真。
这没有说错,虽说钱家叔侄领二万多明军固守仪真,可他们在整备防御之时,已经遣散了仪真百姓。
这出于两种考虑,一是钱家叔侄已经明白自己此战凶多吉少,而明军也不可能继续向仪真增兵,也就是说不管守不守得了,仪真最后都会被清军占领,无非是拖延江北清军时间长短罢了。清军残暴屠杀已世人皆知,能少死些人总是好的,百姓苦,何必将他们拖累?
二则,仪真已经被清军占领日久,谁能保证城中百姓不会向清军暗通款曲?
所以,遣散百姓,收拢物资,封锁城门,都是必要的。
那么,就算整支明军全部阵亡,伤亡人数也是个定值,不会超过过江明军的总数。
可丹徒却不一样,虽说一直是清军占据着镇江城,可镇江府各县却是在庆泰朝手里,乃至各县官员,那也是明臣。
夏完淳占领失守没几日的丹徒,百姓自然壶浆塞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
而夏完淳也没有时间去疏散民众,面对江心岛清军疯狂反扑,直接就封锁了城门,于是这场战役的残酷在于,无数城中百姓在协助明军守城的战斗中伤亡。
没有准确的数字,只是战后,夏完淳重伤,一万建阳卫仅剩一千八百人,而丹徒城中,说家家披孝,十室六、七空,一点都不夸张,可见战斗之惨烈。
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管是仪真,还是丹徒。
在此时吴争的眼中,那就是两颗棋子。
倒不是说吴争的心肠已经狠到六亲不认的境地,而是经历了死里逃生的吴争,明白在这个乱世中的生存法则,仁和善已经不适用了,唯有铁血方能生存。
对别人狠,对自己亦狠。
以五千骑和三千多步兵,就敢想与五千八旗骑兵硬撼,虽说最后确实是成功了,但这种做法,确实够狠。
哪怕在崇祯朝,以数万明军要全歼清一支五千骑兵,那也是鲜有前例的。
当时明军能歼灭一、二千清骑,那就是举朝庆贺的大捷了。
可这还不算狠。
狠的是,吴争在丹阳全歼清骑之后,义无反顾地率部北上,去进攻一个尚有一万多清军精锐的镇江城。
这确实有点疯狂。
这就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
赌清军不敢象自己一样,孤注一掷,出城迎战。
有句话说得好,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清军占着镇江城,且已经占据了一年多,那就是穿鞋的,他们需要防守四面,就算集中最大的兵力于一面,他们也得防备城中明人百姓趁机反抗,所以,兵力分散是肯定的。
而吴争如同前去“打劫”,是光脚的,可以无所顾忌地集中一面、一处、一点,进行攻击,只要清军不敢出城迎战,那么就算攻城失利,只要想撤,完全撤得了。
这就是双方的优劣态势。
三场战役,同时进行着。
仪真最先,丹徒其次,镇江城最后。
可战斗结束,却是反向排列。
镇江最早,丹徒其次,而仪真一直持续到战争嘎然而至。
吴争一样打得很辛苦。
三天之中,镇江城南门,被明军十六门火炮轮番施虐。
单就城门,已经换了四次。
最后清军开始拆除北门城门,运至南城安上。
而城墙上,清军的火炮同样也砸毁了明军七门火炮。
说它是砸毁,而不是炸毁,那是因为实心弹不具有爆炸力。
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