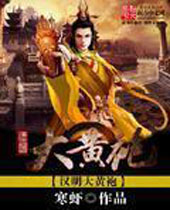汉明-第4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气势,也没谁了,豪迈得紧。
他这话一出,边上那几人就笑开了花,齐声道:“对,对,是得郑一斤请吃酒……同去,同去。”
那郑一斤大眼一瞪,“去去去……我说是请小郎倌吃酒,可没说请你们,那散了吧,做活去。”
许老二又挤怼道:“做啥活啊……官兵都围了四五天了,连个人都进不来,哪有活?我说郑一斤,你要是心疼铜钱就是说……那小郎可说了,他请。”
吴争心里有些奇怪,于是开口道:“都去吧……在下带了银子,请得起。”
那郑一斤霍地回头,瞪着吴争道:“打我脸呢?”
没等吴争回答,他又转头指着那三人骂道:“就你们几个杀才吃货,不做活就想着吃……得,今日我郑一斤豁出去请了,走,上刘老三的酒馆吃酒去。”
吴争三人,被这五人簇拥着,走向街道不远的酒馆,可心里是真奇怪了,这些人怎么也没法和乱民牵扯到一起。
能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外地人,如此热情。
为了顾及京城人的面子,死撑着请人吃酒,说明这些人的心里,还是自豪于自己是个京城人的。
心里奇怪着,转眼就到了郑一斤口中嚷的刘老三的酒馆。
两层的小楼,可酒馆仅一间,这一间也忒小了些,门面最多不过两米,准确地说,是一间门面生生劈来了两半,另一半上着门板。
若不是屋檐下斜挑着一面三角酒旗,上书“徐记酒馆”四个风一吹就倒的字,吴争是真没法想象这也叫酒馆?和皇城周边的酒馆比,那真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酒馆里光线暗得如同傍晚,连盏灯都没点。
一进门,一股浓浓的腥味扑面而来,里面就能放下三张桌子,那桌子已经找不出它原来木头的颜色,黑乎乎、滑腻腻,哪是一个“惨”字了得?
若是平日,吴争宁可是趴在河边喝口河水,也不敢进这种酒馆来喝酒。
郑一斤自来熟地一进门就大嗓门喝道:“刘老三……刘老三,生意上门了,还不下来招呼?狗x的不会在楼上藏了个娘们吧……再不下来,我可上来了掀被窝了!”
“你敢上楼梯一步,信不信我一刀剁了你?”声音不大,但话语却狠的声音传来。
说来也怪,从开始咋乎到现在的郑一斤怂了。
他没有一丝犹豫地收回已经踏上第一级楼梯的脚,“嘿嘿”尬笑道,“徐老三,我可是来照顾你生意的。”
一张清秀的青年男子面孔从楼梯处出现,身上长袍虽说打了几个补丁,可没有人会说它不是长袍。
“郑一斤,你家里可有五张嘴等着喂,别不知从哪得了几个铜钱就得瑟……先把一两二钱酒钱还了再说。”
郑一斤顿时脸色赤红,呐呐道:“今日我请人吃酒,现钱……欠帐来日再还,少不了你的。”
“店小本薄,请回吧。”淡淡地一句,那张脸缩了回去。
“别……别介呀。”郑一斤急得嚷道。
吴争此时开口道:“店家何苦逼迫……这位大哥的欠帐,我替他还了。”
郑一斤一愣,刚要开口拒绝。
此时,那缩回去的脸,又转了出来。
他倒没有搭理吴争,而是冲着郑一斤道:“你平日靠力气做活赚钱养家糊口,怎么……改行行骗了?”
郑一斤急得连连摇手道:“没,没有的事,我哪能做那种事?”
吴争有些不耐了,开口道:“店家开门做生意,哪有将客人拒之门外的?我不少你酒钱,尽管上酒菜便是。”
那张脸终于正眼打量了一下吴争,没有说话,但人总算是走下来了。
他冲着后面喊了一声,“二娃子,出来招呼客人。”
喊了两遍,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擦着腥松的睡眼,嘟哝着出来。
吴争笑着招呼同来五人入座。
一会儿,那男孩一手拎着个锡壶,一手捏着一叠陶碗,走到桌前,“咚”地往桌上重重一放,就走了。
吴争道:“店家,喝酒总得上两下酒菜吧?店里有什么好的,尽管上来就是。”
那徐老三这次很配合,冲着后面喝道:“二娃子,找些下酒菜端上来。”
郑一斤俨然一副主人样,分配好酒碗,还在各人面前的碗里斟好了酒。
“来,小郎倌,见面有缘,算是给你接风了。”
吴争微笑着端碗,岳小林、鲁进财突然伸手阻止,“少爷,这碗也忒脏了。”
第九百六十二章 阁下是官吧
郑一斤眼一瞪,一抬手,就饮光了碗中酒,将碗重重往桌上一顿,看着吴争。
另外几人也是脸色不善,将酒一口喝完,看着吴争。
只有许老二端着碗微笑道:“小郎怕是出身富贵……不喝也罢。”
吴争抬手轻轻划开岳小林、鲁进财的手,对二人笑道:“无妨,入乡随俗嘛。”
说完端起碗来,喝了一口。
那徐老三远远看着吴争喝酒,脸色有些微微变动。
哪想,这一口差点让吴争吐出来,这哪是酒,分明是醋,酸得让人掉牙。
这下吴争是真升起一股怒意,沉着脸喝道:“店家,你卖的这也叫酒吗?”
岳小林、鲁进财疑惑地慢慢尝了一口,顿时“噌”地起身,手按向腰间。
徐老三目光闪烁,他慢慢走上前来,平静地说道:“乡野地方,有得喝就不错了。客官若是想喝好的,可以去长安街。”
郑一斤等人也劝道:“小郎莫生气,这不怪徐老三,官兵在外围着,货物都运不进来,这酒坛一开,天气炎热,自然就酸了……好在总是酒,喝不坏肚子,将就着也就是了。”
这时,那二娃子端着二碟下酒菜,吴争撇了一眼,敢情,郑一斤没说假话,一碟炒豆,没放油的那种干炒,一碟盐水煮豆。
吴争这下真是哭笑不得,慢慢坐了下来。
岳小林、鲁进财随着慢慢坐下。
郑一斤陪笑着道:“小郎来得不是时候,这要是早些天,这酒还酸不了,还有那玄武湖的鲜鱼,少不得为小郎做上一顿醋鱼、蒸鱼、煎鱼……。”
说着说着,郑一斤自己咽了口唾沫。
许老二在边上招呼道:“来,来,吃酒,吃酒。”
吴争实在喝不下这酒了,于是抓了把炒豆,分给岳小林、鲁进财,算是陪吃了。
这时,边上店家刘老三突然开口道:“阁下是官吧?”
这话一出,所有动作都停顿了。
吴争确实一惊,看着刘老三,笑问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一阵寂静之后,郑一斤率先跳将起来,瞪着吴争道:“敢情你是来刺探消息的吧?”
许老二等人也是目光中带着敌意。
刘老三上前两步,走近吴争,道:“外面禁军包围得如同铁桶,进来一人已是不能,可你们三人就这么施施然进来,就足以说明你是官。”
吴争依旧微笑着问道:“但也可以解释为,我来此地寻亲,用银子买通了官兵,然后大大方方地进来啊。”
刘老三道:“所以我没有当即点穿,只是怀疑。可这二人起身时按向腰间,显然是带了刀吧?你会说他们只是随从,可官兵或许会为了银子放你进来,却不会为了银子,在这风口浪尖,放带刀者进来吧?”
吴争哈哈大笑,道:“店家好眼力,我确实是官,本官给事中吴越,这是朝廷行文。”
说着,又将份糊弄过禁军百户的文书往桌上一拍。
郑一斤拿起行文,上下翻弄了两下,递给了刘老三。
敢情,他不认识字。
刘老三接过,看了看,递还给吴争,拱手道:“原来是吴大人,只是不知道吴大人乔装打扮,前来鱼市街何为?”
吴争道:“奉朝廷之命,前来安抚民众。”
“安抚民众,用不着藏头藏尾吧?”
“那你认为本官是来对百姓不利的?本官此行就这三人,就算想对百姓不利,也是不能吧?”
这话有道理,让郑一斤等人脸色稍稍缓和起来。
刘老三突然问道:“听大人说话口音,应该是绍兴府人吧?”
“对,你猜得没错。”
“大人姓吴,与会稽郡王可有关系?”
吴争一愣,随即答道:“我和王爷是同乡,两家相邻不到二里地。”
“这么说,大人与会稽郡王能联络得上?”
“当然,此次入京,我就是做为王爷随从来的,在朝廷让王爷暂时总理朝政之后,王爷任命我为给事中,处置北门桥民众之事。”
“如何处置?”
“有理说理、无理鞭挞、违法缉捕、欠债还钱!”
这十六个字,浅显易懂,实为人间至理。
刘老三精神一振,首次激动起来,“大人所言当真?”
“当真!”吴争沉重应道。
刘老三突然屈膝跪在吴争面前,磕拜道:“学生有冤屈在身,要出首户部郎中陈仲奎欺诈钱财、鱼肉百姓、逼死人命,请大人主持公道!”
这一幕太出乎吴争意料,愣了半晌,吴争伸手搀扶道:“你是生员?”
此时的秀才,是功名,寻常人可不敢自称“学生”。
刘老三不肯起身,他一脸木然道:“学生刘元,崇祯十六年的生员。”
“你先起身,坐下好好说,真有冤屈,本官定替人作主。”吴争皱眉,手上使了些劲。
若是平常,吴争不爱搭理这种事,这天下本就没有什么绝对公平可言,真要管世间所有事,就算自己化身千万,怕也忙不过来。
要治根,还得重新建立有效可行制度、法律。
但此时,吴争本就为了乱民之事前来,加上郑一斤等人这么“热情”地招待,吴争倒也愿意听听刘元究竟有何冤屈。
刘元显然不象郑三斤等人粗犷有力,就象他自己说的,只是个手无缚鸡的书生,被吴争一使劲,抗不住了,这才起身坐下,慢慢说了起来。
然而他的脸上依旧一片木然,完全没有任何激动或者激愤,就象是在说别人家的事一般。
刘元家原本在西城三山门一带,家底也算盈实。
刘家三子,两兄早亡,仅余刘元一子,家中有一座约二亩院子,一座祖宅,二十亩水田(江南水田那可是实打实的不动产),还有两间铺面,经营些日常百货杂物,日子也过得安生。
两年前,户部开设钱庄,以二成高利息(月息)吸引储户。
刘元他爹拿着家中积余大概二百五十两银子存入,每月可支取五两的利息。
五两可不是个小数目,京军一月的饷银原本才一两,后来被吴争的北伐军一比对,才增加至二两(但士兵拿到手的,最多才一两二、三钱),也就是说,这利息可以抵得上近三个成年劳动力了。
第九百六十三章 骗局
这原本应该算是好事,坊间百姓纷纷称赞朝廷与民福祉。s
半年之后,户部钱庄开始增加利息,从二成开始加,几乎每月都加,三个月后,利息已加到了三成,还在加。
这原本也是好事,民众可以得到暴利嘛。
可问题是,每一次加息,过往已经存入的银子,不享受这待遇。
这也有理,签下的契约,一般都是两、三年才返还本金,没到时间,自然不能提前取出。
但在民众心里,那种煎熬是不可估量的。
试想,半年前存入的银子,和半年后存入的银子,数量相同,利息却低了一倍。
这可是现银啊。
钱庄里的人对外称,只要继续存入银子,就能享受到更高的利息。
百姓们听了心中百爪火燎一般,可谓夜夜辗转反侧。
家中的银子存完了,于是开始从亲朋好友处借。
刚开始还行,借得到,可没多久,借不到了。
谁也不傻,听到有如此获利丰厚的事,怎么可能借钱?
不用说亲朋好友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借,自己不会存哪?
就在百姓们走街窜巷,到处寻钱之时。 s
有一家银号出现了,但它不是钱庄,只是银号,不吸储,只放贷。
可谓天公作美,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啊。
银号的掌柜,甚至被人称为大善人。
因为银号放出的银子,利息还真不高,月息二成,这相较于户部钱庄三成多的利息,那就算是散财童子了。
因为从银号借一百两,每月支付二两月息,可转存到户部钱庄,每月可得三两多的月息,这转转手,一百两本金,就能凭空赚得一两多的息差,就算许多百姓目不识丁,可这简单的算术,还是算得出来的。
于是,百姓趋之者众,刘元他爹也是其中之一。
可银号也不是平白就放贷的,它有个规定,就是需要抵押。
抵押物只收房屋、田产,且抵押比很低,仅按价值的四折,也就是说,一百两的田能抵押出四十两。
去存钱时,不会给你抵押物,去借钱时,非有抵押物不可,世事就是如此!
而且,每笔借贷,时限都是六个月,最多不超过一年,也就是说,到期还不出,抵押物就是银号的。
其实,到这份上,稍微聪明些的人都知道风险在哪了。s
户部钱庄的契约是两年起,可银号高利贷最多一年,那一年后,拿什么还?
所以,除了一些胆大的百姓,少量借贷之外,没多少人借贷。
这时候,户部钱庄确实急人所急,立马出了一个告示,钱庄即日起,存银契约可从一年起。
于是,民众惊喜起来,纷纷跑向银号借贷。
而银号这时也稍稍变了些规矩,那就是只借贷半年的,若要借一年也成,抵押物只按三成计,也就是说一百两只贷三十两。
两厢规则一变,就有了转圆的余地。
聪明人,特别是自恃聪明的人,算出了可钻的空子。
于是,涌向银号开始借贷。
开始时,银号放出的确实是真金白银,民众借到后,再转存进户部钱庄。
可后来,银号不再放银了,只是一张盖有印章的条子,民众拿到手后,往户部钱庄一递,就当是银子用了。
民众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方便,试想几百两、甚至上千两,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