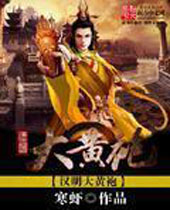汉明-第76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利益诉求的不同,此时各人的屁股决定着他们的脑袋。
多尔博又离席回了内院,他得向他姐姐东莪问策了。
最后,反倒是不识兵法的东莪,给出了她的建议,那就是所有建议都采纳。
病急尚能乱投医,乱拳也能打死老师父,只要是个法子,用用就是了。
于是,滋阳缇骑四出,一面向清廷求援,当然,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求援,一面向凤阳府求援,甚至还派出了一路去联系海州,请求停战议和,这,怕也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再说了。
天晓得,阿济格此时自身难保,除非允许他率军撤向徐州,仅要他派援兵,那估计是与虎谋皮了。
而最能说服多尔博的,就是东莪提出,多尔博“亲征”,而且是带着东莪自己的“亲征”。
东莪的意思是,只要两军遭遇,东莪愿意替多尔博说降沈致远,从而避免一场不该有的战争。
多尔博欣然采纳了东莪的谏言,在他看来,还是“以和为贵”啊!
……。
沭河之上,无数艘渡船争渡。
密密麻麻地人群中,一队军服不同的游骑在四处徘徊着。
没有人去理会他们,也没有人去制止他们。
直到这队游骑自觉无趣,悻然离开。
“将军? 为何不……杀了他们?”一名副将疑惑地向沈致远问道。
沈致远放在手中望远镜? 往副将手中一丢,“不值当? 留下他们? 鄂硕必会清醒过来,让他们回去? 鄂硕反而搞不明白我真正的意图。”
“将军英明!”
“少拍马屁。”沈致远指着正在忙着渡河的军队,问道? “没人质疑本将军令吧?”
“将军放心? 各营将领都已经知会过了,无人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将军一手提携的,怎会质疑将军军令?况且,谁不明白如今北伐军已经掌控战局……没人想以卵击石!”
沈致远点点头道“如此甚好……传令下去? 前锋一旦渡河? 迅速向占据莒南十字路,配合莒州方向,对安东卫形成夹击之势。”
“是……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等等……再重复一遍,记住,只包围? 不进攻。”
“可……若对方先动手呢?”
沈致远轻哼道“那就……歼灭!”
“遵命。”
……。
可沈致远无法预料到,鄂硕会在南下途中? 调安东卫余部大军向莒南方向运动。
这就造成两军前锋,几乎在同一时间? 在莒南方向正面遭遇。
毫无悬念,这时已经陷入无法善了的局面? 两军随即不约而同地向对方发起了进攻。
而这种正面交战? 无法象突袭可以迅速击溃对方? 战局一时陷入胶着。
之前沈致远和吴争所有的部署,都被打乱了。
不得已之下,沈致远只能先打好眼前这仗再说,他调莒州方向的偏师南下,两面夹击莒南清军。
可这样一来,莒州方向的“堵漏”就缺失了,鄂硕有了充裕的撤退时间和空间。
那边鄂硕接获急报之后,迅速派人向赣榆岳乐传讯,随即下令大军北撤。
而赣榆岳乐本就不看好凭自己一支孤军,能守住赣榆小城,听闻沈致远率叛军抄了自己后路,岳乐毫不犹豫地下令连夜北撤。
而城外鲁之域对赣榆城进行的是佯攻和骚扰,双方在两天之中,几乎没有正面交战,最多的只是相互炮击。
正因为如此,鲁之域无法在夜里发现城中守军已经撤退,直到天亮再发起一波佯攻时,才发现,敌人跑了,仅有的收获,就是岳乐撤退时留下的数十断后残兵。
但因吴争事先有过叮嘱,对敌驱赶为主,杀伤为辅,所以鲁之域并没有下令追击,而是派人知会钱翘恭,由风雷骑追击来扩大战果。
吴淞卫随即入城,赣榆光复!
……。
赣榆收复,昭示着北伐大门正式开启。
但不管是鲁之域的吴淞卫、泗州池二憨部、广信卫以及钱翘恭的风雷骑,皆已经精疲力尽,急需休整。
阿济格闻知岳乐向北撤至安东卫,便已经明白,东翼已经不可靠,他不得不改变原本想夺回泗州战术,开始正式思考向北寄人篱下,还是向西与吴三桂争夺陕甘的主导权。
而多尔博派人转道济南府,向安东卫鄂硕传讯——撤兵。
在莒南激战的沈致远接到吴争的命令,主动与莒南鄂硕部脱离接触,率军往南,进入淮安界,与刚刚收复赣榆的吴淞卫会师。
退回安东卫的鄂硕,在与岳乐商议之后,决定无视多尔博的命令,固守安东卫,同时由岳乐回京请援。
到了这个节点上,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休兵,战局由此进入了大战前的静默期。
……。
建兴二年,九月十五。
淮安城。
吴争以大将军名义,召开军机会议。
除了三个战场主将,建兴朝首辅黄道周代表皇帝朱莲壁,率团赶来参加会议,兵部、户部尚书及侍郎,左营廖仲平也在其中。
连新任招抚将军、衡阳卫指挥使的刘放,也列席了此会。
参与会议的人数高达二、三百人之巨。
只有和州庐州方向还在交战的夏完淳,因战事正酣、路途遥远没有赶来,派了一名副将做为代表。
这是后世史书记载的赫赫有名的“淮安会议”。
会议将这场局部的“报复”战争,正式定性为“北伐战争”。
既然是北伐战争,便是国战。
既然是国战,便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
齐心协力,共赴国难。
个人的利益,再不好拿到台面上来讲了,甚至群体利益也得为国战让位。
就此,不管是建兴朝,还是大将军府,对这场战争的各种不同声音,嘎然而止。
无数志士日思夜盼的王师北伐,在不经意之中到来了。
黄道周在会议上宣讲了皇帝的旨意,授吴王临机决断、专擅之权,总理北伐一切军政事宜。
吴争随即以大将军的名义,向建兴朝治下二十九府(包括大将军府所辖十三府)下达了征兵令,这征兵令与之前不同,这次是举国皆兵。
lt;scrptgt;;lt;/scrptgt;
第一千七百二十五章 混不吝的刘放
此次与会之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共识,这个时候,再无人去纠结穷兵黩武这四个字了,再无人敢据理力争,提出财力不足的理由了。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民族动员,就象吴争在会上说的,巨轮滚滚,谁敢挡路,必会被碾个粉碎!
但如果说与会者没有一丝杂音,其实是不准确的。
只是太多人,不得不将杂音放在了心里。
但也有混不吝的,譬如刘放这厮,就在会议尾声时,便向吴争“发难”了。
因他终于搞懂了“衡阳卫指挥使”的特殊性,这特殊确实太特殊了,特殊得让刘放原本刀都砍不进的脸皮,都烫得发红。
他也搞懂了“招抚将军”这不入流,让人忍俊不禁的封号,更明白了他正五品的军职,在这些声名赫赫、战功卓著的将领面前,显得那么的“卑微”。
刘放不服啊,他认为自己的军功足以青史留名、当受万人称颂。
于是,他向吴争发难了,当着所有与会者的面,包括他心服口服的池将军。
刘放是这么说的,“王爷你太欺负人了……三王啊,杀两擒一啊,刘某的功劳不管放在哪朝哪代,那都是得封王晋爵、被人竖大拇指的……区区五品指挥使,还有那……啧啧屁的招抚将军,刘某都没脸回去见人了……王爷,没您这么欺负人的!”
所有与会者的眼睛都看向吴争,他们在观察吴争的反应。
这里有追随吴争崛起的嫡系将领,也有半路投靠的将领,更有并非站队吴争这边的建兴朝官员和将领。
他们都在观察着吴争。
刘放只是个混混,这,谁都知道。
可他的功劳,确实太过“吓人”。
如果将功劳分拆开来,给予任何人,那么,求值有至少得多些几个王爷。
这不是一件个例事件,而是一个风向,政治的风向,决定着日后各个阶层、各个势力对权力的划分标准。
没有人怀疑,吴王殿下的权力? 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还有人怀疑吴王殿下的权力,那这人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不? 是脑子浸水了,而且浸了不是一天两天? 是一年半载了。
但吴王能封王吗?
当然不能,哪怕是封刘放一个郡王。
所有人都在观察着? 甚至有种吃瓜看戏、唯恐事情不大的阴暗心理。
确实? 吴争突然将此战定性为国战,伤及了许多人的利益。
或许,这也是对吴争“一手遮天”无声的反制吧。
……。
然而,让许多人都失望了。
吴争对刘放的“嚣张”并不为意。
不仅不为意? 反而当场宣布? 以大将军之名,晋刘放为昭勇将军。
这将军位可是正儿八经的将军位,正三品散阶。
同时,吴争以吴王王爵及临机专擅之权,授刘放轻车都尉? 从三品衔。
这样一来,加上原本刘放的衡阳卫实职? 可谓官、散、勋一应俱全了。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 刘放是再正经不过的建兴朝高级将领了。
所有人都惊讶了,这是吴争又一次颠覆了大明祖制? 而且更加肆无忌惮。
因为从太祖朱元璋始? 明律讲究得就是一个父子传承。
有道是“龙生龙? 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所有人,从祖辈起,就已入籍。
这个籍,不仅仅是指户籍,而包括职籍,如上、中、下九流,下九流衙差、梆、时妖、打狗、脚夫、高台、吹、马戏、娼妓,绝不能升为中九流。
中九流童仙、相命、郎中、丹青、隐士、琴棋、僧、道、尼,也绝不允许入上九流。
可谓层层泾渭分明。
所以,象一个衙役,听起来是个官差,但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官一样。
刘放出身下九流,不管是衡阳混混,还是巡检司差役,都不允许他成为一个正经官员。
这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可吴争,将这天壤之别一挥手,轻易击碎了,谁不在惊骇之余,意识到吴争的权势,已经离那位置,仅一步之遥了……不,其实就是一张纸。
正是这个原因,在吴争宣布晋升刘放之后,所有人都齐声称颂“王爷英明”,并“热情洋溢”地向刘放道贺,天晓得,许多人心里对刘放的那种鄙夷和轻视,如同对待一个“暴发户”一般的鄙夷和轻视。
刘放自然是不晓得的,晓得也不在乎。
至少他在当下,是满意的。
他觉得吴王殿下还是英明的,是个可以效忠的对象。
所以,原本想要从吴争这索要粮饱和装备、弹药的刘一手,居然在会后一声不吭,或许,这就是市井之人擅长的“投桃报李”吧。
……。
战争的性质改了,但实力和局势,不会因战争性质的改变而改变。
财政司依旧捉襟见肘。
军工坊的产量已经到了极限。
就算会后全民动员,新征的士兵,也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武器装备。
水师前往安南、沙捞越、文莱、吕宋的购粮船队,第一次返回,也只带来数十万石粮食。
而被吴争寄于厚望,派马士英前往巴蜀购粮,结果是李定国的婉言拒绝。
这倒不能怪李定国自私,而是大西军全军出动,它的体量,甚至比北伐军都要大,大将军府都不够吃食,大西军就更不能自足了。
李定国不派人来向吴争索要粮食,就已经算是体谅到吴争的难处了。
织造司的股份已经抛出,听说其中有一湖广富商,豪掷千万家财,独吞了织造司二成股份。
可银子不能马上变成粮食和武器,甚至大量地抛出,只会造成物价飞涨。
莫执念的银元计划已经实施,这事倒非常顺利,五百万银元,被建兴朝二十九府民众争相抢购,为此带来近二百万两的“盈利”,可还是无法消解财政司的饥渴。
如果说淮安会议是建兴朝举国转为北伐的里程碑,那么,实际上,这最多只是一次精神上的动员大会。
此时的吴争,什么都缺,粮食、布匹、铜铁等等,就没有不缺的。
而且这缺的物资,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三个方向,就象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喂饱了,长不大啊。
可来自文官一系的暗中掣肘,让吴争感到了一丝力不从心。
明着反对易防,暗着来,真心,累!
第一千七百二十六章 上紧箍咒
“王爷,吴淞卫急需休整……哪怕是十天半月,您亲眼所见,此次海州、赣榆二战之后,吴淞卫减员高达七千多人,急需补充兵力啊……再有,战后我军弹药奇缺,想要继续北上,火炮炮弹更须立即补充……王爷,末将并非虚言啊!”
鲁之域急了,他的四周,都是与他有着相同诉求的将领,谁的日子也不比谁好过。
这与战前,北伐军饷银、福利为世人称道截然不同,如今,从开战以来,除了最初一个月,军队两月没有发饷了。
而第一军从杭州府出发至吴淞口渡江,没有按旧例,拨付一两开拨银子。
李过更急,他赤红着眼睛,瞪着吴争道,“王爷,您不能厚此薄彼……当初您令我孤军入凤阳,又令我率广信卫强攻凤阳城……广信卫上下无不浴血奋战,攻临淮城时……城上血战,王爷想来应该知晓了……整整二千多条命哪……都是追随李某,从山西辗转数千里的老弟兄啊!”
池二憨一声不吭,脸色麻木地看着门外。
可史坤憋不住了,他朝李过、鲁之域怼道:“二位将军虽说言之不虚,可咱们第一军在盱眙、泗州打得可不比你们轻松,从天长转进盱眙时,总计不到六千兵力,在盱眙硬抗总计三万敌军,足足一月有余……你们伤亡不小,咱们伤亡更大……六千人,如今仅剩二千人,卑职想问问二位将军,该谁先补充?”
这话让鲁之域暂时闭上了嘴巴。
李过却不认同,他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