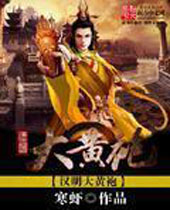汉明-第78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建兴当霸不霸!想之前北伐军二次北攻,每每遇见王师告捷之时,吴王殿下要么黑兵回师,要么与敌媾和……北伐六载不竟全功,想,多少人翘首以盼,却徒叹奈何……!”
这显然是有备而来啊,李颙吓得赶紧伸手去捂冒襄的嘴,一边忙着圆场,“王爷莫怪,辟疆他……怕是又灌了黄汤了。”
吴争的脸色阴沉到了要滴水的程度,但依旧扬了下手,“让他说,想来不说光了,他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李颙不得不放开冒襄的嘴巴,后退两步,可担忧的神色,一览无疑。
反观冒襄一脸平静,仿佛他方才是在对吴争歌功颂德一般,全然没有俯首请罪的觉悟。
“讲啊。”吴争不耐烦地催促道,“到了这时,反而怕了?”
冒襄哪是怕?
他舔了舔嘴唇,道:“若是王爷赏口茶润润嗓子……那就最好不过了。”
吴争差点想脱鞋子砸他脸上,可终究顾及自己王爷的身份,干咳一声,身后鲁进财瞪着牛眼,从侍女手中接过茶盏,上前几步,生硬地往冒襄面前一送。
力道用得大了些,有小半杯洒了,有些还溅到了冒襄的前襟上。
可冒襄浑然不觉,还笑着向鲁进财道了个谢,然后一仰头,也不管茶水是不是烫,就这么一口饮干了。
他身后的李颙紧张至极,他似乎明白了,华夏千古读书人,哪朝哪代都不乏以诤搏名之人,可,可冒襄他,不至于此啊!吴王殿下本就有用他之意,何须如此犯颜搏名?
吴争呵呵一声道:“好了,茶也饮了,嗓子该好使了吧?讲吧!”
“谢王爷赐茶。”冒襄一抹嘴巴,再次用他独有气势道,“天下谁人看不出,当今吴王殿下有登极之意,可王爷纵有王霸之梦,身边唯缺良臣谋国……今日今时王师北进,轻取徐州这千古兵家必争之地,若王爷一如之前,只为攻城掠地,岂非暴殄天物……?”
“本可豪取,偏要蚕食,此为谬误一也!本应当仁不让,偏偏瞻前顾后,此为谬误二也……!”冒襄就差扳着手指了,“敢问王爷,想太祖皇帝起于草莽,可问过天下人,为社稷正朔否?”
吴争这次听明白了,前半句是在指责自己前两次北伐,半途而废。
后半句,那是在劝进了。
又是一个想得从龙之功的读书人!
可冒襄这神色,怕是凶悍了些,这声音,怕是大了些,以至于鲁进财下意识地握紧刀把,向前半步,以至于吓得李颙面如土色,以至于门外扈卫悄悄将头伸至门边,向里探视。
“说完了?”吴争不动声色地问道。
“意犹未尽!”冒襄反倒气呼呼地道,仿佛他才是被指着鼻子骂的那个。
吴争挥了下手,示意鲁进财退后。
“既然讲完了,那就回答孤一个问题。”
“请王爷赐教。”
第一千七百七十章 冒襄自荐
“有道是书生空谈误国,孤想问问你,说了那么多,你心里可想好解决问题之法?”
“唯有一股作气,直捣黄龙!”冒襄不假思索地道,“灭国复土之功,足以彪悍青史……顺天府承天殿上大位,谁敢窥视与王爷相争?非王爷莫属!”
吴争轻嗤道:“此话,这些年孤听得多了,没什么新鲜的。”
冒襄回道:“王爷担心的,无非有三,一是西南永历会举兵讨伐吴王窃国,但以襄看来,永历帝苟延西南边陲数年光阴,若无吴王崛起起东南沿海,想来清军早已扫荡云贵,永历帝怕是早已西遁,既然永历几年前都难以与吴王争锋,今日此时,又何惧之有?”
“况且,晋王送世子、嫡女于杭州府,又与王爷有翁婿之义,真到了那时,想来晋王也见到了如今江浙之地繁荣富庶、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形,应该清楚永历与吴王之间不可忽视的差距了吧……如此,又何惧大西军之有?”
“王爷担心之二,为建兴帝、明室及江南百姓会举兵伐不义,但以襄看来,全不必担心,这六年间江南百姓知吴王而不知皇帝、知大将军府而不知有朝廷已是常情,就算建兴帝、明室不甘心就范,可朝廷所控的只是应天府周边及江北数府之地,江北之地,民心尚未收拢,号令反清尤勉为其难,何况反吴?”
“王爷担心之三,为王爷一旦登上大宝,永历、建兴二帝会联合讨伐,这就更加不堪了,襄断定,二者从属绝不超过十万之众,而十万乌合之众,岂能与王爷麾下虎贲争辉……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如此,吴王殿下明明手中握有宝玉,偏偏礼让再三,给了永历、建兴两朝君臣原本不该有的暇思,白白背了这恶名罢了……襄言尽于此,望王爷三思!”
听听,听听,多好的口才,不当说客简直是暴殄天物。
如果吴争不是个穿越者,恐怕就被他说动了。
吴争没有当明朝忠臣的想法,也没有逆来顺受的觉悟。
他的想法很简单,驱逐鞑虏、复汉衣冠,尽早结束这乱世,让华夏大地休养生息,以应对已经开始入侵大陆的东、西方外敌。
如果真要是再打一场内战,没有个三年五载根本不用想,还得死多少人?
死去的人口,至少又得二、三代繁衍生息才能补回,半甲子啊,能做多少事?
如果真能和平统一,为何要战?
仅仅是为了那个位置?
那位置真能生死人肉白骨?
还是坐上后能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
相反,吴争太清楚那位置的苦难了,被人为地圈禁在四方城里,受着内外臣子们的忽悠,如同一只笼中的鸟儿,哪有做一方诸侯来得快活?
只要扩大相权,将皇权进行约束,吴争认为做个新朝的诸侯,更符合自己的心意。
吴争一直在纠结,第一次见到冒襄时,这厮就劝进,如今无非是故伎重施罢了。
吴争问虽是问了,但心里早已有数,读书人嘛,指点江山罢了,真正要让冒襄实务,说出针对性的可行方法,那就难了。
果然,冒襄低下了头。
吴争呵呵笑着,想尽快结束这一次谈话。
不想,冒襄很快抬起头来,道:“吴王手中长林卫,襄久有耳闻,然宋安宋大人才疏学浅,不足以堪当重任,数年之中,持如此宝器却未竟全功,实令人扼腕叹息……襄向王爷厚颜自荐,领长林卫大档头一职,愿为北伐大业和王爷登极效犬马之劳!”
吴争愣住了,都说明末读书人胆大到厚颜无耻的地步,如今听冒襄一席话,吴争觉得“厚颜无耻”四个字说得太轻了。
吴争向来谨记“毛爷爷”那句“枪竿子里出政权”的话。
大将军府一应政权,皆可交托于人,唯一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而长林卫就是吴争在这世上最后的自保手段,怎能交给外人?
一开始时,吴争让莫氏一个女子掌管,无非也是为了放心。
之后宋安接手,吴争岂能不知宋安的才能,可不也是为了放心吗?
何况宋安这些年来,进步还是很快的,至少没办砸过什么大事,可塑性还是让吴争满意的。
如今冒襄这厮突然自荐向吴争要长林卫,这让吴争一时愣住了。
冒襄道:“这两年,襄急在心里啊……襄多年辗转于江北各府,对当地人情世故皆了然于胸,若是让襄主掌长林卫,襄可以向王爷立下军令状……南起长江,北至山海关,两年之内,长林卫在江北的景况可以让王爷耳目一新……同时,襄还可以为王爷策反清廷重臣!”
吴争沉默不语。
冒襄问道:“王爷可是不信襄?”
这话问的,让吴争都感觉不好意思了,但还是点头道:“你如何取信于本王?”
“襄家中还有老父健在,有妻苏氏、妾董氏,膝下一子二女,若王爷允准,襄可将阖家迁于杭州府,劳王爷照抚。”
吴争惊讶于冒襄的滴水不漏,这显然是早已有了准备的进谏。
吴争起身,来回走了几圈,抬头道:“孤不准。”
冒襄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的失望无以言表。
“既然如此,襄没话可说了……襄,告退!”
说着冒襄也不理李颙,甩袖转身。
“慢!”
身后传来吴争的声音,冒襄一喜,霍地转身,“王爷改主意了?”
吴争平静地:“你方才也说了,你的人脉皆在长江以北……这样,孤可以任命你为长林卫二档头,虽居宋安之下,但江北长林卫,皆隶属于你,孤另授你专擅之权,债权处置江北长林卫事宜,你意下如何?”
冒襄福至心灵,他双腿一曲,跪伏道:“臣,谢王爷提携之恩!”
李颙至此松了一口气,含笑上前,向冒襄拱手道喜,“恭喜辟疆兄才华得展!”
吴争挥了下手道:“滋阳大捷,宋安率部正阻击鳌拜所部,你的上任须此战之后……对兖州战局,你可有想法?”
第一千七百七十一章 商城危机
冒襄起身道:“滋阳大捷,兖州再无可与我军抗衡之敌,以襄之见,当令陈胜将军率部急速向北挺进,一来,增援宋安、钱翘恭二位将军,二来,若能击溃鳌拜所部,那进攻济南府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只要攻克济南,青州、莱州、登州三府就成了孤悬之地,光复指日可待。而就算陈、宋、钱三位将军无法击溃鳌拜所部,将战线稳固于济南府,那兖州也就是王爷囊中之物了,若清廷来交涉,哪怕是千百万黄白之物,也绝不还回去。”
吴争无语,他听出来冒襄又在隐指自己之前一战,将徐州换了银子之事。
不过吴争此时心里高兴,毕竟滋阳大捷嘛,想了想道:“陈胜所部北进,若东昌、大名二府清军东攻,滋阳就危险了。”
冒襄道:“王爷放心,东昌府仅三千清军,大名府多些,但也只六千人……这样,臣请前往大名府一行。”
“何意?”
“臣与大名府总兵有数面之缘,如今王师北攻至滋阳,应该可以说降。”
吴争问道,“可有地把握?”
“六成。”
“六成已可一试!”吴争指着鲁进财,对冒襄道,“孤让他带些人一路护送你去。”
冒襄忙摇摇手道:“不必多此一举……襄以白身入大名府,反而能避人耳目,也不会被人挡在门外,而陈将军北进,王爷要前往滋阳坐镇,岂可少了鲁大人在身边?”
吴争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点头道:“不必强求,若事不成,尽速返回,有孤坐镇滋阳,区区数千乌合之众,何惧之有?”
……。
然而,相较于北伐军这边高歌猛进,汝宁府那边李定国陷入了困境。
而且不是一般地困境。
李定国至商城才知剧变,他一面向永历禀报战况,希望调整既定战略目标,一面派人三路救援。
原本他是想守住商城,那么只是既定目标无法达到罢了,已经到手的果实能守住,毕竟大西军兵锋已经从湖广攻入汝宁府了。
可李定国没想到的是,阿济格会悍然大军强攻商城。
他更想不到的是,在岳阳临时驻跸的永历帝,竟迅速北上至武昌府,还在这一路上连发六道旨意,令李定国加紧北攻,一举攻下开封。
这不是开玩笑嘛,先不说大西军此时补给线漫长,身后湖广差不多被大西军“搜刮”干净了,十几万大军二千里奔袭,此时的大西军完全可以用“强弩之末”来形容了。
其实李定国的决策很英明,就该固守商城,哪怕阿济格疯狂强攻城池,那也是一场消耗战,大西军以城墙为凭恃,阿济格想速胜,那根本就不可能。
只要等到援军赶来,阿济格诸部被反分割、包围,也不是不可能。
可惜,永历帝朱由榔心性与崇祯雷同,属于“明君”之列。
典型的志大才疏。
这话说得或许有欠妥当,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好心,一定会办坏事。
皇帝亲至前线,可以激励士气,如果是精擅行伍的皇帝,那就更能临机决断指挥大军了。
可朱由榔打过仗吗?
虽说在这明末战乱之年,也吃过不少苦,在张献忠率大西军攻入湖南时,朱由榔跟着他爹桂端王朱常瀛颠沛流离,最终父子俩还是被大西军俘了,着实吃过不少苦头。
可他确实没那军事才能,你说好好地待在岳阳大后方,吃点喝点,哪怕是征些秀女,坐等李定国打完了再说嘛。
朱由榔偏不好这口,非要学亲历亲为,闻李定国战报之后,他坐不住了,圣驾亲征,大有君王死社稷的豪迈。
六道圣旨,敦促李定国北攻,这让李定国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
如果天高皇帝远,那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可皇帝已经移驾自己身后了,能不听吗?
不听就是抗旨,要杀头的。
李定国也不想数年扶明,到了落个不臣恶名,于是勉为其难,出城迎战阿济格了。
这就是一场灾难,与白文选、马维兴战败被俘截然不同。
白文选、马维兴是大意被伏战败,说是前后二万大军覆没,可死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大部分是四散溃逃,等战争结束,大部分还是能收拢的,而白文选、马维兴不幸被俘,清军已经不如五年前了,那时明军、义军将领被俘,十有被斩首,如今就连以强悍著称的阿济格下意识都不敢轻易杀俘。
只要战后换回来就是,当然,前提是二人在被俘期间不会降清。
可李定国眼下却不同,商城西、北两座城门被阿济格、孙可望包围,且敌军正向东门漫延,也就是说,真正可以与外联络的,仅剩南门。
这个时候出城迎战,既为降低守御实力,稍有不测,那就是城外城内连败。
当然,李定国也有不妥之处,他自恃有二百象兵,凭以往与清军的作战经验,清骑战马一见大象,大都会原地以蹄刨地、止足不前,那么,以此时城中一万骑兵,就有希望与阿济格主力一战,只要胜得一仗,不但商城之围可解,皇帝想要的攻开封府,未必不是幻想。
出于这种考虑,李定国定下了迎战之策。
连夜以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