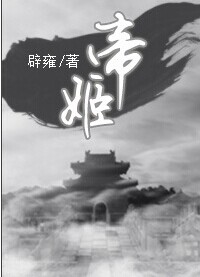帝姬-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然如此。”她说道。
“我看你这几日在这山野间忙得不亦乐乎,难道不是喜爱如此?”
她微微一滞,随即又取出一块根茎,半晌方道:“先生果然见微知著,传言您有通彻天地只能,您又知道些什么呢?”此言不无讽刺。
他伸手取下脸上覆着的书,向她看去,眸如寒星,目光透彻,似要将她看穿,“郡主通彻明达,但知与不知,何者更好,世人总是莫衷一是。”
这般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却令她心中一抖,脸色蓦白。
“人于世间总似提线木偶,区别只在线多线少罢了,”他却视而不见,只将道经合上,漫不经心地道,“正如我,最终仍是要出仕的,纵然我其实不愿。”
越青阳神色深含惊愕,她以为此行结果已定,却未料他竟然会应承,“你要出仕?那你一开始为何拒绝?”
他又靠回躺椅上,闲散道:“考验你们的诚意呀,世外高人不都如此,我若轻易答应不就显得太掉价了。”
越青阳:“……”
原本所有人都以为此行必定空手而返,谁知峰回路转,众人俱是兴奋不已,请得渊泽先生入朝,加上和阳郡主在御前美言几句,此事又是功劳一件,故以对回京皆是迫不及待。只除了越青阳,念及又要返抵无处不是桎梏的宫中,一阵怅然。
江渊泽应承出仕之后,并不拖沓耽搁,只是简单地与师叔作别,并让他将一封信带回师门,收拾了简陋的行李,便随越青阳回京。
“先生,你既是不愿,却为何又要出仕?”辘辘而行的马车中颠簸中,越青阳终是忍不住问道,后一句已然是叹息,“有什么理由能抵得过闲云野鹤、散发扁舟的自由呢?”
江渊泽倚着车壁,闭目养神,听闻越青阳所言亦未睁开眼,“世人对自己求而不得旁人却轻易拥有之物总是尤为在意,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不为之事,难道郡主不是如此?”
越青阳面色苍白地垂首,轻声道:“是如此。”这原本是她的秘密,除了她自己,与那些已然辞世之人,她相信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江渊泽却如此轻易地道破她的秘密,纵使他言辞隐晦,她亦能察觉到他的了然,果然不愧是天下闻名的渊泽先生么……
“我出仕只为承人之诺,总有归去之时,小郡主,是否比你幸运?”江渊泽似笑非笑道。
越青阳:这人好讨厌啊!
“隆隆”几声巨响将马车中的两人一下惊起,越青阳掀开马车布帘正欲呼喊羽林卫,却被窗外的景象惊得怔愣。只见数块巨石将车队砸得一片狼藉,地上数处闪避不及的被碾压而过的人马尸体与血迹。仿佛从天而降的黑衣人已同羽林卫缠斗在一起,刀光剑影在日光下闪耀不止。
“郡主,渊泽先生,勿出马车!”
随着羽林卫队长的一声长吼,几道箭矢破空而来,“笃笃笃”地钉入车厢外侧,越青阳一惊,“啪”地将车窗合上。
同时合上车窗的江渊泽皱眉道:“对方人多势众,有备而来,羽林卫怕不是对手。”
越青阳脸色煞白,强自镇定道:“那如何是好?”
话音未落,原本禁闭的车厢门忽地轰然而开,一名黑衣蒙面人杀气凛然地闯入,手中利刃直直向越青阳刺去。
越青阳无处可避,眼见利刃便要刺穿胸口,下一刻,面前刃尖却蓦地停住,连带黑衣人摇晃着倒下。
不知何时立在黑衣人身后的江渊泽手持长剑,一脚将重伤的黑衣人踢下马车,匆匆对越青阳吩咐道:“坐稳。”随即转身捉住驾车缰绳,策马拉车疾驰而去。
眼见马车驰行,黑衣人纷纷向车马围攻而来,却被羽林卫奋力相阻,偶有一两人靠近,俱被江渊泽砍翻踢倒。
但马车方行出数十丈,其后锐箭便纷纷而至,江渊泽不得不一手持缰绳,另一手不断以长剑挡下箭矢。他猛地一勒缰绳,马匹吃痛,不管不顾向前疾驰,他却反转身来,一手捉向越青阳,按入怀中。
未等越青阳有所反应,便被一把带着滚下马车,立即又自山坡翻滚而下,他一手将她的头紧紧按在怀中,她的背部却不可避免地被石子碎土摩擦得背部火辣辣地刺痛。
终于缓下滚落势头,两人俱是冷汗淋漓、面容苍白,江渊泽却即刻站起,一把抱起越青阳,强行运起轻功疾速而行,同时快速解释道:“方才前路是断崖,而马车与他们拉开一段距离,树林茂密,他们看不到我们滚落马车,一时或许会以为我们随马车翻落,但很快便会再追来,我们必须快走。”
越青阳向来娇生惯养,何时受过这般的伤,此刻全身无处不痛,但形势紧迫,她只能咬紧牙关忍耐,况且,她的目光看向江渊泽苍白却沉冷的面容,他伤得更重,却要负她疾行,想必更是艰苦。
作者有话要说: 求收藏,求留言嘤嘤嘤……
☆、【壹柒】不信人间有白头(三)
不知行了许久,江渊泽终于停住脚步,将越青阳放下。越青阳一落地,便四处张望,放眼尽是丛林茂密,土石野草,不由问道:“此为何处?”
不想江渊泽却道:“我如何得知。”
“那你为何停在此处?”
江渊泽:“跑不动了。”
越青阳:“……”
他说的是实话,在越青阳落地的同时,他也以手撑地瘫坐下来。越青阳眼尖地望见他背上已有丝丝血痕自衣中渗出,不由道:“我在附近找找有无水源。”
他点头嘱咐道:“别走太远。”
越青阳亦不敢走远,幸运的是她走到约摸半里之外,“哗哗”水流之声便传入耳中,她立即折返,对江渊泽道:“我听见水声了,你还能走么?”
江渊泽立即起身道:“走吧。”
越青阳看他背上血痕一眼,问道:“要我扶你么?”
江渊泽似笑非笑道:“要我抱你么?”
越青阳被他暗含的轻佻激得脸上一红,别过头不理会他。
江渊泽便也不再说话,两人在沉默中往水源处而行。
一道细细的溪流贯彻山间,在岩石沙砾上斗折南行,轻快涌动,明澈可见底。
江渊泽手上捉着一把方才路上采的外敷伤势的野草,递了大半给越青阳,此时两人顾不得男女大防,各自清理起手脚上伤势。但半晌后两人却面面相觑起来,手脚上的划伤尚可自己清理,背上的……该如何是好?
“你转过身去,脱衣服。”越青阳忽然道。
“不必了。”江渊泽默然一阵,说道。
“我都不介意你别扭什么,”越青阳涨红了脸,“你会医术,应知伤势不处理的后果。”
江渊泽终是妥协了,转过身去,衣裳褪下,白皙劲韧的背部便袒露在越青阳面前,只是对着这布满道道割裂创伤破损的脊背她反倒提不起害羞的心思了。
草药的清凉、伤口的刺痛以及……指尖的柔软让江渊泽背部紧绷,脊骨突显,半晌过后,随着上药完毕,这种奇异的折磨才消失,江渊泽不由微微松了口气,他迅速将衣裳穿上,转过身来,对越青阳不怀好意地道:“轮到你了。”
“什……什么?”越青阳知道他的意有所指,脸上不由再次烧起来,“我伤得不多,就不必了。”她受伤确实不重,方才自山坡滚落,江渊泽以另一手臂为她挡去了部分背部与砂石间的刮擦。
江渊泽一本正经道:“我会医术,知道若是伤势不处理,即使是细微创伤,亦会导致死亡。不必害羞,我只是作为一个医者为你处理伤势罢了。”
见她犹豫着迟迟未有反应,他催促道:“快些,我们要在天黑前找到人烟,否则夜宿山林可不是有趣之事。”
江渊泽同样没有欣赏女子细腻背部的轻佻心思,只是匆匆地为她擦上药草。越青阳咬着牙,难堪尴尬得泪水不由渗出,但她背对着江渊泽,故他并未看见,直到她重新穿上衣裳,转回身,才望见她眼中隐隐泪痕。
他心下叹息,却又不知如何安慰她,只能道歉:“对不住。”
她瞪他一眼,说道:“若是你真是歉疚就把眼睛挖掉。”
江渊泽:“那你就当我是假的歉疚罢。”
所以说,这人真的是很讨厌啊!
越青阳自幼长在宫闱,娇生惯养,在这山野间步速自是不快,而江渊泽也不再有气力负她而行,故以两人只能缓慢前行,幸而虽是遇上一些毒蛇野兽,但却未遇上追兵。
视野所及的不远处出现的简陋草屋让两人眼中一亮,不由加快步伐上前敲门,却无人应答。江渊泽径自推开简陋木门,屋中家徒四壁,仅有几张板凳、一个烧火的土炕而已。
“许是猎人午间休憩的小屋罢,”江渊泽揣测道,“看来附近也许有村庄。”
他话音才落,便忽然转身,警觉道:“有人。”
越青阳同样一惊,双手紧张地不由自主捉住他的衣袖。
“只有一个人。”他说着,将门掩上,背靠着门边墙上,若是来人不善,便可在对方开门的瞬间突袭。
门“吱呀”一声打开,江渊泽却未出手,只见来人一身短衣葛布,虎背熊腰,身负弓箭,似是猎户装扮。
他见到两人同样惊疑,“你们是谁?”
江渊泽便随口编了一个俗不可耐的落难兄妹的故事,递给猎户一些碎银,猎户便表示可以带两人回到他们村庄。
当日晚间,两人便宿在猎户家中,晚风夜凉,寒月如霜,越青阳蜷缩在床上,累及,就要昏昏欲睡,却忽闻坐在身旁的江渊泽道:“我们跑不了。”
“什么意思?”她蓦地清醒了几分,睁开眼问道。
他神色平淡地说道:“再过一会,便会有人来捉我们。”
“啊?”这回她睁圆了眼,惊异道:“为什么?
“猎户的神色有些不对,而且我听到他暗中对村人说报信云云。”
“那我们怎么不走?”
“想必报信所得酬金不少,若发现我们欲走,村中所有人都会前来阻拦我们,”他揉了揉额头道,“我一个人尚可悄然而行,加上你……”
越青阳彻底没了睡意,懊恼道:“早知便不同那猎户回村了。”
“村人对附近地形熟悉不过,我们迟早会被找到,”江渊泽侧首看她,夜色沉暗中,他的眼眸被月光映得微亮,“放心,我算了一卦,我们不会有事。”
越青阳望着他浸在黑暗中的面容良久,翻过身去,闷声说道:“你如此会推算,为何算不到我们竟会被迫于此境?”
他耸了耸肩,道:“我只推出此行必有一劫,不料竟来得如此快。”
她哼道:“你如此说岂非事后诸葛。”
江渊泽终于不再说话。
昨日虽是劳累了一日,但在提心吊胆之下,越青阳在晨光熹微时便醒转,她眨了眨眼,模糊的视界逐渐清晰,却见身侧的江渊泽并未躺下,仍是盘腿而坐,双手置于膝头,似已熟睡。以为他未醒,越青阳轻手轻脚地下床,走出屋外。
红日自东方的轨迹冉冉而上,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投射到江渊泽身上时,他终于睁开眼,同时打开的还有屋门。
几个黑衣人没入屋内,其中一人道:“渊泽先生,请随我们走罢。”
“和阳郡主在何处?”他沉声问道。
“自是也随我们走了,”那人回道,在江渊泽走近时疾点了他身上几处大穴,“渊泽先生武艺高强,我等不得不失礼了,请见谅。”
一个时辰后,押着江渊泽的马车终于在一座不起眼的宅院前停下,江渊泽随黑衣人缓缓步入大堂,只见一名黑衣锦袍的男子负手背向而立。
“晟阳侯。”他说道。
男子转过身来,面容刚肃,年逾不惑却目色明锐如少年,对他拱手道:“孤久仰渊泽先生之名,却未料竟是年少有为。”
江渊泽似笑非笑地道:“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①”
晟阳侯并不介意,只坦然道:“孤自是心不在道。”
江渊泽却转而问道:“和阳郡主可安在?”
然而回答他的却并非晟阳侯,而是从身后传来的伴随着细细碎碎脚步声的少女清澈声音,“劳先生记挂,我很好。”
江渊泽默然望着眼前的少女,良久不语。不过一个时辰,她已不再是那副憔悴褴褛的落难模样,甚至亦非淄林山上的衣饰朴素。羽衣华裳加身,步摇玉簪挽发,正是一名郡主该是的模样。
越青阳却未看他,而是对晟阳侯道:“王叔,让我与渊泽先生谈谈罢。”
晟阳侯目光掠过两人,微微颔首,步出厅门。
“你有什么想问我的么?”
越青阳重新面对江渊泽时,他发现她的脸色一如先前苍白,这大约是她与昨日唯一共同的模样了,他心中生出了许些唏嘘无奈,只道:“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
越青阳有些好笑,他果然是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可是随即口中又蔓上莫名的苦涩来。她定了定神,说道:“我并非永平王之女,实为因‘清君侧’而忤逆皇后,被满门抄斩的虞宁王之女,由晟阳侯夫人所救,替代早夭的永平王之女入宫闱。而晟阳侯亦实为先昭陵太子之子。如此说,你明白了么?”
江渊泽面上无波无澜,只道:“明白了,你们想如何?”
“自是希望先生站在我们一边,”越青阳道,“如今圣上病弱,皇后执掌大权,顺者昌逆者亡,有欲登大宝之势,甚至不惜谋害越氏皇族。能与之抗衡的惟有掌握兵权的晟阳侯,其为我越氏江山之维系。”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江渊泽依旧无动于衷,“我说过,出仕只为承人之诺,报人之恩。”
“渊泽先生,”她肃容道,“你该明白,我们费尽心思请你来,不会给你选择的机会。”
“那可有劳郡主费尽心思了。”他不假思索地嘲讽道,随即却是微微一怔,心下叹息,其实他竟然还是在乎的么。
随着他这句话,越青阳自再见到他起一直戴着的冷肃的面具似乎有了裂痕,不由低下头,掩饰自己复杂的神情。
空旷的厅堂一时陷入了沉默中,两人之间惟有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