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曾祖母在世时,我的奶奶是不敢说一句这样的话的,因为我的曾祖母就不是我曾祖父的原配,据说,我曾祖父的原配因为喜欢吃豆子,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被蛔虫活活咬死了。我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医学常识。
我的曾祖母生了四儿一女,直到八十八岁,才故去。她是杨开慧的表亲,所以在□□时才保住了这个地主家里所有人的命。我的曾祖母死后与我的曾祖父同墓而眠,葬在离我老家房子不远的山上,每年过年我的爷爷便会带我们去祭拜,而我曾祖父原配的墓,至今尚不知在何处。
自从我的姑姑吴曦燕离婚以后,她就由做了二十多年的妇女变回了一个少女。她二十多年来不曾变化过的肥胖身材一下子清瘦了下来,有一年过年我还见到她穿了那一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
唐大林对我挤眉弄眼,“有一天我看见我们班有个同学穿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不仅如此,吴曦燕还做了最时髦的发型。我觉得她看起来和旧照片上她少女时代的样子并无二致,笑起来和三十年前一样天真烂漫。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的老年并不发生在生命的后半段,比如吴曦燕。她的老年从她出嫁的那一瞬间就开始了,但是当她结束了她的婚姻以后,她就完成了她的老年生活,开始补偿她自己那未曾开始的盛年生命。
我一直喜欢我的姑姑吴曦燕,哪怕是在她老年的那二十多年里。但是毫无疑问,当她结束了她的老年,变成了我的同龄人时,我更加爱她了。我感觉我像是等了她二十多年,终于等到我和她一样大。
离婚后的吴曦燕经常借我的书看,并且有所共鸣。
我们时常一起聊天。
彼时,我已有了正在谈婚论嫁的男友。我向吴曦燕诉苦,我害怕我的婚姻,不仅是婚姻,一想到婚礼我就已经开始感到恐惧。我恐惧我的婚礼将会发生在一个酒店,满场都是我父母或者我男友父母的客人,我恐惧我会被推搡着,望着眼前根本不认识的人,笑成一朵花,再一口闷干杯子里的酒。
提及此,吴曦燕便说起了我表姐唐大林的那次升学宴。
“那些客人大都是唐家那边的,很多我都不认识。唐家么,喜欢弄些这种酒席,收礼金,我最烦这些应酬。”吴曦燕突然笑了,“后来我看了礼单,一家子人,送一百块钱,来吃中饭,吃完中饭又留下吃晚饭,还要住一晚,醒来又要留下吃早饭。唐家人啊,真是有趣。”
吴曦燕嘴上用“有趣”代替了她心里的别的词,我猜测那个词可能是“荒唐”,也可能是“好笑”。但是“有趣”二字足见了她的功底,就像有风度的英国人在想骂街时却皮笑肉不笑地说一句“interesting”一样。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的姑姑吴曦燕是没有放下的,至今她对过往种种耿耿于怀,并且用词斟酌。她只是表面变成了一个少女,内里却仍然枯萎成了一个老人。那一刻我也明白了,没有人可以不老,即便维持了鲜嫩的躯壳,灵魂在岁月中,也早已被吸干了养分。
可能她自己并不知道,她努力地挣脱开那二十多年如斗争般的生活,可她的骨子里却在悄悄地怀念。
☆、下
我的母亲周安平并不喜欢的我的姑姑吴曦燕,这无干于姑嫂关系。周安平对吴曦燕的不满,来自于吴曦燕这个人本身,她认为吴曦燕太喜欢倾诉自己的不幸,太喜欢指责前夫家的不是,这么多年来,她的耳朵几乎已经起茧。
我的母亲更加不满的是,她的女儿,也就是我,居然心甘情愿地对吴曦燕的倾诉洗耳恭听。
有一回我去我姑姑家,当时我表姐唐大林正在读研究生,正在医院苦哈哈地跟导师的门诊。
我姑姑吴曦燕塞给我一个盒子。
盒子是红色丝绒制的,看起来已是破旧,不像是新买的东西。打开盒子的时候发现盒子的铰链处都是坏的——
盒子里是一个白玉的镯子,成色不算很好。
“你别嫌弃,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我的姑姑说,“这是你奶奶在我结婚的时候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给你。”
我对她说,这东西照理该传给我表姐唐大林。
“不用。”我姑姑说,“你姐姐像个男孩子一样,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
唐大林的确像个男生,从小就是。以前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婶婶带着唐大林和吴臻臻一起去公共厕所。唐大林一脚刚踏进女厕所,就有人喊我婶婶,“哎!怎么回事儿啊,你儿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带进女厕所啊?”
此事一直被引为笑谈,最终成为了每次聚餐的必备节目。
就算我表姐唐大林不稀罕这个镯子,我也不该要,我说,就算唐大林拿这个镯子当摆设,压箱底也行。
我姑姑吴曦燕拿起盒子就往我包里塞,“说了给你,你就拿着,我妈给我的东西,我说什么也不能交到唐家人手里去。”
我蓦然心惊。
后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包里有一个烫手的手镯,彼时我还藏不住话,回家后在饭桌上立马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跟我母亲说了。
“找个时候把镯子退到你奶奶那里去。”我母亲的声音斩钉截铁。
我的母亲为此训诫我,却不是训诫我收了我姑姑的镯子,而是告诫我,做人要学会放下,不要耿耿于怀,斤斤计较。
我小声反驳我的母亲,“可是谁也不知道姑姑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没有理由让她放下啊。”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与其衡量是非的尺度,所以我的母亲对我姑姑的所言所行无权置喙。那个时候我自己却忘了,我的母亲也有自己的底线与其衡量是非的尺度,我对我母亲对姑姑的评价这件事自然也就无权置喙了。
只是身处其中之时,我母亲将自己当做了世间万物的尺度,道德的标杆。而我虽然讨厌与人论及道德,但那时我的确也将我自己当做了世间万物的尺度,以及道理的本源。
我母亲对我的反驳怒从心起,但她为了维持自己一个理性人的形象,压制了自己的情绪。
她说,她只是觉得做人不要在别人背后说那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唐家种种,都不该再提,没有意义。说到最后,我的母亲几乎哽咽,“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说这些。我只知道我嫁到吴家这么多年,就是吴家的人,我为吴家做了一辈子贡献,我坦然,我问心无愧!”
她又一次感动了她自己。
所以我说她与我的祖父祖母并无区别。幼时我看电视剧,电视剧里说坏人的心都是黑色的,彼时我已经知道黑的反义词是白,便对一旁的祖母说,“奶奶是好人,所以心肯定是白色的。”
还在看电视的祖母神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的心不是黑心,也不是白心,我是一颗红心!”说到“红心”二字时,她隐隐透出不容置疑的骄傲自豪。
她也感动了她自己。
后来我想,我的祖母和我的姑姑一样,她极力挣脱了过去那个荒唐可怕喊口号写大字报的斗争时代,可她的骨子里却在悄悄地怀念。
我的母亲作为新时代的职业女性,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权利。她也极力挣脱了那个女子嫁到夫家便像献祭一样没有自我的时代,她似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可是她精神的故乡,仍然处在旧社会偏僻的山村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我的母亲谈心。因为我发现,她和我的姑姑吴曦燕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她也为自己的婚姻感到不平,并且渴望倾诉。但是她不愿公然承认自己婚姻的不成功,更不愿承认她早已满腹怨怼需要发泄需要倾诉。就像一个用仅剩的最后一点钱买下食物的穷人,吃进嘴里发现食物已经变质,也要继续咀嚼下咽,并且阻止自己想要将食物呕吐出来的生理反应。她视这种呕吐为不道德。
而我已经学会了不与她争辩,毕竟我无法□□裸地指明她逻辑上的漏洞:在她评价“我姑姑背后说唐家人”这种行为不道德时,她自己也在背后指责了我的姑姑。
我更不愿与她讨论她的婚姻。
我记得曾经,我不但愿意对我姑姑的倾诉洗耳恭听,对于我母亲的抱怨,我也是不拒绝的。我甚至觉得我有做心理医生的天赋。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医者不自医,同理,如果我遇到的是我自身家庭中的问题,我也就无法客观地给出建议了。
因为当我身处其中,便无法清醒审视问题,而当我将自己从家庭剥离开去,给出客观建议时,我母亲便要骂我冷血无情。
我一直不觉得我的家庭幸福,可是我的父母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如果我胆敢说不,他们便要责怪我不知好歹。但我并不认为我活得比唐大林或者吴臻臻幸福。只是我的不幸,没有那么狗血,没有那么典型,没有八点档的话题性。但我的不幸是最普遍的,是时代分配给这个世界大多数家庭的不幸,这种不幸,无人同情,甚至无法向人开口言说。就像中产阶级,他们比大多数人生活得更优越,可是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看得见更上层的模样,带着爬上上流社会的希冀,可上层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早就被瓜分完毕,于是中产阶级被现实击得头破血流,却无法叫苦。
我的父亲吴宏文与我的母亲周安平是高中同学。
我的父亲原本考上了我老家附近县城的一中,县城最好的中学,但是因为一中离家太远,一月只能回一次家,无法帮家里干农活,所以上完高一我父亲就换了离家近的农村高中。比起农民家庭短视这种说法,我更愿意心地善良地相信这是身为农民子女的无奈。
高二的时候转学的吴宏文和我的母亲周安平成为了同班同学。
他对周安平的第一印象产生于一次上课铃响时。当时吴宏文已经坐在了座位上。在上课铃声结束的最后一秒,几个女同学一起进了教室的门,边走边说边笑。吴宏文并不知道那几个女生在说什么,他只注意到其中一个女生笑的时候嘴巴咧得最大,眼睛眯得最小。
他心想,怎么会有人笑起来这么难看。
于是他记住了这个女生,并且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名为预感的东西——
这个女生将来会成为他的老婆。
这个女生就是我的母亲周安平。
以上,就是我父亲与我母亲的罗曼史。这段罗曼史,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告诉我父亲“一见钟情才是真爱,日久生情都是习惯”的后,我的父亲才告诉我的。我无法证实,这段仅仅发生于我父亲内心独白的故事是不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尤其是他说起这段罗曼史的时机又是如此的尴尬,似乎只是为了给他们所谓的爱情正名。
在之后我又听说了“一见钟情不过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权衡利弊”,这次我并没有把这句话告诉我的父亲。因为我怕他露出什么马脚,令我们彼此尴尬。
在我了解这段罗曼史前,我不是没有探寻过我父母的爱情。我曾经是一个好奇心极度旺盛的人。我不但探寻我父母的爱情,甚至在知道有安全套这种东西之后,还光明正大地问我的父母要过,理由是没有见过,想看看长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还小,并没有意识到不是每一对已经有了孩子的夫妻都会有那种东西。
我听过的,我父亲与我母亲爱情的最早版本,是从他们大学毕业开始的。
他们是高中同学,但是考到了不同的大学,大学时期并没有恋爱,只是偶尔书信往来。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的父亲写信说,她快要大学毕业了,她的父母打算把她嫁出去,她问吴宏文,愿不愿意为她做军师,出谋划策。
放在几乎人人荷尔蒙外喷的今天,这信中含义非常浅薄,不需要咀嚼。但我的父亲吴宏文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可正是这个不解风情的人,看见信中内容的那一刻福至心灵,他知道周安平需要的不是一个军师,而是一个男朋友。
于是他们开始了以结婚为目的的自由恋爱。
我的父亲在恋爱过程中送过我母亲很多东西——
项链,在我母亲坐公交车的时候被偷了。
自行车,在我母亲把它停在家门外的时候被偷了。
……
总之,我父亲送给我母亲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我出生以后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就不曾送过我的母亲任何东西。
事实证明,我的父母可能确实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的曾祖母在我父亲吴宏文正在热恋的时候去世了,这本来怪不到我母亲头上去。
但是那天,吴宏文和周安平说好了要去约会。
我的曾祖母对他的孙子说,不要去。
那时她已经是一个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的老人了。吴宏文挣扎再三,还是去了。
走之前,他对我曾祖母说:“好,我哪都不去,留在家里。”
等吴宏文回到家的时候,我曾祖母的尸体已经冷了。
我的父亲为此感到懊悔,从那时起,他便成了一个孝子,视他吴家的事,为世上第一大事。
我的父母结婚以后三年生下了我。此后两年,他们在别的城市打拼,在工作上倾尽心血,于是把我寄养在老家,大概一两个月来看一次。
自我两岁,我的父母调至本省的省会工作,我的寄养生活才随之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此后二十余年的生活,都是为了让我意识到,人生本没有意义,我的父母只是在重复我祖父母的不幸。
自我叔叔去世以后,我祖父的眼睛里就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了,他时常对我的祖母大发雷霆。但我发誓,只要我的祖母一过世,他的眼里又会只剩下我的祖母,天天以泪洗面,心怀愧疚,后悔不迭。然而当我的祖母在世时,我的祖父不会对她有一丝一毫的仁慈。
我听说过不少我父母恋爱时的浪漫故事,比如项链,比如自行车,甚至我父亲曾经带我母亲跳交谊舞。但是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便不曾见过我父母之间有任何浪漫可言。
充斥我记忆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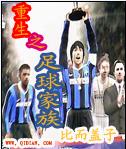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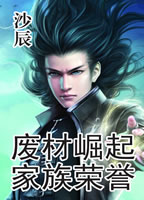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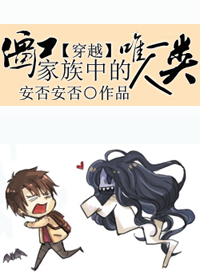
![(综英美同人)反派家族企业[综英美]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16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