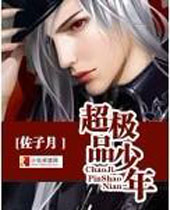浮生寄流年-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那句话只是权宜之计,赵小天却不疑有他,还只当她是不好意思了,毕竟她方才当着两个陌生男人的面又哭又闹,换成谁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他立刻答应下来,临走时还帮她倒了杯温水。
南谨心里还装着另一件事,勉强笑道:“谢谢。”
落日的余晖融在远处高耸的楼宇之间,将天边映得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红橙蓝紫交替重叠,浅淡的云层被勾出一圈金色的边。
盛夏傍晚暑气犹存,连地面上都是热烘烘的。医院就在市区里,一墙之隔的院外是一条市区主干道。晚高峰还没正式开始,路上的车已经渐渐多起来,隐约可以听见汽车引擎声和零星的喇叭声,夹杂在热风里远远地扑送过来。
急诊大楼的后门外头原本是个停车场,最近因为医院扩改建,车子都停到地库去了,这块地便被划为花园绿地区。
除了新铺的草坪外,院里还移种了许多高大茂盛的树木,环绕着大楼,郁郁葱葱,树荫遮蔽下来,仿佛暑气也消了大半。
萧川站在树下抽烟。浅金色的夕阳余光透过高高的树叶缝隙,稀疏地落下来,像一把零碎的金片,散落在他的肩膀上。
他今天穿着棉质的休闲衬衣,袖口随意卷到肘部,可是现在那里已经凌乱不堪,是被人捏皱的。那个女人泪汪汪地拽着他的袖子,明明已经神志不清,偏偏手指还能攥得紧紧的,最后他掰开她,才发现她似乎是因为紧张害怕而正轻微地痉挛。
他站在外面抽了两三根烟,却始终没怎么开口说过话。
余思承不免觉得有些异样,叫了声:“哥。”
他没应,眼睛在淡白的烟雾后头微微眯起来,看着前方不远处。
余思承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场地中央有个小型的石雕喷泉,喷出的水流四下飞溅,将周围的地面打湿了一圈。有位年轻的母亲正在那里哄孩子,那孩子还很小,大约只有三四岁,也不知为了什么,趴伏在妈妈肩头哇哇大哭。
他们与这对母女隔得并不远,可以隐约听见那个年轻母亲的轻柔絮语。然而那孩子却不怎么好哄,哭声始终没有停下来,这时恰好有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从她们面前匆匆经过,孩子看到更是整个人缩成一团,哭声更大了,看样子十分伤心。
这样一幅场景在医院里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其实并不稀奇。毕竟医院这个地方、医生这个职业,总是不招小朋友们喜欢的。
余思承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看的。结果就听见萧川淡淡地开口说:“她也一样,像个小孩子,害怕医院和打针。”
他的语调平静,目光仿佛没有焦点,更像是穿透了眼前的人和事,看到更遥远的过往。
他口中的“她”没名没姓,余思承却立刻听懂了,不禁有些惊愕。自从秦淮死后,所有跟在萧川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曾听他主动提起她。
可是今天……
饶是余思承平日反应快口才佳,一时之间竟也不知该如何回应,只好清清嗓子,迟疑半晌才劝道:“哥,过去的事就别想了。”
萧川的目光转过来,朝他瞥去一眼,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我还以为你不敢接这个话题。”
是不敢。
相信没人敢在萧川面前主动讨论有关秦淮的任何话题,可是余思承只觉得这道眼风扫过来,凌厉得像一把冰刀,令他不自觉打了个寒噤,也只得老实承认:“我这还不是怕哥你多想嘛!”
萧川不置可否,低头掐灭烟蒂,动作停了一会儿,他的语气很淡,眉宇间的那抹倦意也很淡:“是今天这个南谨让我想起了她。”
他当然还记得,以前的秦淮有多么害怕去医院。为此他曾经问过她,而她的回答则是:“因为小时候大病过一场,住了很久的院,每天都在打针吃药,结果弄出心理阴影来了……”
事实当然不会这样简单。可是既然秦淮不肯说,他便也不多追问。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怪癖,而她的这个怪癖,其实也挺可爱的。
因为秦淮和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她聪慧敏捷,勇敢独立,并不喜欢黏人,也不喜欢撒娇。偏偏只有在看病打针时才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楚楚可怜地依偎着他,仿佛只有他才能救她脱离苦海。
她眼泪汪汪的样子十分招人疼惜,如同一只急需被人保护的幼小的动物,一点力量都没有,变得那样柔软可爱。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她的天、她的地,是她唯一的依靠。
这么多年以来,他的身边一直有许多的人,他们为他做事,同时也都在受着他的荫蔽,却唯有在保护她的时候,竟会令他产生一种甘之如饴的感觉。
她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静静地待在他的羽翼下。
他从来没有这样疼惜过一个人。
记得有一次,恰好是隆冬季节,还有两三天就要过年了,室外气温最低时能到零下几摄氏度。她在外头淋了雨,结果很快就感冒发烧起来。他将医生叫到家里,可是即便如此,她一听说最好要打一针,吓得脸色更加苍白了,孩子气地蜷在被子里,说什么都不肯将身体露出来。
当着外人的面,他也不好去哄她,只能转头跟医生商量。最后还是医生无奈地妥协,说:“那就吃药吧,再用物理方法降温。半夜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结果那天晚上,她果然烧得很厉害,吃了药也几乎没什么效果。他只好整夜不睡,就那样抱着她,用棉球蘸上酒精,在她的身体和四肢上来回擦拭着降温。
而她始终表现得十分乖巧,既不吵也不闹,只是偶尔觉得冷,便会朝他怀里挤一挤,紧紧地靠向他,像一只安静蜷缩的小猫。
直到下半夜才终于渐渐退了烧,她被渴醒了,声音虚弱地吵着要喝水。
一大杯温水咕咚咕咚灌下去,她才清醒了些。或许是因为刚刚发过烧,她脸上没什么血色,一双眼睛倒更显得清透明亮,犹如暗夜里的明珠,只是此时睁得大大的,惊讶地望着他:“你怎么还没睡?”
他简直哭笑不得,看来她之前是真的烧迷糊了。
外面天快亮了,他抱住她一起躺下来,声音低低沉沉地,半哄着说:“再睡一会儿。”
他是真的困了,又忙了一整晚,放下心来之后睡得格外沉。等到一觉醒来,窗外正飘着鹅毛大雪,身侧早已空荡荡的,就听见门廊外传来一阵清脆欢畅的谈笑声,貌似又恢复了十足的活力。
他原本以为秦淮是个异类,哪还有成年女人会因为看病打针而吓得瑟瑟发抖呢?结果没想到,在秦淮走了五年之后,今天竟然又遇见了一个这样的女人。
当南谨苍白着一张脸,哀求似的拽紧他的时候,他低头看见她眼睛里薄薄的泪意。那一层闪烁的水光犹如惊涛骇浪,在瞬间狠狠地击中他的心口,心脏涌起一阵猝不及防的闷痛,让他觉得呼吸都是费力的。
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在某个时刻却像极了秦淮。不是因为她的脸,而是因为她的神情、她的眼泪、她揪住他不肯松手的姿态。
他向来足够清醒冷静,可是这一次,他用了太大的力气才能克制住自己瞬间产生的冲动。
他差一点儿就失态了,差一点儿就以为,这个靠在自己身边的、柔弱得像一只初生小动物一般的女人就是秦淮。
在烟草的作用下,萧川重新镇定下来,所以当赵小天走出来找到他们的时候,看到的仍是那张冷峻的面容。
赵小天替南谨表达了谢意,并委婉地表示不需要再上楼去看望南谨了。
余思承把烟掐掉,点点头说:“那我们先走了。”
“好的。”赵小天想起来,客气地转述南谨的话,“南律师说了,等她康复了,请二位吃饭。”
余思承手里掂着车钥匙,笑道:“没问题。”
上了车,他才问:“哥,想去哪儿吃饭?”
萧川望着窗外,最后一线夕阳也沉没在林立的楼宇间,晚霞褪去,天空被蒙上一层浅浅的灰色,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他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地说:“去林妙那里。”
余思承闻言,不禁微微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却什么都没说,只是一手搭在方向盘上,一手掏出电话通知林妙。
“我这儿正好还没开饭呢,你们赶紧过来。”林妙没有犹豫,声音听起来干脆利落,似乎心情很不错。
难得她这样热情好客,余思承挂断电话后,目不转睛地看着车前方笑了一声:“哥,还是你面子大。”
要知道,有多少人想去林妙那儿蹭饭吃都没成功。
林妙家的大厨是她花了大价钱,专程从香港老字号酒楼挖来的,手艺超一流。余思承他们又都是孤家寡人,没老婆没孩子,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的,难免垂涎她家的菜,可是全被她挡在门外,显然并不欢迎他们。
程峰曾经半开玩笑地评价说:“这女人成天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简直白长了一张妖精似的脸。”
余思承深以为然,他也觉得林妙并不好相处,但又不得不佩服她。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混迹于一帮大老爷们儿中间,却并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做得差。
她从十几岁起就跟着萧川,这么些年,也是萧川身边唯一能留得下的女性。她性格孤傲、处事冷静,手段凌厉狠决,有时候甚至不像一个女人,可又偏偏长着一张艳丽至极的面孔。
只是她不爱笑。
似乎也只有在萧川跟前,林妙才会笑得多一些。
所以,当程峰这样评价她的时候,沈郁在旁边不冷不热地接了一句:“她那张脸,也不是长给你看的。”
是给萧川看的。
包括她难得的笑容,也是给萧川的。
这些年来,这几乎已经算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了,只是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假装不知道。
这是个不能被公开的秘密。
就连林妙自己也很清楚,有些事,只能守一辈子,一旦宣之于口,那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显示引用的内容……
回复回复此封邮件回复全部转发删除更多。。。
wxy1991…1128
二十二岁之后,因为人生中有了那个男人的存在,于是一切都被颠覆了,走向了另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26秒前
邮件详情显示邮件详细信息
wxy1991…1128 26秒前
发给:
wxy1991…1128
抄送:花霏雪
二十二岁之后,因为人生中有了那个男人的存在,于是一切都被颠覆了,走向了另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
暴风雨终于在凌晨正式来临,以一种强劲的姿态席卷全城。
南喻住的楼层高,呼啸的风声听得尤为明显。风将窗户玻璃吹得隐隐作响,夹杂着噼里啪啦的雨点声,吓得她连连吸气:“姐,万一一会儿断电断水了,我们怎么办?”
“反正已经关灯睡觉了,断电也没关系。”黑暗中,南谨的声音听起来就淡定多了。
南喻忍不住又往她身边靠了靠,整个人钻进空调被里,瓮声瓮气地抱怨:“最烦刮台风了。上回还因为突然停电,差点儿被困在电梯里出不来,真是要吓死人了。”
“你挨我这么近干吗?我都快被你挤到床下去了。”南谨伸手推推她,“小时候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能改?”
南喻抓住被角,“扑哧”一声笑起来。
她当然还记得小时候,那时也是这样,姐妹俩就爱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其实老家的房子都是自己盖的,有三四层楼那么高,一人一个房间还有富余。可她偏偏就喜欢黏着南谨,于是经常半夜抱着枕头和被子,光脚溜到隔壁房间,手脚并用地趴在南谨身上,最后两人睡作一团。
怀念着幼年的时光,南喻不免感叹:“姐,我们俩好久没一起睡觉了。”
“都这么大了,总不能还跟小孩子一样吧。”
“姐,你变了。”南喻说,“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现在越来越理性冷静,不好玩了。”
其实她只是随口这样一说,结果没想到竟让南谨突然沉默下来。
南喻意识到自己可能讲错话了,一时之间却又不知如何补救,结果只听见南谨淡淡地说:“人总是会变的。”
是啊,人总是会变的。
南喻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借着极微弱的一丝夜光,勉强能看见身边那人的侧脸。
她想,南谨连长相都完全变了,心又怎么可能没有变呢?
其实时至今日,南喻依旧有些不习惯,却也仅仅是不习惯而已。因为,最震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她还记得那一年出了严重意外的南谨、九死一生的南谨,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仿佛即将支离破碎,全身上下几乎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紧闭的眼睛。可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南谨经历了什么,因为有大约两年的时间,南谨始终在外地工作,一次家都没回过。
在那两年间,南谨与家中的通信倒是有的。她只知道,南谨毕业后进了一家通信公司,很快就被派驻到海外工作。
南谨在信里描述了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非洲地区物资贫瘠,电和水都非常宝贵,当地没有网络,手机基站也少得可怜,因此不方便打电话,只能靠书信偶尔联络一下。由于她工作太忙,就连逢年过节都没空回家一趟。
其实南喻一直没想通,姐姐大学时的专业明明和通信工程不沾边,怎么最后却进了这么一家莫名其妙的公司?
直到后来南谨出了事,各方人马仿佛从天而降般,救援声势搞得十分浩大,似乎她是个相当重要的人。当时的南谨不但立即被安排住进全国最好的医院,而且有人负责了全部的医药费,并有专人来替家属做心理疏导工作,承诺会尽最大努力救治南谨。
也是直到那个时候,南喻才终于知道,原来南谨消失的那两年,其实没有去非洲。
可是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又遇见过什么人?却始终没有答案。
今天晚上,南谨破天荒地主动住到她这里来,南喻一时没忍住,终于犹豫着问:“姐……”
“嗯?”
“萧川是什么人?”
窗外风雨大作,驱散了最后一点睡意。
南谨一开始默不作声,只是静静地听着那凄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