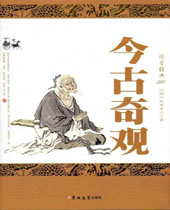今古奇观-第17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招,深中其意。看了帖子,乃道:“拜上相公,明日早来领教。”那家人得了言语,即便归家,回复家主道:“汪太爷拜上相公,明日绝早就来。”那知县说明日早来,不过是随口的话,那家人改做绝早就来,这也是一时错讹之言。不想因这句错话上,得罪了知县,后来把天大家私,弄得罄尽,险些儿连性命都送了。正是:
舌为利害本,口是祸福门。
当下卢柟心下想道:“这知县也好笑,那见赴人筵席,有个绝早就来之理。”又想道:“或者慕我家园亭,要尽竟日之游。”吩咐厨夫:“太爷明日绝早就来,酒席须要早些完备。”
那厨夫听见知县早来,恐怕临时误事,隔夜就手忙脚乱收拾。
卢柟到次早吩咐门上人:“今日若有客来,一概相辞,不必通报。”又将个名帖,差人去邀请知县。不到朝食时,酒席都已完备,排设在园上燕喜堂中。上下两席,并无别客相陪。那酒席铺设得花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
且说汪知县那日出堂,便打帐完了投文公事,即便赴酌。
投文里却有本县巡检司解到强犯九名,赃物若干。此事先有心腹报知,乃是卫河大伙,赃物甚多,又无失主。汪知县动了火,即时用刑拷讯。内中一盗甚黠,才套夹棍,便招某处藏银若干,某处埋赃几许,一五一十搬将出来,何止千万。知县贪心如炽,把吃酒的念头放过一边,便教放了夹棍,差个心腹吏带领健步衙役,押资前去,眼同起赃,立等回话;余盗收监,赃物上库。知县退坐后堂,等那起赃消息。从辰至未,承值吏供酒供食了两次,那起赃的方才回县,禀说:“却是怪异。东垦西爬,并没有半个锡皮钱儿。”知县大怒,再出前堂,吊出前犯,一个个重新拷掠。夹到适才押去起赃的贼。
那贼因众人怒他胡说,没有赃物,已是拳头脚尖,私下先打过几顿。又县司兵拷打坏的,怎当得起再夹,登时气绝。知县见夹死了贼,也有些着忙,便教禁子狱卒叫唤,乱了半晌,竟不苏醒。汪知县心生一计,喝叫:“且将众犯还监,明日再审!”众人会意,将死贼混在活贼里,一拥扶入监去,谁敢道半个死字。又向禁子讨了病状,明日做死囚发出。汪知县十分败兴,遂想着卢家吃酒,即刻起身赴宴。此时已是申牌时分,各役簇拥着大尹,来到卢家园内。
且说卢柟早上候起,已至巳时,不见知县来到,差人去打听,回报说在那里审问公事。卢柟心上就有三四分不乐,道:
“既约了绝早就来,如何这时候还问公事!”停了半晌,音信杳然,再差人将个名帖邀请。卢柟此时不乐,有六七分了,想道:“是我请他的不是,只得耐这次罢。”俗语道:“等人性急。”
又候了半晌,连那投邀帖的人也不回来。卢柟道:“古怪!”再差人去打听。少停,同着投邀帖的人一齐转来,回复说:“还在堂上夹人。门役道:“太爷正在恼怒,却放你进去缠帐!拦住小人,不放进去,帖尚未投,所以不敢回报。”卢柟听见这话,凑成十分不乐,又听得说夹问强资要赃物,心中大怒,道:
“原来这个贪残蠢才,一无可取,几乎错认了!如今幸尔还好!”
即令家人撤开下面这桌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
“快把大杯筛热酒来,洗涤浴肠!”家人都禀道:“恐太爷一时来到。”卢柟喝道:“柟!还说甚太爷!我这酒可是与那贪残俗物吃的么?况他爽信已是六七次,今晚一定不来。”家人见家主发怒,谁敢再言,随即斟酒,供出肴馔。小奚在堂中宫商迭奏,丝竹并呈。卢柟饮过数杯,叫小厮:“与我按摩一番,今日伺候那俗物,觉道身子困倦。”吩咐闭了园门。于是脱巾卸服,跣足蓬头,按摩的按摩,歌唱的歌唱。叫取犀觥斟酒,连饮数觥,胸襟顿豁,开怀畅饮,不觉大醉。将肴馔撤去,赏了小奚,止留果品按酒,又吃上几觥,其醉如泥,就靠在桌上,齁齁睡去。家人谁敢去惊动,整整齐齐,都站在两旁伺候。
里边卢柟便醉了,外面管园的却不晓得内里的事。平日间宾客出进得多,主人又是个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日逐将园门大开惯了,今日虽有命闭门,却不把在心上。又且知道请见任官府,倘若来时左右要开的,且停一会儿。挨落日衔山,远远望见县头踏来,急忙进来通报。到了中堂,看见家主已醉倒,吃一惊,道:“太爷已是到了,相公如何先饮得这个模样?”众家人听得知县来到,都面面相觑,没做理会,齐道:“那桌酒便还在,但相公不能够醒,却怎好?”管园的道:“且叫醒转来,扶醉陪他一陪也罢。终不然,特地请来,冷淡他去不成?”众家人只得上前叫唤,喉咙喊破,如何得醒。
渐渐听得人声嘈杂,料道是知县进来,慌了手脚,四散躲过。
单单撇下卢柟一人。只因这番,有分教,佳宾贤主,变为百世冤家;好景名花,化作一场春梦。正是:
盛衰有命天为主,祸福无门人自生。
且说汪知县离了县中,来到卢家园门首,不见卢柟迎接,也没有一个家人伺候。从人乱叫:“门上有人么?快去通报,太爷到了。”并无一人答应。知县料是管门的已进去报了,遂吩咐不必呼唤,竟自进去。只见门上一个匾额,白地翠书“啸圃”两个大字。进了园门,一带都是柏屏。转过弯来,又显出一座门楼,上书“隔凡”二字。过了些门,便是一条松径。绕出松林,打一看时,但见山岭参差,楼台缥缈,草木萧疏,花竹围环。知县见布置精巧,景色清幽,心下暗喜道:
“高人胸次,自是不同。”但不闻得一些人声,又不见卢柟相迎,未免疑惑。也还道是园中径路错杂,或者从别道出来迎我,故此相左。一行人在园中任意东穿西趟,反去寻觅主人。
次后来到一个所在,却是三间大堂,一望菊花数百,霜英粲烂,枫叶万树,拥若丹锦,与晚霞相映。橙桔相亚,累累如金。池边芙蓉千百株,颜色或深或浅,绿水红葩,高下相映。
鸳鸯啵丰蚱湎隆M糁叵氲溃骸八胛铱淳眨卦谡飧鎏弥辛恕!本吨撂们跋陆巍W呷肟词保抢锛蹙葡┯幸蝗耍钔孵凶悖又邢蛲舛吭谧郎洗螨J,此外更无一个人影。从人赶向前乱喊:“老爷到了,还不起来!”汪知县举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又见旁边放着葛巾野服,吩咐:“且莫叫唤,看是何等样人。”那常来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细一看,认得是卢柟,禀道:“这就是卢相公,醉倒在此。”
汪知县闻言,登时紫涨了面皮,心下大怒道:“这厮恁般无理!故意哄我上门羞辱!”欲待叫从人将花木打个稀烂,又想不是官体,忍着一肚子恶气,急忙上轿,吩咐回县。轿夫抬起,打从旧路,直至园门首,依原不见一人。那时已是薄暮,点灯前导,那些皂快,没一个不摇首咋舌道:“他不过是个监生,如何将官府恁般藐视!这也是件异事。”知县在轿上听见,自觉没趣,恼怒愈加,想道:“他总然才高,也是我的治下。曾请过数遍,不肯来见,情愿就见,又馈送银酒,我亦可谓折节敬贤之至矣。他却如此无理,将我侮慢!且莫说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该如此!”到了县里,怒气不息,即便退入私衙不提。
且说卢柟这些家人、小厮,见知县去后,方才出头。到堂中看家主时,睡得正浓,直至更余方醒。众人说道:“适才相公睡后,太爷就来,见相公睡着,便起身而去。”卢柟道:
“可有甚话说?”众人道:“小人们恐不好答应,俱走过一边,不曾看见。”卢柟道:“正该如此。”叫管门的,打了三十板:
“如何不早闭园门,却被这俗物直到此间,践污了地上!”教管园的:“明早快挑水,将他进来的路径扫涤干净。”又差人寻访常来下帖的差人,将向日所送书仪,并那罈泉酒,发还与他。那差人不敢隐匿,遂即到县里去缴还,不在话下。
却说汪知县退到衙中,夫人接着,见他怒气冲天,问道:
“你去赴宴,如何这般气恼?”汪知县将其事说知。夫人道:
“这都是自取,怪不得别人。你是个父母官,横行直撞,少不得有人奉承;如何屡屡卑污苟贱,反去请教子民。他纵是有才,与你何益?今日讨恁般怠慢,可知好么。”汪知县又被夫人抢白了几句,一发怒上加怒,坐在交椅上,气愤愤的半晌无语。夫人道:“何消气得?自古道:‘破家县令。’”只这四个字,把汪知县从睡梦中唤醒,放下了怜才敬士之心,顿提起生事害人之念。当下口中不语,心下踌躇,寻思计策安排卢生:“必置之死地,方泄吾恨。”
当夜无话。次日早衙已过,唤一个心腹令史,进衙商议。
那令史姓谭名遵,颇有才干,惯与知县通赃过付,是一个积年滑史。当下知县先把卢柟得罪之事叙过,次说要访他恶端,参之以泄其恨。谭遵道:“老爷要与卢柟作对,不是轻举妄动的。须寻得一件没躲闪的大事,坐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
那参访一节,恐未必了事,在老爷反有干碍。”汪知县道:
“却是为何?”谭遵道:“卢柟与小人原是同里,晓得他多有大官府往来,且又家私豪富。平昔虽则恃才狂放,却没甚违法之事。纵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处挽回,决不至死的田地。那时怀恨挟仇,老爷岂不返受其累?”汪知县道:
“此言虽是,但他恁地放肆,定有几件恶端。你去细细访来,我自有处。”谭遵答应出来,只见外边缴进原送卢柟的书仪、泉酒。汪知县见了,转觉没趣,无处出气,迁怒到差人身上,说道:“不该收他的回来!”打了二十毛板,就将银酒都赏了差人。正是:
劝君莫作伤心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却说谭遵领县主之命,四处访察卢柟罪过,日往月来,挨至冬末,并无一件事儿。知县又再四催促,倒是两难之事。一日在家闷坐,正寻思卢监生无隙可乘,只见一个妇人急急忙忙的走入来。举目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家人钮文的弟妇金氏。钮文兄弟叫做钮成。金氏年纪三十左近,颇有一二分姿色,向前道了万福:“请问令史:我家伯伯何在?得遇令史在家却好。”谭遵道:“钮文在县门首。你有甚事寻他?”金氏道:
“好教令史得知:丈夫自旧年借了卢监生家人卢才二两本银,两年来,利钱也还了若干。今岁丈夫投卢监生家,做长工度日。卢家旧例,年终便给来岁半年的工银。那日丈夫去领了工银,家主又赐了一顿酒饭,千欢万喜。刚出大门,便被卢才拦住,知道领了工银,索取前银。丈夫道是年终岁暮,全赖这工银过年,那得有银还债?卢才抵死要银。两家费口,争闹起来,不合骂了他‘奴才’,被他弟兄们打了一顿。丈夫吃了亏,气愤回家,况是食上加气,厮打时赤剥冒了寒,夜间就发起热来。连今日算得病共八日了,滴水不进,太医说是停食感冒,不能疗治。如今只待要死,特来寻伯伯去商量。”
谭遵闻言,不胜欢喜,道:“原来恁地。你丈夫没事便罢,倘有些山高水低,急来报知,包在我身上与你出气。还要他大一注财,够你下半世快活。”金氏道:“若得令史张主,可知好么。”正说间,钮文已回,金氏将这事说知,一齐回去。临出门,谭遵又嘱咐道:“如有变故,速速来报。”
钮文应允,离了县中。不消一个时辰,早到家中。推门进去,不见一些声息,到床上看时,把二人吓做一跳。原来直僵僵挺在上面,不知死过几时了。金氏便嚎啕大哭起来。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那些东邻西舍,听得哭声,都来观看,齐说:“虎一般的后生,怎地这般死得快!可怜可怜。”钮文对金氏说道:“你且莫哭,同去报与我主人,再作区处。”金氏依言,锁了大门,央告邻里暂时看觑,跟着钮文就走。那邻里中商议道:“他家一定去告状了。地方人命重情,我们也须呈明,脱了干系。”随后也往县里去呈报。其时远近村坊尽知钮成已死。早有人报与卢柟。原来卢柟于那日厮打后,有人禀知备细,怒那卢才擅放私债,盘算小民,重责三十,追出借银原券,卢才逐出不用,欲待钮成来禀,给还借券。及至闻了此信,即差人去寻获卢才送官。那知卢才听见钮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先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且说钮文、金氏,一口气跑到县里,报与谭遵。谭遵大喜,悄悄的先到县中禀了知县,出来与二人说明就里,教了说话,流水写起状词,单告卢柟强占金氏不遂,将钮成擒归打死,教二人击鼓叫冤。钮文依了家主,领着金氏,不管三七念一,执了一块木柴把鼓乱敲,口内一片声叫喊“救命”。
衙门差役,自有谭遵吩咐,并无拦阻。汪知县听得击鼓,即时升堂,唤钮文、金氏至案前。才看状词,恰好地邻也到了。
知县专心在卢柟身上,也不看地邻呈子是怎样情由,假意问了几句,不等发房,即时出签,差人提卢柟立刻赴县。公差又受了谭遵的叮嘱,说“太爷恼得卢柟要紧,你们此去,只除子女孩子,其余但是男子汉,尽数拿来。”众皂快素知知县与卢监生有仇,况且是个大家,若还人少,进不得他大门。遂聚起三呈四弟,共有四五十人,分明一群猛虎。
此时隆冬日短,无已傍晚,彤云密布,朔风凛冽,好不寒冷。谭遵要奉承知县,陪出酒食,与众人发路,一人点起一根火把,飞奔至卢家门首,发一声喊,齐抢入去,逢着的便拿。家人们不知为甚,吓得东倒西歪,儿啼女哭,没奔一头处,卢柟娘子正同着丫鬟们在房中围炉向火,忽闻得外面人声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叫丫鬟们观看。尚未动步,房门口早有家人报道:“大娘,不好了!外边无数人执着火把打进来也!”卢柟娘子还认是强盗来打劫,惊得三十六个牙齿矻磴磴的相打,慌忙叫丫鬟:“快闭上房门!”言犹未毕,一片火光,早已拥入房里。那些丫头们奔走不迭,只叫:“大王爷饶命!”众人道:“胡说!我们是本县太爷差来拿卢柟的,什么大王爷!”卢柟娘子见说这话,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