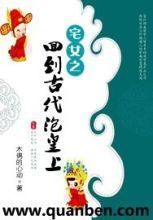皇上,请您雨露均沾-第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皇帝恼得眯眼:“心里有气就摆明了说!你少跟爷又提什么皇上、奴才的。爷不缺奴才,爷只是缺一个你!”
从圆明园回来之后,她还是头一回瞧他说话急成这样。言语都是直接冲口而出,而并未在脑子里转过。
他是天子,一言九鼎,一言决定生杀,所以他素常说话都是慢悠悠,显见都是每一个字都斟酌清楚了才出口。可是这一刻,他当真是急了。
真是的,只是瞧他这模样,她心下就又有些没出息地软了。
她怕他瞧出来,便紧忙低低垂下头去:“……若是皇太后,四爷还能怎么着?”
1
282、放心()
一秒★小△说§网。。】,无弹窗!
7更
见她终于肯说实情了,皇帝这才放松下来,最后难得悠闲还挑高了长眉。
“你那语气,可不是挑衅爷呢?你自以为问住爷了,爷必定无言以对。你便由此自自然然可以寒了心。什么出宫之类的话,你也早在嗓子眼儿都预备好了。”
语调终于又慢了下来,是他一贯的悠然自得。
婉兮只垂着头:“奴才只是觉着,皇太后是皇上的额涅,皇上又是孝子,奴才岂可因为自己这么点子小小事体,徒惹了皇上与皇太后之间的嫌隙去?”
皇帝哼了一声,不慌不忙端起酸汤子来喝。喝完了放下,却冷不丁伸手,从她衣襟里抽走帕子去,擦了擦唇角。
婉兮一时没防备住,等叫出来,他已擦完了。
然后,顺手就塞在他自己袖口里了。
婉兮这一张脸登时就又红透了,她小心瞄一眼窗外,然后朝他摊开手:“爷,还来!”
他凝着她的眼,直到将她盯得支撑不住,他才哼了一声:“行,还你。小抠儿!”
说着,他从自己袖口里抽出来一条,随随便便扬给她。
婉兮不疑有他,自然接过来就想收好。可是却一打眼便是朝他瞪眼。
哪里是她原本那条?换成了一条她不认得的!
虽然是个半旧的,用色、用料和用工又并不是明显的上用规矩,不过她也能猜着就是他的!
她不由得咬住唇,“爷这又要作甚?”
他轻叹一声,因是在皇后宫里,便忍着没去捉她的小手。
“那帕子,你留着拭泪。只要你心里觉着委屈,就别憋着,都哭出来。把泪珠子印在那帕子上去,爷就都知道了。”
。
他这人……真是的。
婉兮明明还生着气呢,被他这冷不丁来的一句话,竟险些当场就掉泪了。
她紧忙背过身儿去:“爷这是叫一条帕子替奴才解气咯?爷当真是劝架高手,这法子用得真是俊!”
“你少讥讽爷!”皇帝叹口气,在后头盯着她后脑勺笑。
“既说开就好了,爷心下自然有数。爷回你刚刚的话儿:你问若是皇太后,爷可管?爷告诉你,爷不问是谁,只问那事谁对谁错。你忘了,爷不仅是皇太后的儿子,爷更是这天下的天子!”
“身为天子,爷心下当揣着一杆秤,衡量这天下万事。这事爷回头还要去细问问,总归不会叫你委屈了就是。”
。
婉兮虽然心下还有狐疑,总不信他真会她而对皇太后如何;或者说就算有法子,也只是发落那狠心的嬷嬷去罢了。
可是总归,她心下是顺溜些了。
她便垂首:“实则……我心下原也不是那么想的。我虽觉着委屈,也没想真叫爷跟皇太后因了我而顶撞起来。终归母子乃是天下人伦,爷是孝子,对老人家有些事儿多少该忍。”
皇帝凝着她。
她那小模样,说的话还带着未散尽的委屈。可是她这番话却说得真心实意,并没有虚情假意去。
他便忍不住伸手捏了她手腕一记:“爷办事的法子多着,不必非要那样撕破面皮。总归爷查明之后,必定给你一个交待去。”
“难为你个小丫头,受了委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心下就更知道该怎么做。总归爷还是那句话,在这宫里不管何事何人,你放心就是。”
1
283、四知()
8更
皇帝从皇后宫里回到四知书屋,嘴角含着浅浅一抹笑意,坐下。
这间书屋位于正殿“澹泊敬诚”后面,他更喜欢到这里来独自思忖。
“四知”出自《周易》,说“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这正符合他治理朝政所奉行的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风格。
他坐了一会儿,叫李玉:“宣傅恒。”
少时傅恒来到,皇帝唇角依旧勾着那抹笑:“小九,朕有一件要紧的差事要交给你去查。”
傅恒瞧着皇帝的神色,便施礼问:“……皇上的意思,可是噶尔丹策零的使团?”
皇帝却一笑,轻轻摇头:“不是那个,那个不要紧。朕要你去查一个人。”
是什么人在皇上心中,比噶尔丹策零更要紧?
傅恒不敢怠慢,心下微微一紧,问:“请主子示下。”
皇帝促狭眨眨眼:“是皇太后宫里的一个妇差,叫二喜的嬷嬷。”
“哦?”
傅恒约略有些闪着,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在皇上心里比噶尔丹策零更要紧的人物,竟然只是个妇差。
皇帝点点头:“妇差都是你们内务府里挑了送进来的,于是朕忖着,这个人由你去查较为方便。”
因终究皇太后身边的人,傅恒也自然加着小心:“只是不知……奴才应该从哪个方向去查?”
傅恒不知此时是不是自己瞧花了眼,只觉上座的皇上面上仿佛浮起满面的坏笑来。
皇帝轻哼一声:“……她呢,欺负人了。”
傅恒这话又有些没头没脑,没见过皇上与他这么说话。
“主子的意思是……?”
皇帝叹口气:“是你姐姐宫里的人——九儿。”
傅恒心下这才猛然一沉。
“求主子开示,九儿她可有事?”
皇帝眯了眼瞧着傅恒:“没大事,但是朕不想就这么算了。所以这个差事要派给你去查,小九,你可明白?”
傅恒登时轻咬银牙,唇边已是凝起陌生冷意:“主子放心,奴才必定掘地三尺,丝毫都!”
这日皇帝特地泛舟湖上,陪皇太后一起用膳。
水风清凉,粉荷摇曳,正是叫人心旷神怡。
皇帝含笑道:“儿子的生辰就要到了。都说儿子的生辰便是额涅的受难之日,故此儿子想借生辰之前,先陪额涅回狮子园瞧瞧。”
太后面上微微一变,将手中的象牙筷撂下:“你八月要进木兰围场,又何苦要从中抽出时辰来特地去狮子园一回?”
“先帝爷在位十三年,都从未木兰秋狝过;就更别提要去那狮子园瞧瞧。先帝爷自己都不挂心的事,咱们娘俩也不至于要这么上心了。”
狮子园是先帝雍正当皇子时,被圣祖康熙爷御赐的园子,是雍正当年在热河的住处。
而当年有关皇帝身世的传言,就也发生在狮子园的一处草房。
传言都说,皇帝就是出生在那处草房里。
皇帝淡淡一笑:“皇考生前勤政,才始终未有机会回来看看。儿子既然来了,就应当代替皇考去瞧瞧,也为瞻仰皇考生前风采。”
太后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微微皱眉。
皇帝手肘一挪,手边一个黄釉暗刻龙纹的茶杯忽然掉到地上,摔碎了。
皇帝便皱眉回望:“二喜嬷嬷,朕的茶杯你也敢摔?”
1
284、偷人()
一秒★小△说§网。。】,无弹窗!
1更
皇帝这话一出,周遭人便都傻了。
尤其是二喜妈妈。
她是伺候在畔,不过这御膳却轮不着她到桌旁伺候,故此她距离那茶杯还有好几步远呢,即便伸手也触碰不着啊!
皇上怎地就赖在她头上了呢?
可是不管心里怎么想,二喜妈妈却也不敢造次,连忙跪倒,朝上磕头:“奴才该死!求皇上开恩!”
皇太后也不由得朝皇帝瞧过来,低声道:“皇帝今儿这是怎么了?”
皇帝朝皇太后淡淡一笑:“额涅最是菩萨心肠,对手下奴才最是宽仁。日子久了,便不免有些奴才蹬鼻子上脸,借着额涅的慈恩,做些下作的事。因顾着额涅,这几年儿子这耳朵里也听了不少禀报,不过儿子都压服下去了。只是没想到,儿子的宽仁却纵了这帮子奴才,叫他们更加无法无天!”
皇太后心下也是咯噔一声,放缓了声息问:“你是说二喜她……?”
皇帝伸手掸了掸袖口,仿佛刚刚这袖口碰着那茶杯都染脏了一般。
“二喜,朕问你,当年内务府选你妇差,进宫陪伴太后,那要符合什么规矩?”
二喜一怔,忙答道:“必得是年满四十岁,无子、无牵挂的孀妇,方得入选。”
皇帝微微眯眼:“你可有隐瞒?”
二喜忙磕头:“岂敢有隐瞒?!”
皇帝恻恻一笑:“是么?你的意思是,你果是无子的孀妇喽?”
二喜慌忙伏地答:“奴才旗籍上都有明明白白记载,况且从旗下佐领一直上报到内务府,中间层层官员都要为奴才作保,奴才才能有资格入选。皇上纵不信奴才,也要信那户籍,更要信那些作保的大人们呐!”
皇帝轻哼:“你的户籍没记错,那些官员们按着你的户籍查证,自然也没错——你的确是死了男人,你跟你男人也没有儿子。从这一项上来说,谁都没错。”
皇太后眯眼瞧着儿子。
此时的儿子就挨着她身边儿坐着,又明明已近生辰了,这会子原本无论从距离上,还是从感情上,他们母子原本都该是最亲近的。可是她却不知为何,只觉此时距离着儿子好远,好远啊。
那距离,仿佛就是从慈宁宫望向太和殿的距离;是一个原本应该近在身边的母亲,却不得不屈服于君权,不得不将自己与儿子之间的距离拉成一个臣子和一个天子之间的距离那样一般。
儿子长大了,儿子已是统领这天下的帝王。
儿子的心,她已然渐渐看不清、看不透。
甚至,就算儿子开始在她眼前儿,当着她的面儿玩儿起了心眼儿,她都已然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
皇帝享受够了二喜妈妈的惶恐,这才缓缓坐直,用手指敲了敲桌面。
“可是你在外头,却曾瞒着你家里人,跟别的男人生下过儿子!”
“只不过你男人死的当口恰恰好,就在你生下那儿子不久,你男人就死了,于是他永远都没办法知道你的那个秘密了。”
船上一时鸦雀无声,人的眼睛都转向二喜妈妈,带着各种各样的情绪盯着她。
二喜仰头望向皇帝,嗓子眼儿里哑哑有声,却已是说不出话来。
良久船上才传出一串哀嚎:“皇上,奴才冤枉。那都是邻里扯老婆舌的冤枉了奴才去,奴才没偷过人啊!”
1
285、生非()
2更
二喜妈妈被拖下船去。
办事的太监都明白规矩,一边拖着已是一边伸手狠狠捂住了二喜妈妈的嘴,不叫她喊叫出来,扰了主子的兴致。
可是即便如此,皇太后又哪里还有用膳、游湖的兴致?
她冷下脸来,目光并不看向儿子,只看向湖上:“皇帝,二喜的事你可查实了?二喜陪伴哀家多年,哀家自认也能看得清她的性子,她如果当真在外头偷过人,有过野孩子,她至少应该透露些许出来才对。可是这些年哀家瞧着,她并无行差踏错。”
皇帝淡淡抿了口酒:“所谓孀妇门前是非多,尤其她这样壮年守寡的,邻里之间这样的传言便更多。那传言多到叫内务府的官员们都不敢再漠视,不得不上报给儿子知晓……这样的事,儿子已不必捕风捉影去查,只从这传言本身,便已不宜叫她再伺候在额涅身边。”
皇太后忍着恼意,微微闭上眼:“皇帝,你难道没想过,这些孀妇门前的是非,实则许多是无中生有么?!”
皇帝倒毫不犹豫地点了头:“额涅说的对。这世上原本许多事就都是无事而生非。”
。
这日船上的事,只有皇帝与皇太后身边的人才知道。
外头人能知晓的,只是那个在皇太后跟前有头有脸的二喜妈妈莫名地不见了。就算有人小心跟皇太后宫里的人打听,也都推说是二喜害了病,不宜伺候在皇太后身边,这才送出宫去养老了。
纯妃本和皇后一起侍奉在皇太后身边,那日婉兮受苦的事她也亲眼瞧见了,于是听二喜妈妈的事儿传来,她便只是淡淡一笑。
“这世上哪儿有那么巧的事?”
纯妃身边的女子巧蓉也忖着:“这是皇后娘娘当日不好当着皇太后的面护着手下人,这便时候拿到了那二喜妈妈头上去?”
纯妃盯着玻璃水银镜子里自己秀美依旧、然则还是染了些岁月痕迹的面容:“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么回事。可是你再细想,皇后娘娘一向在太后跟前俯首帖耳,那二喜也算太后跟前得用的,皇后又如何敢在事后再拿那二喜妈妈出气?”
巧蓉有些不解:“若不是皇后,那还能是谁?”
纯妃也眯了眼,用牙梳缓缓梳理自己青丝:“……这世上,就连皇后都不敢做的事,你道还有谁人敢做?”
巧蓉也吓了一跳:“难道是皇上?可是……皇上又是为何?”
纯妃也停住牙梳:“皇上的心思最是难猜,他这样做可能是皇后出一口气,也可能是限制皇太后……不过,却也有可能是那个女子。”
“那个女子?”巧蓉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主子缘何这样想?”
纯妃放下牙梳,转回头来盯住巧蓉:“那日你也在本宫身边。你以为那女子是缘何被皇太后罚?”
巧蓉仔细想了半晌,自是没敢说是自家主子先在太后面前提到那女子的。于是只道:“……终究还是皇太后看不惯她是个汉姓女。”
纯妃便笑了:“你想想,如果皇后当时太后面前特地多说一句那女子‘灵秀聪慧’,皇太后至于非要将那女子叫到眼前来仔细瞧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