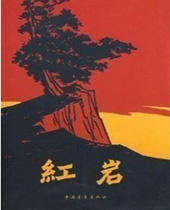红岩-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边山岩上和通向半山楼房的途中,都有许多经过伪装的,被周围的森林掩护着的碉堡。
“这是什么地方?”刘思扬问着自己。他把目光集中在白色楼房周围。渐渐看清楚了,楼房周围的岩石是白色的,树干也是白色。敌人怕囚禁的人从监牢里逃跑,岩石、树木漆成白色,即使是暗夜里也无处躲藏。楼房周围的墙,也是那么高,比渣滓洞箍得更紧。墙上,隐隐约约,看得见电网的支架……啊,又一处秘密的集中营,也许这就是传说中最恐怖的魔窟白公馆吧?
特务提着枪,把刘思扬押上山去。石板路又陡又高,刘思扬心跳得厉害。将近一年的黑牢生活,使他憔悴、衰弱了。他暗自希望这里就是白公馆,希望在这里找到那个姓齐的同志。
巨大的铁门,出现在眼前。铁门之上有几个古老的字:“香山别墅”。一看见这几个字,刘思扬忐忑的心情很快就稳定下来。香山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别号,魔窟居然用上如此富有诗意的名称,这里显然就是白公馆。啊,果然到白公馆来了。
沉重的铁门没有打开。高墙左边,几个面目狰狞的特务,全是美式军装,已经在办公室门口等着。特务熟练地把刘思扬全身上下搜查了一番,和渣滓洞一样,登记姓名、年龄、编号……只是这里囚服上的符号和渣滓洞不同,是蓝布作成的“A*毙危皇恰啊痢毙危直鸱煸谧笮睾秃蟊场4拥羌遣上,他看出了S.A.C.O.几个英文字——这是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简称。一个理发兵走来,不待他坐好,三两刀就剃光了他多年蓄留的长发,却没有剃去他被软禁在家时保留下来的满腮胡须。然后,高墙边的侧门打开,迎面出现了一排楼梯,这排楼梯一半通向楼上,另一半通向楼下,侧门恰好开在楼梯中部转弯的地方。进门后可上可下,便于特务进行监视。刘思扬来不及多看,就被推上了楼。楼上,宽大的走廊包围着牢房,几处楼角,都有特务防守。刘思扬被几个特务迅速推进楼角左后方的一间窄小的房间,卡嚓一声,铁门锁上了。脚上刚钉上的十斤铁镣,妨碍着他的行动,再加上才从光亮的地方被塞进这窄狭黑暗的角落,看不清周围的东西。刘思扬默默地站着,定了定神,才发现有一对炯炯的目光,犀利地盯着他。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陌生人,中等身材,结实、方正的脸,眉宇间有着一股倔强的豪气。额角上,几处发亮的伤痕,更增加了挺立不屈的光彩。但是他那尖锐的目光,却明显地带着怀疑。似乎,这个被单独囚禁的人,并不欢迎新来的伙伴。
两对眼睛互相探索。刘思扬看出对方用目光在质问:是朋友,还是敌人?
“我叫刘思扬。”
“我叫成岗。”声音是冷冰冰的。
啊,成岗!渣滓洞的人谈论过他。说他受过多次毒刑,说他下落不明,也许早已不在人世,谁知道在这里竟见到了他!
刘思扬像见到了亲人。和成岗在一起,今后两个人又可以并肩战斗。而且,通过成岗,他一定能更快地,也更安全地找到那位叫齐晓轩的同志,把自己遇到特务骗取情报的经过向组织报告。他最近遇到的事件,清楚地证明,特务不仅毒辣,而且处心积虑,不断变化着手段,从未放弃破坏地下党和狱中党组织的目的。重新被捕以来,刘思扬的心情很复杂,充满了担心与焦急,因此,他一连几次挑起话头,想和成岗谈谈,可是成岗的反应却很冷淡。显然,成岗在复杂的斗争中,十分谨慎小心,在查清新人的来历以前,不愿和他过分接近。
沉默,很快打断了他们之间偶尔的谈话,小小牢房的空气凝结起来,分外沉闷。
“他有点固执。”刘思扬默默地想,不通过互相间的谈话,怎能互相了解?偏偏自己又急于向党报告重要情况!他想说:“成岗,你知道么,你搞《挺进报》的时候,收听新华社广播的人正是我,我们早就是亲密的战友。”干脆告诉他吧,刘思扬想自己介绍一下,但又克制着。不,用不着这样,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不会轻易相信的。在这里,人们需要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只有在新的生活与斗争中,才会互相了解,信任。
近来的遭遇,使刘思扬胸中充满烈火一样的仇恨,然而此刻,在自己的战友面前,却不能痛快地让怒火熊熊燃烧,喷射,他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苦恼。
天慢慢黑下来。夜,来到陌生的魔窟。
牢房里很黑,看不清房内的一切。只有一道道微弱的淡黄光线,穿过窗户,把铁窗上的栏杆影子,印在凹凸不平的楼板上。栏杆的影子,弯弯曲曲地十分柔软,好像不是用铁,而是用什么轻薄的带子悬挂起来,风一吹就会四散飞去。这是哪儿来的光线?从密云里透出的月光,还是岗亭上射出的灯光?远处,泉水淙淙地流过,比白天听得更清楚。这是涧水从后边山头上泻下,窗口上望得见怪石林立的山壁,却望不见那条山涧。泉水的声音时大时小,没有停过;只有注意去听,或者沉静的时候才听得着,不去注意,又好象没有似的。和泉水潺潺声一道传来的,还有风声,夹着松涛,这是午夜的劲风,在漆黑的荒山上咆哮。刘思扬静静地听着,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朦胧中,他好象看见那流动的泉水,轻轻滑过山头的悬崖,又像正坐在那翠绿的松林中间,听松枝在风中自由地摇曳……记忆在眼前轻轻展开,刘思扬重新经历着过去的事情:狱卒出现在窗前。牢门打开。在叫自己。同志们苍白而激动的脸。火热的握手,默默无言地告别……难忘的同志们,今夜定会和他一样,睡不着觉。他们会低声谈论着他,猜测他的命运。刘思扬眼前,出现了渣滓洞那些不能再见面的,曾经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同志们的眼睛……远远地浮现出那对又大,又亮,流露着深情和痛苦的眼波……眼波突然一变,成了深夜里越墙而入的刺人的目光!
窗外响起了一阵巡逻的夜哨的脚步声,渐渐近了,是两个从不同方向巡夜的哨兵突然遭遇,发生了误会,同时拨响枪栓,大声询问“口令”。然后,两个哨兵在谈话。刘思扬想听他们谈的什么,但太远了,听不清楚。
哨兵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泉水和风还在不息地响。
“你怎么不睡觉?”背后忽然传来成岗低沉的询问。刘思扬的思路被打断了。
“我……睡不着。”
铁链锵锵地响,成岗动了一下。嵌在脚上的铁镣,像冰一样冷而且重。刘思扬一时看不清他的身影,只能听到他淡淡的声音: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刘思扬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能说明此刻的心境,只简单地说:“想渣滓洞的同志们。”
成岗不再说话,在铺位上默默地躺着。刘思扬独自坐着,眼睛仍然盯着黑暗的墙壁……天亮了,楼上楼下还是静悄悄的。刘思扬睁大眼睛,躺在屋角里,望着房顶上雪白单调的天花板。没有黎明时的歌声,也没有熟悉的战友们读书的声音,一点略带生命气息的响动都没有。山上的涧水,潺潺地流,在这万籁无声的清晨,听得十分清楚。
这里不像渣滓洞。这个感觉,昨天一到就产生了,此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深,更鲜明了。一年来,他习惯于用渣滓洞人们的眼光,来衡量一切,因而,他感到白公馆这个地方,完全不像渣滓洞那样活跃和充满斗争。甚至,这里连渣滓洞那种深夜里激动人心的梆声也没有……到了放风的时间,刘思扬拖着沉重的铁镣,蹒跚走出牢门,希望尽快打量一下这座魔窟的环境。走到楼栏杆边,了望了一下四面的高墙,墙上布满电网,只能从电网的孔隙中,才望得见远处的山峦。高墙中间包围着一个天井模样的院坝,除了他们住的这座楼房,在院坝右边还有一排房子,粗看像平房,细看却有几层,有一间门上挂着“管理室”的牌子。管理室旁边,是条阴森的隧道,通向平房底下黑黝黝的地底。院子里有谁栽了几棵绿色的小树,幼小、纤弱,那岩石的院坝不能给它们以些许的营养,但这些小树竟然活着,叶片绿绿的,细小的枝干,就像从树上攀折下来,活生生地硬插在岩石上的。墙头上,涂满了反动标语。刘思扬瞟了一下,什么“以三民主义训练思想,以三民主义规范行动,以三民主义约束言论”。还有一些大字:“统一思想!”“以三民主义消灭马列主义!”……
刘思扬不屑再看。
院坝里,空荡荡地,渺无人影。
隔了一阵,才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无声无息地在院子里出现了。他的头发雪白,满脸花白的胡须又浓又密,像刺猬的箭毛一样遮住脸庞,只露出一对滞涩的眼睛。他糊里糊涂地沿着院坝,用一双枯黑的脚板,机械地神经质地独自跑步……也许,这个人就是老大哥说过的,那个老疯子?
又隔了一阵,才看见,几个骨瘦如柴的人,赤着脚,慢吞吞地也到院子里来了。他们似乎只会按照迂缓的习惯动作,缓缓地散步,眼神灰暗而迟滞,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张望。他们很少抬头上望,最多,只用冷冷的目光,微扫一下楼上新来的人。像根本没有发现刘思扬似的。只有一个稍微年轻点的,提了个瓦盆,在给那几株小树洒水,仿佛无意之间,多看了刘思扬一眼,但也只是多看一眼,再没有更多的表示。
真是个冰冷的世界。刘思扬对于铁窗生活,早已逐渐习惯了。不管是在二处,或者渣滓洞,他都得到过无数同志式的友爱和关心。一张字条,几句鼓励的话,轻轻的一个微笑,和那些在牢房阴暗角落的墙壁上坚贞的题词……都使他感到是和集体生活在一起,免除了冷淡和寂寞。可是,走进白公馆的第一分钟,那种可怕的寂寞,就开始使他心里发凉。此刻他的这种感觉,更沉重了,比成岗带给他的更加沉重。这里的人们面目呆滞,几乎没有表情,多年的囚禁生活,似乎使他们失去了欢笑的可能。同样是中美合作所里的集中营,但是,渣滓洞和白公馆大不相同。白公馆关的人少些,尽是案情严重的人。他们不是用日、月,而是用年岁来计算时间。那些苍白而衰弱的人,许多是被捕了十年八年的,他们被埋在活棺材里,也许早已丧失了对自由的怀念。
也许,这里有党的组织?但是刘思扬无法相信,这里能出现渣滓洞那样狂热的斗争。
刘思扬冷静地观察着,过了几天,他进一步发现白公馆集中营情况的复杂。这儿关的人不多,但什么样的人都有。住在成岗和刘思扬隔壁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黄以声,身材魁伟,是国民党东北军的军长,特务称他“黄先生”,生活受优待,很少和人讲话,成天靠着栏杆,或者迈着机械的军人步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走到尽头就来一个立正动作,再向后转,再机械地前进。他喂着两只猫,一大一小,散步时,溺爱地把猫抱在怀里,轻轻地叫“乖乖,乖乖”。刘思扬没有和他讲过话,大概成岗和他也没有往来。只是前两天,一只小猫不见了,他四处寻找之后,偶然走过窗前,才对成岗和刘思扬说了一句话,问他们看见了他的小猫没有。
黄以声身边,时常出现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孩子的身子特别细弱,却长了一个圆圆的头。这是谁的孩子,怎么出现在集中营里?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长着一双聪明诱人的眼睛,不像是特务的小孩。每天,这孩子都带着书,晃着一个大脑袋,到黄以声房间里去。刘思扬见过这孩子几次,那个奇怪的孩子并没有被刘思扬的铁镣惊跑,相反地,孩子靠近一步,抓住门上的铁条,踮起脚尖,把又大又圆的脑袋,伸进了风门,大胆地问他:“你是从渣滓洞来的?”
刘思扬深深地惊诧了,这孩子怎么知道他的底细?“你看你嘛,”小孩笑了,小手摸着下巴。“胡子好长哟!你在渣滓洞起码关过大半年!”
刘思扬摸摸自己满腮的胡须,完全被孩子的判断迷惑住了。
“二天我来找你们耍,黄伯伯要我背书了。”孩子说完,便跑向黄以声的牢房。到了门口,没有忙着敲门,却回头朝刘思扬说了一句令人无法理解的话:“成岗是我的朋友!”
还有一个更古怪的家伙,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走路时驼着背,踮起脚,一摇一摆。他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蒋介石过去的侍卫队长;原来是个红得发紫的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他想谋杀“老头子”,马上被抓起来,打成了残废。这侍卫队长,已经关了十四五年,是白公馆最老的“政治犯”之一,也许“老头子”有一天还要用他,所以一直受着看守人员的优待。他的消息灵通,一天到晚和看守人员靠在楼栏杆边吹牛。碰着成岗和刘思扬出来放风,也要踱拢来扯上几句闲话,感慨一番。那些看守员说他是“相命专家”,他也吹嘘自己精通“麻衣神相”,到处找人看相,解说手掌上的纹路。这几晚上,他为看守员算命到得意之际,哈哈大笑,虽然隔了墙壁,也听得到他那枭鸟一般的怪笑。住在楼上的,差不多都是受特殊优待的“政治犯”。也许,受着特殊优待的,还有那个不知名的小孩。这些人,虽然和成岗、刘思扬只隔一道墙壁,待遇却完全不同。听说这层楼的左面,还关得有一些重要人物,其中有一个军统局的少将、西安集中营的所长,有人说是因为政治犯逃跑而被囚的,可是刘思扬却一直没有见过这个,来历不凡的特种人物。
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顶楼上。他们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来的。特务从来不准他下楼。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也不准和他见面。
楼下,才是关共产党员的地方,人数不大多,将近一百人。可是前前后后,却关过两千多人。除了现在活着的,其余的人,都已陆续在漆黑的夜里,牺牲在松林坡上,或者附近的镪水池里了。许多革命者,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和共产党员关在同一牢房里的,还有一些违犯了“纪律”的军统特务,从尉级到校级都有。这些特务,在禁闭期间,还负有特殊的任务。他们在牢房里,日夜监视着共产党员的一举一动,随时密告政治犯的活动。
刘思扬觉得,即使日夜受着监视也好,只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