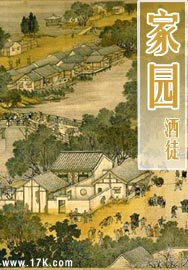将进酒-第19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丁桃哭得鼻涕冒泡,拽着晨阳喊道:“哥!快让大夫进门,府君又烧起来了!”
大夫们战战兢兢,聚集在廊下,小声商谈着药方。那雨淘洗着庭内九里香,把花瓣冲得满地都是。乔天涯跟费盛淋雨而归,踩过花瓣,在檐下迅速擦拭着身上的水。
“先前给元琢瞧病的大夫都在这儿了,”乔天涯把帕子扔回去,“葛青青从厥西调的大夫也在,就没一个能治病的?”
“这烧反复,”晨阳没敢对着窗户讲话,偏身低声道,“说是元气坏了,就跟瓷器似的,没几个敢下药。”
“上回讲元琢也是这个话,”乔天涯没对大夫开呛,顿了须臾,“府君早年是用药坏了身体,但是这些日子在家里调得仔细,不应该的。”
“主子心里也想往好里治,药都在按时吃,”费盛捏着擦水的巾帕,忧心忡忡,“……还是那日伤得太重了。”
屋里要散药味,谁都不想这会儿去惹二爷,就站在檐下等着传唤。可是端药的仆从进去,不到片刻,就听见沈泽川吐的声音。
萧驰野半抱着沈泽川,一摸兰舟背部,都让汗浸透了。药全洒在地上,沈泽川吐不出东西,酸水以后就是干呕。他这会儿胃都是拧着的,人愣是给吐清醒了。
深夜起雾,惨白的灯影晃在雨里,庭院内的脚步声就没有停过。雨把庭院泡得潮,床褥换了一回。
费盛忐忑道:“备个炭盆,烘得干些。”
晨阳看呈出来的纱布浸血,也不知道是萧驰野的还是沈泽川的。
历熊盘腿坐在门边上,自顾自地睡了一会儿,到寅时醒了,费盛让厨房给他盛饭,他埋头扒了一大碗,吃饱了继续坐着,盯着进出的人。
“卯时劝二爷睡会儿,”乔天涯蹲柱子边,擦火点着烟枪,道,“这么熬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就睡里边,我们守门……”
他话音没落,边上就伸出只手,轻轻拨开了他的烟枪。
乔天涯回头,看着姚温玉。
“怪呛的。”姚温玉转着四轮车,面朝正屋。
袅娜的烟雾冒着,在湿淋淋的雨夜里化作那点看不见的温柔。乔天涯撑膝站起来,把烟枪熄了。
卯时院里寂静,天黑了又亮,连续守夜的近卫也在干耗。费盛靠着柱子,闭眼缓精神,突然耳朵微动,睁开了眼,半晌后门口才有动静。
“回来了,”费盛倏地跳下阶,“骨津回来了!”
檐下的灯笼灭了一只,萧驰野听见动静,待片刻后,帘子轻挑。
“二爷,”一路露宿风餐的骨津单膝跪在外间,“我回来晚了!在半道上就听说端州城让骑兵给围了,赶马道都没来得及!”
萧驰野猛地起身,从里间出来,檐下几个人静气凝神地听着。骨津面上的雨水没擦干净,他迎着萧驰野的目光,不敢犹豫,说:“二爷,大师……确实死了。”
作者有话要说: 很晚很晚还有章6000更,明天有课班养生护发的小朋友可以先睡,早上醒来能直接看
第254章 既然()
雨珠把残花打到泥巴里; 再将它的弱瓣敲得七零八落。风卷竹帘,让屋内景象微晃,叫人看不真切。
“我到河州找到大师的俗家,证实大师回到河州以后,就被颜氏以看病为由带走了,”骨津换了口气,“但天无绝人之路,既然!”
门口的近卫都被骨津这句“既然”给吊起了心; 然而他没有后续。
既然?既然什么?
历熊正在捡着罐里的蜜饯吃,突然看廊子尽头冒出颗光滑的蛋。那蛋罩着宽大的僧衣; 提溜着两行袖子小跑; 经过历熊的时候还不忘瞟一眼蜜饯。这一看没留心脚下,自己把自己绊倒了,“扑通”一声跌进竹帘里。
“哎呀!”蛋趴着身子; 仰头说; “给二爷请安!”
众人定睛一看,竟然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和尚,比丁桃还要小。小和尚拖着袖子双手合十; 神情肃穆; 念道:“阿弥陀佛!”
他带着河州口音,念不清楚“弥”字; 听起来像是“阿你陀佛”。
“二爷,”骨津说,“大师肯回河州; 正是为了这小子。”
“嗯嗯,”既然煞有其事地点着头,“正是为了小僧。”
“大师年岁已高,自知不久将辞别世间,可是既然年纪太小,大师便回到河州,把他交给了俗家远亲,岂料就在那时遇见了颜氏。”
“颜公子说要带小僧去玩,”既然眨着澄澈浑圆的眼睛,“小僧要提水,他等得不耐烦,就先请师父走了。”
萧驰野看既然年纪这般小,仅存的侥幸彻底熄灭了。
骨津像是知道萧驰野心中所想,继续说:“既然年纪虽小,却深得大师真传,医术精湛,有他为府君看诊,二爷……”
“嗯嗯,”既然使劲摇着头,“不行的,萤光岂能与皓月争辉?小僧和师父,就像小溪和汪洋,比不得的!”
他脸上的婴儿肥尚未退尽,不仅眉眼间尽是天真,就连言辞都充满稚气。历熊忘了吃蜜饯,跟丁桃从门边歪着脑袋,一起端详这颗水煮蛋。
骨津拎起既然的后领,说:“你先去瞧瞧!”
* * *
既然给沈泽川把脉,他时而皱眉,时而自言自语。
萧驰野放轻声音,问:“如何?”
既然垂眸看着沈泽川的手腕,过了良久,对萧驰野说:“府君真白呀。”
既然白嫩的面容上没有试探。他眼神清澈,夸赞沈泽川,就像是夸赞一泓清泉、一方白云那般自然,萧驰野可怖的占有欲在这里找不到发作的地方。
“府君身体虚弱,是药坏的,但好在这半年调养细致,元气尚存。”既然挽起袖子,捏着笔冥思苦想,往空白的纸上写着方子。
萧驰野不敢就此放心,追问道:“继续用药便可?”
“那肯定不成呀,外伤也是伤,腰都给捅了。府君今夜若是昏厥,或是短暂停止喘息,二爷都不要着急。”既然惋惜地说,“小僧要劝二爷,以后就不要再让府君动武了。府君的身体实在不宜用那样力道刚猛的拳法,一拳出去,唉,别人是痛啦,可是府君也要痛,不划算的。待熬过这两夜,等烧退了,要养上好几年呢。”
既然把方子递给萧驰野。
“府君这半年还是用左手写字吧。”
既然顺势看了萧驰野的掌心,道:“二爷身体健硕,也要注意休息,这伤不能泡水。”
萧驰野说:“几年是多久?”
既然摸着脑袋,道:“我也不知道……养着总没错的。”
萧驰野捏着方子,看向垂帷。沈泽川呼吸匀称,昏睡不醒,伸出的手腕露在微暗的房间里,就像既然说得那样白,白得仿佛摸一摸都会融化。
* * *
沈泽川在昏沉里做了个梦,梦见十五岁的他站在阒都门前,等着师父和师娘还有纪暮接他回家。他穿着花娉婷做的小袄,看细雪沿着城墙簌簌地掉。
纪暮趴在墙头,朝他喊:“川儿,要去哪儿?”
沈泽川揪着新袄,怔怔地说:“回家呀。”
纪暮抬起头,跟他一起望着端州的方向,道:“那等等,爹就要来了。”
沈泽川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他从天亮等到天黑,明明下着雪,他却觉得好热。
纪暮搓着手臂说:“哥有点冷,你要上来烤火吗?”
沈泽川摇头:“我好热。”
纪暮便在墙头生火,他伸着双手取暖,跟沈泽川聊天。他说:“这趟回去,哥就能娶亲了,娘念叨了好几年。”
他们等了很久,沈泽川腰间痛,小腿痛,哪里都痛。他拭着汗,始终望着前方。
纪暮看天色暗了,忽然喃喃着:“爹不来了。”他的火烧尽,起身穿上搁在一旁的军袄,趴在墙头,冲沈泽川露齿一笑,“川儿。”
沈泽川仰起头,走了几步,看着他。
纪暮说:“哥的哨声响了,等不了了,要走了。”
沈泽川点头,习以为常:“那你去吧,我给娘说。”
纪暮露出头疼的神色,叹道:“哥发愁,你……”
“我从这走回去,”沈泽川抬指指着远方,“很近的。”
纪暮看着沈泽川,眼神温柔,说:“我弟弟可怎么办啊。”
沈泽川听见马蹄声,他有些雀跃,喊道:“哥,师父来了!”
纪暮没有说话,只是那样撑着首笑。
沈泽川转过头,看天际飞出只展翅的海东青,接着跑出匹通体乌黑的马,只有前胸一点白。他停下脚步,看那马跑到他身前。
马背上坐着个戴着头盔的少年郎,海东青落在他肩膀,他摘掉头盔,露出张不太高兴的脸。他俯身过来,端详着沈泽川,说:“杵着干什么?上马,二公子带你走。”
沈泽川不理他,他便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头盔叩在沈泽川的头上,然后扛起沈泽川。
“啊,”沈泽川闷在头盔里,说,“我要回家。”
萧驰野屈指弹沈泽川一下,蛮不讲理:“你跟我走。”他走几步,像是生气,“你不认得我吗?”
沈泽川说:“不认得。”
萧驰野作势要把沈泽川扔进雪里,他将沈泽川抛起来,在沈泽川惊慌失措的时候又稳稳地接住。海东青落在他肩头,他看着沈泽川哈哈大笑起来。
沈泽川抬起头盔,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原本已经要黑下去的天骤然亮起来,风吹动萧驰野的发,周围遮挡视线的城墙尽数消失,无边无际的草野横铺在脚下。他就这样抱着沈泽川,还贪心地摸了摸沈泽川的面颊。
“我想把你藏起来,”萧驰野在风里大声说,“或者把你装在胸口的兜袋里。”
沈泽川听不清楚,他仰头,问:“你说什么?”
萧驰野看着他,照着他面颊狠狠亲了一口,答道:“我说你真好看,太他妈好看了,再也不会有人比你更好看了,我发誓!”
沈泽川捂着面颊,大声回道:“你骗人!”
萧驰野不顾他的挣扎,抱紧他,在他耳边说:“我错了。”
风停下,萧驰野倏地就长大了。他宽阔的肩膀挡着光亮,拥着沈泽川,既像是刚刚睡醒,又像是还在梦中。他解开的头发跟沈泽川的交错在一起,铺在被褥间,中间横着根小辫。
沈泽川睁着惺忪的眼,呆了半晌,困乏地说:“绑着了。”
“嗯,”萧驰野用长指拎起小辫,“结发为夫妻啊。”
沈泽川才醒,还在缓劲儿。萧驰野给他搓着背部,说:“该起了。”
沈泽川被搓得微微侧过身,正趴在萧驰野胸膛。萧驰野手上有茧子,搓起来很舒服。沈泽川眼睛都要眯起来了,还不忘对萧驰野生气地说:“你好吵啊。”
萧驰野用带胡茬的下巴猛蹭他,说:“我都要被你搞死了沈兰舟。”
沈泽川用裹成粽子的右手戳了戳萧驰野的面颊,两个人自然而然,接了个病恹恹的吻。
数日的阴雨停歇,端州转晴了。
既然虽然很谦虚,但三日后沈泽川就能按时进米粥了。小和尚站在窗边,虔诚地念着“阿你陀佛”,在萧驰野问他想要什么报酬时,他不假思索地指向历熊的糖罐。
众人都松了口气,在历熊拒绝前递过了糖罐。
* * *
屋里开着窗,沈泽川枕着靠枕,听费盛说完话。
“倘若是细作,确实不需要在身体上留下这样明显的文身,”沈泽川左手拿着元琢写的呈报,都是这几日的重要事,先生们不好自作主张,“你的意思是,他们之所以还带着四脚蛇文身,是为了跟普通蝎子区分开?”
“四脚蛇都隶属于阿木尔,自诩是悍蛇部的分支,”乔天涯说,“卓力要上战场,有文身不奇怪,但潜入的四脚蛇还有文身,只可能是担心自己被人搞混。”
萧驰野问:“犹敬怎么说?”
“刺客用的户籍是真的,樊州确实有这两个人,但极有可能是被替换掉了,”费盛说,“毕竟只知姓名不知样貌。”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孔岭稳声说,“黄册每年都要填报,即便各州衙门在核实情况的时候收录画像,也不能久存。”
但是乔天涯的猜测没错,潜入的四脚蛇为什么要带着文身?这样一旦被查,就根本跑不掉了。阿木尔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私兵,连卓力都是“借”给哈森的,表明他格外看重这些四脚蛇。如果真的是为了把自己跟蝎子区别开来,那就跟常年游荡在中博境内的蝎子有关系。
“端州距离格达勒不近,距离阿木尔更远,再快的马也不能把消息即刻传到,”萧驰野对东边的军事地图了如指掌,“哈森的猎隼都没能飞回去,这两个四脚蛇不是阿木尔派来的。”
阿木尔调兵,是对戚竹音攻击格达勒,哈森没有回援的最坏打算,他确定哈森的死讯只能是这两天的事情,因为茶石河不好渡,所以他也无法在前几天就对四脚蛇下令,时间上来不及。
姚温玉神色一动,说:“四脚蛇既然是阿木尔的私兵,就不会轻易听别人的调遣,如果不是阿木尔给他们下的刺杀命令,那就只能是有人假借阿木尔的名义给他们下了命令。”
费盛眉头紧锁:“倘若如此,那就还有蝎子,或者四脚蛇待在我们身边,他知道端州的动向。”
高仲雄总是立刻紧张起来的那个,他说:“那岂不是坏事了?此人很熟悉中博事宜啊!”
“这些四脚蛇若是久居境内,即便有户籍凭证,也会因为文身被记录在册,”乔天涯说,“他们是新混进来的。”
“衙门查得这么严,”孔岭说,“他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城太难了,得能避开近卫的检查。”
“那还真有个地方可以,”晨阳对府君微微行礼,“茨州蝎子在境内不受盘查,他们能够跟着海日古自由行动。”
海日古的蝎子原本只能待在北原猎场,受守备军的严格看管,直到他们随同离北铁骑在茶石天坑立了功,中博就此解开了对他们的束缚。如果四脚蛇是跟他混在一起,那文身的事情就能说通了。
费盛当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