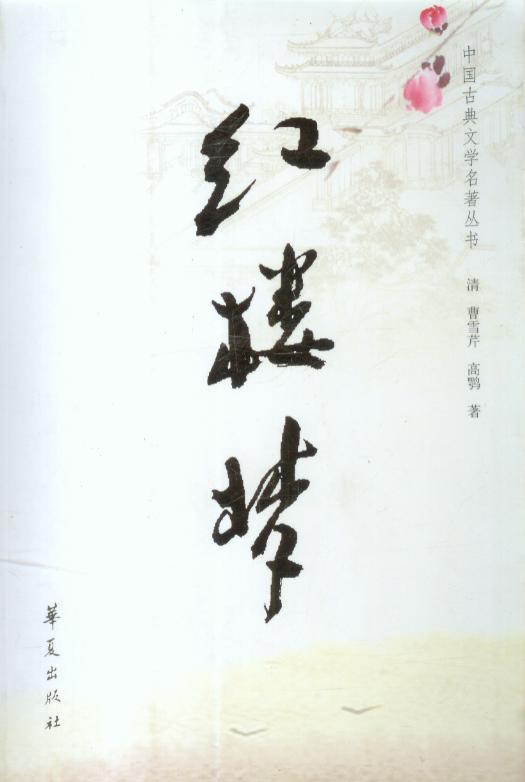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ž������է�졣ˮ�����������㣬�����ʵʵ����һ�ƣ���ɫ������ס�
�������������������Ɠ��ò��ᣬ�����Լ�����ס�ˣ�����û��������
������ҹ�����������ᵯ�ڴ����ϣ�������ͷ��յ�ƣ����ˡ���Ϩ���ˣ�����ֻ���������ķ���������ɲ�ǣ������ʱ����˿̵��˸��ij��ǣ��·������˷���ͻȻ��ӿ�����˹�����
����ˮ�������������룬һ���ӱ�����������������������§ȥ�������Dz����ˣ�ֻ��һ�Ʒ磬������ʮ����������Ѱ��������ͷһ���������е�ӵ�й���
���������������ϣ��������������Ĵ��������ζ��ţ��پ���Ѫ����ӿ����������һ���������⣬������ԭ�һ�Խ��������ʰ��������������ʼ�ոл���������ƫ�Ǹ������ܲ���������һ�졣
��������˭���������������ô���������̶�������һ�δγ�Ц�ҵ����⡣��
����Ϊ����Ʒò������������ı����������ֻ��������С������繣�÷Ӱ�ᴰ��ī�ʣ���ȴҹҹշת����֮���ã����������Ӱ�Ӷ������ɣ�
�������ڴ��ϵ��ǣ�����˺ҧ���·�й��ʲô����ŭ�⣬����˵�ޣ�������ij���ɾ�ҩ�����������ڻ��е�Ů�������������������˿̷�����������ֻҪ��ô�þ�һ�ͻ����˰ɣ��������������Լ������������Ѫ�ö�ã�
�������㡢��ſ�����������Ǻ�˿�����ʹ�����۶���������������������ƴ�����Ƶ��˴�˺ҧ�����ֱۡ������ֻص���һҹ�����������������ԽԽ���Ҳ����һ�������³���ֱ������������Ԩ��
����ˮ�ܲ������ᣬֻ�������������������䣬���ݵ�����ȥ�����������ţ�һ��һ�Ž����ǰ�Ŀ��ӡ��Դ�������������Ҳ�а���û�������ˣ���ʱ�����ƿʣ����л���һ���������������ڴ��ݼ����صӵ�������Խ��Խ���صĴ�Ϣ���̵�Ҫ����
�������ų���֮�䣬�����������Ĵ����������������Ǹ��ͷ�����ӣ�ָ�������������ļ�������붼���룬�þ���ȫ����������ȥ��������һʹ��ת�۱��߳��϶����Ѫ���ӣ�ˮ����Ȼ���˿�����������ֻ��ҧ�����ţ�һ�¡����¡���ֱ������ƣ���ߵ������֣������أ������ۻ�������ȥ��
���������ˣ���������������������Ҫ��̫ҽ�ˡ���
����ˮ�ܸ�������ͷ������ͬ���Ը�ο��һ�����ӡ���������������ϣ���Ҳ�������۽Ǻ�Ȼ�߳��ᣬ���ڹ������������������ڵ��Dz������ˣ�żȻ��ҹ����������������ע����������Щ���µ��Σ�ȴһֱû�жϹ��������ܻ�����ǰ���龳���ŷ��ݡ�������ռ��������ֻ�б������������Ƶ�����Խ���������ˡ�
����ˮ�ܸ���ͷ��ȥ������Ķ�ǣ���dz���ҵĺ������ڶ��ϲ��ϷŴ������û�ж㣬����ӭ��ȥ��ס���IJ��ӣ�������ͬ���������ˣ����ѵֵ������һҹ�´档��
�������������һ�����죬��֧Ⱦ��Ѫ�Ľ������ӣ����ڴ�߬�������ģ����ѵ����ϡ�
�����ܾúܾ��Ժ���ɫ��ʤ���������������ë��������ӹ����ǣ���ѩ�ˡ�
����������ͷŭ�ŵķ磬�����������ۣ�����������ɫ��ƽɴ�ʶ���������ô���ţ����ӵ�����һ�룬��������Ұ�ﷺ���۽�Ĺ⡣������̫���ˣ�������Щ���£���������dz����������
����һ˫���ݵ��ֱ�ӵ�������������乵ĺ��⣬�������������ڻ��������������������Ǻ��¹���������ֻ�����ɵ�Ȧ�����ࡣ������һ�£����ͷ��ش������������������ɷ�����˯��
��������ô�ˣ��������ﲻ�����������Ƭ�̣����ߵ������͵��ʵ���
�����������ر����ۣ�����������ûʲô��������η����ë���ַ��ˡ���
������Ŷ����������������ô����˵����ˮ����֪�������ѣ�Ҳ���ƽϣ�����һ�����������̫�䣬�ϲ�����ס�ˡ��������˰����̹�ɨ�������DZ��徻�����٣���Щ����÷���ʹ���ˣ����ο�������������һЦ���촽�������Ķ��ޣ����ް����ز��˲䣬�����ο����ҽ�Щ��Ҳ������ȥ���㣬��˵�ɺã���
��������������ü����Ȼ���þ������е㷢�飬�·�������ҧ�����ĺۼ��������������������������Ҫѹ���������Ĵ���һ�κ��Ȳ��������ѹ����������廬��С�ߣ��������ϵ���䦿������̲�ס���˸����䣬�����ȴ��������������������ľ���������
����ѩ�µ÷��ˣ������庮���������ص��¹⣬���ȵķ����ڸ����ϣ���Ю�����������������������죬���������������ѹ���Ѿõ�ʹ����
����ӳ��ççѩɫ����ض�����һ����ɪ��ǽͷ��֦������С��÷������Ӱ����ŷ�������һ�о�������ˮ������̧������ʰ���������ڼ��ϣ���ͷ������������ɴ�����ѻѻ���㷢�ں�Ҷ�����̿����ƺ�˯��������
����������һ���ڷ�������ָ�������ƣ�ͻȻֹ��ס���룺Ҫ���и����Ӿͺ��ˡ�
��������ͷ����㼵���Ц������ת���־��û���������Ҳֻ�Ǹ�����Ӱ��һ˲�����������Ժ������ų�ȥ������ͣ�˺�һ�ᣬ�ųٻ��ķ��Ŵ�Ե����������֧���ӻ��ڣ���˳����������ɢ��ͷ��������纽��ˣ�����ȴ�������������ڵ��ᡣ
����ֻҪ����������ʲô������ֵ�õģ���ô����
����������ο�Ƶ����ţ���һ�濫����ʪ����۽ǣ�����ž��ú��ܵ㡣
�����л�Ҫ˵��������Ȼ�����ӳ��˵㣬�ɻ��Ǹ����������
��ұ�������ȥ�Ϸǻ���ȥ��������֮������ȥ��~
���쳤Х���������DZߴ�Ѫ�߲���Ѫ�����Ǻ�з�ŷɴ��������;���~
�����إҼ
����һ�����죬��ѩ�µ������ּ�����ֵ���µ�������������ϯ�Ǵ�С����������ɨ�����ߵ����̹ݣ���Ƨ�˼���ɽ�����������á�
���������̹�ԭ��ˮ������ʱ���������ĵط�����˵����Ҳ�����Ľ���լԺ����ͷ����ů��һӦ��ȫ������൱���ɣ������������˼ҵ��̳�֮����
������������ֻ�����������ˣ�������Ц����Ҳ�У�������֪�����Ǽ�ɽ���ӵ�ʯͷ�����ǵ������Ӫ���������õĻ�ʯ�ڣ����˴��Ǯ����ϧ�Ӻ�������ǧ�����������������������ɽ�ɺ��İ�÷�������ǽ���Ѳ�����������ѡ����÷�����˷�Ļ�˵���������Ӿ���ˮһ���������ģ�ת�۶���֪��������ȥ�ˡ�
������������˵˵�������÷����һ������Ҫ����ô��ԩ��Ǯ���ɸ����������ˡ����ܻ��Ե����ӽ���������������������˴�ɽ���ȣ��չ����ĵ������ӭ��һ��ˮĥ��ǽ������ǽ�ϵ�ש�ۣ�ԶԶ�ɼ����ﻨ������ʢ�������˱ǣ�ֻ���ú����߹ǣ�������ʱ�������ġ�
����������˵����������ȱ����������ЩǾޱ�¼�������������Ҳֵ����Ǯ���ٲ�Ȼ���ָ����������������ﻹ�ó����ء���֪��ү����ô��ģ�ר�������ź������һ��Ҳ�����⼸�쿴ͷ������
����������÷���Dz�����������������һ֦�������ӵ��Ż�������ͷ�����ᣬ�������ҿ��źã��ѵ������Ҳ��ֵʲô����
���������������ˣ�ֻ��������Ц���������ϣ����˵����Ǹ����ˣ������������ŵ�����������ɫdz��ζ��Ҳ����ã�������Щ�������������㣬���Ŵ���Զ���ŵļ�������
�����Ͼ�һ����Ц����������λ���֣��㲻������Ҳ�־��Ӻ�С�ˣ�����ζ���ȷ��ֿɲ�Զ�ˡ���˵����࣬��ˮ���㣬��÷�����ĺô���ƫ������������֮�䡣����
���������˲����ˣ��ٷ��˵����������ˣ����ײ�һ�����ϸ�������������ӣ�û�ٶ�����ɣ���
�����Ͼ鲻��Ӧ���Ļ�����������˼�����������ֱ�Ц���ң������dz���������ģ�������ͷ��Ľ������ѧѧ����ˡ�
������������Ц����������Щ���ˣ����ռҺͳ�ͷ������ѧ��ѧ�����֡�ֻ���⻨�����Ҳ̫���ˣ��ߵ�Խ�����ź��㿴��������ģ����Ӳ�ֱ����Ҳ����һ��綼�����ã����ǰ����������������л���ˡ�������һ����߶�ţ�һ�潫���ϵĻ�ѩɨ����
��������˵ʲô�������⻰����ͣ�½Ų���������Ҳ��ʲô���ź��ˣ��ⲡ÷����Ե�ʵģ���÷����Ϊ����ֱ�����ˡ�������ֻ����������ȴ�������ĺô���ƾʲô�����װ���һ������������ȡ�ֶ�����
���������������������յ����飬���Ǻ�����ģ�����ͷ����ɨѩ��Ҳ�����ٲ��졣
�����Ͼ�æ������Χ��Ϊ���������ӵ��������������˵������ϸ���»��ˡ���
����˳��̨���������������ȥ������һ�ַ������������仨������ֻ��ָ���ǰ���ᱡ�紵�ۣ����ڰ�ãã��ѩ��������ѱ����١���
�����������ݣ�̿�����ü���������������Ƶģ����������ٰ��������졣������˶�������ֻ���˼��������磬��ɫխ���̰���ϡ���ѩӰӳ������ϣ��ĵ�Խ���ǰ����˪������վ�����Ҳ����������ֻ�������ſ��˿����Ĵ�������һ�顣
�����ⷿ�ﻹ�氲����Ӧ�Ŵ��ⲻ�Ͽķ磬�·��������������֮�⡣����������£�Ż��裬�ۼ�֦÷�������������������ڵ�С�ƣ��Ǻε��������£���֪�������ӵ����ˣ����꺮�������ʱ������ʲô���Ĺ⾰��
������ҡͷЦ��Ц���ڶ��ڵĿ���ǰ���£���Ѿͷ�ǹ�����衣
������������ү����ȥ�ˣ���
���������˻���֪���ɣ����������Ƕ����ĺ����ӣ�ǰ������ү��������Ҫȥ����ɽ�ϴ�Χ������籸��������û�������˾����ˡ���Ѿͷ����һֻ������룬�˶������Ĺ��ڸ�ǰ������ү����ǰ˵�ˣ�Dzū澹������̣�������ʲô�Ը���ֻ�ܸ��߽�����ǡ���
����������˲����֣�ȴ���ȣ�ֻ����¯ů�ţ����������������������й���Ҳ���¶�����������
������������һ�֣���ײ��ʲô��Ц��Ȥ�°㣬�������������ү���·��˲����أ��ⲻ�Ž���������������ã�˵���캮�ˣ��ܵ��и��滻����
�������ҵ����Ѷ��Dz������ģ����������ʲô������˭��Ҫ���������˴�ȥ����
�������Ķ��Ļ������ǿɲ���Ҫ�������������궬�죬Ҳֻ�����˼������ġ�Ҫ�����������ү�Է��˵Ķ��������ǰ��δ���ˡ���
��������û�д�תͷ�泯�Ŵ��⣬ѩ�����ڰŽ��εķ����ϣ�����̾�˿�������
�����������ظ¡���һ������ʲô����������������������ڶ���Ľ��ȼ��ϡ������������£�����������һ�����ʲſ������ֻ����������Ͼ鲦����ᢽ�����һ�ۿ����������¹ҵļ��ӣ�Խ��Խ���죬��Ȼ������������������ƣ��Dz����������Ĵ��и��𣿡�
�������ţ��������������IJ�յ��Ҳ�����߹�ȥ�������������������һ�ۣ�����Щ˵������ɻ���ֻ��Ƥ���ĵ�ͷ����ˮ�ף���������ڣ���Ȼ̾�����������һ����ⶫ�������һ����ڳ�ױ���������һ������ˣ������һ�����Զ������
���������ϣ���ɲ�����ˡ����Ͼ�ϲ������Ц����������˵�����ˣ�����Dz��ţ�Ϊ���ë���������˰�����ġ���
��������˭�������ģ������������и����ë���ع�������Ҳ�̲�ס¶��ϲɫ����
��������ժ�¼��������ӵ���ץ�����ѿ����ѣ�һ��һ�Ŷ������档ι�˰��죬����ת��ͷ˵����������˭����֪����ү����Ū���ģ����������ᱳʲôʪ���ɵģ�Խ�������˷��һ���������ȶ����ˣ��ҿ������Ȱ����ֻ��ĵ��������ү˵ʲô�����ϣ�������͵��������úô���ι�˰��꣬����������������
�����Ͼ�����һ�룬����Ц���������ˣ������Һ��ģ��������ǹٱ������������˸������ˡ�����������ȥ�����ݣ�Ѱ������Ҳû�Ҽ�����
��������˵�أ�ԭ������������ġ�������Ҳ����Ц����������˵���ݼ��ڣ�������㳤��ʶ�ˡ���
��������ֻ��ЦЦ����Ҫ˵ʲô������˵��������������ͷ�����룬����ȥ�����Ľ�צ�ϵ������������λεĽ���Ȧ��������������ף�һ������һ���������������ҡ�
������������ˣ����������ġ�������˵�˾䣬�����ͬ����һ�㣬���㻹û��Ӧ������������������������ȥ������ү˵�����������ˡ���
������Ҳ���������Ѿ���˼���ҳ�����飬�����ˡ�
������ȥ���ܶ�ʮ���������ɽ��·�Ϸ�ѩ���裬�����ߵû���˳������ԯ���Ǹ���ʮ����ĺ��ӣ�ͷ������Ƥ�ñ��һ������ɫ�ķ����������紵���е㷢�ࡣ��ԭ���Ի�������������ɽ������ʮ���죬�����¿�������������ȥ����ɽ��·��
�������ȣ��ϸ�����������������Ե��̴ӣ�����˯�����Եǵǣ���ǿ������ֻ�ۡ�
��������������������ȥ������ĥ�ţ�զ����ȥ��Χ������
�������˸Ͻ���ס�����죬������˿����Һ�û���������⡣���꣡������ߺ�ȣ��ɲ��ɣ�������������˲��£���Ȼ�ٲ�������ͣ�����ô���ɶ����
������ԯ���Ǹ���ʵ�ˣ���������˵��Ҳڨڨ��û����˼����
������ʵ��������Ҳ������������ԥ�˰��죬��Ȼ��ð����һ�䣬�����²�������֪���������룬��ү���������ӹǣ��ľ��������ڣ���������Χ�Ե���ţ��ó��ǰ��°��ˡ���
������ԯ�IJ����⡰Ŷ����һ�������������ӣ�æȡ�����̵ݹ�ȥ�����˽����̴���һ�����еij��ţ�һ����������ָͷ��������ǰ�Ȼ�������������Ϊ���������������ү���³裬���Ǽָ���ͷ����ү�����ӣ����¾Ϳ���ն�ˣ�˵ʲôҲҪ����������һ�⣬�źû�ȥ����ǡ���
����������������������˵�����������ֵ����ף�ȥ�˲��¼ɻ䣿��
�������ɻ䣿�����˺ٺ�Ц��������˵�������б���Ҳȥ������ͷ�磬����ү��������ģ���˵���ߣ����ǹ���ɽ�»����˲���Ҳ�ܲ��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