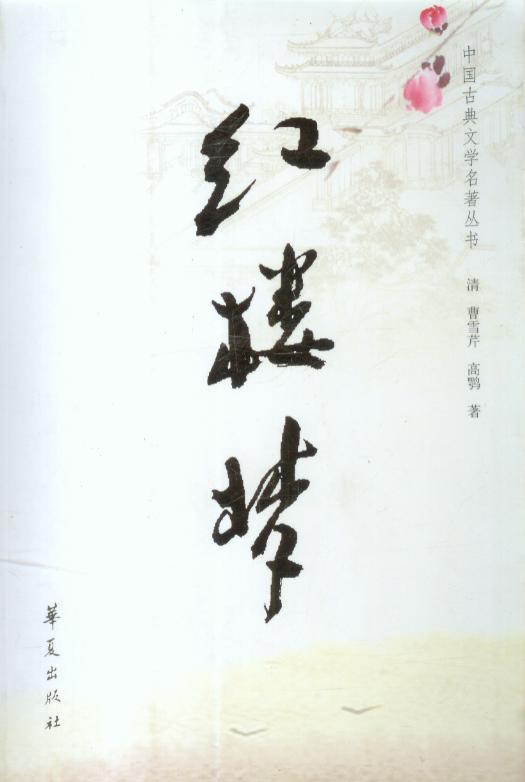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红楼梦同人)红楼·画中人人-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推开狱神庙的铁栏,一阵阴气自幽深的过道扑面而来,众人不由缩紧脖子。顺着台阶下去,过道两旁又狭又窄,也许是年久失修的缘故,墙上赭红色的壁画,已经剥落了差不多。方伯跟在后头,大着胆子瞧了一眼,只见墙上乱糟糟的,有红衣捉鬼的钟馗,有青面獠牙的夜叉。任他向来不信什么阴司报应的人,此刻见了,也冒出一头冷汗。
“姓贾的,有人来找你了。”狱吏下开锁子,向里头喊了一声。
地上铺着干草,有人歪歪倒倒蜷在火塘边上,用破席遮了脸,也看不出来是睡是醒。水溶站在牢门外头,忽然停了那么一刻,他不是不想看,是真的害怕了。他不知道越过眼前这道门槛,自己会说出什么话来。
“要不,王爷觉着为难就不去了。”冯紫英看他撑在铁栏上的手,悄声无息的收紧。
“不,不关你们的事,还是我自己来。”水溶定了定神,抬起脚步慢慢向牢里走去。
墙角的人听见动静,懒洋洋翻了个身,似乎这世间的一切,已经让他提不起兴趣。窗户还开着,鹅毛般的雪絮子破空而入,打在他睫毛上,湿涔涔的化开了。无奈这里没有生火,才站了一会儿,便觉得寒不可禁。
“你是……”那地上的男子抬起头来,眼中神光涣散。
水溶心中一动,扶着他的肩头问:“宝玉,你连我都不认得了?”
“你是?”男子看了他几眼,觉得有些面熟,很久之后才费劲的弄清楚他是谁,“是王爷呀,没错,王爷终于来看我了……哈哈……”
众人被他笑得发慌,心里更没了底,水溶在他身前蹲下来,脱了自己的貂皮大氅,为他披在外衣上。黑貂皮油亮如缎的光泽,一时让宝玉暖和起来,他还嫌不够,恨不得整张脸都埋到大毛出锋里。
“饿了吧?不要紧,等吃饱饭就不冷了。”水溶看着心疼,命人打热水来给他擦洗,又叫方伯把食盒提过来,一层层打开。盒里都是些家常小菜,火腿炖肘子、油盐炒的枸杞芽儿、酒酿清蒸鸭子、腌的胭脂鹅脯、还有几碟子粉菱糕,他记得以前宝玉有爱吃甜的毛病。
“喏,这是你吵着要吃的莲蓬汤,早上赶得急,走了一路,也不知道凉了没有。”
宝玉眼前一亮,慌忙夺过来,狼吞虎咽的就往嘴里扒。两个腮帮子鼓着,两眼直瞪,众人不由想起以前,他含着金汤勺儿的情形,可能从小到大都没遭过这罪吧。
“噗……咳咳……”想是喝的太急了,宝玉一个不留神,呛得直打嗝。
水溶看他这样,又是心疼又是好笑,只得伸手拍着他的后背,好使他气息顺畅些。“别着急,慢慢儿吃,没人跟你抢——方伯,你去给二爷倒碗水来。”
方伯干脆利落的应了声,一溜小跑去了。这边宝玉喝了两口汤,便犯起渴睡来。好不容易扶他躺下,经过这一番折腾,水溶的心情没有好减,反而更觉得烦闷不堪。
怎么说?照这情形看,怕是能瞒一时算一时了吧。
他正在心里盘算着,就听宝玉“啊”的一声叫唤,突然坐了起来,抓着水溶大喊:“玉!我的玉不见了,你们谁拿了我的命根子?”
“什么玉?丢哪儿了,先别急啊。”水溶也被他摇得发晕,在地上团团找了一遍,什么都没寻见。眼看宝玉急的满头大汗,只得安慰道:“你再仔细想想,丢哪了?”
韩琦也凑上来问:“什么玉?你脖子上戴的那块么?”
“不不,”宝玉摇摇手,头摆的跟拨浪鼓一样,“是黛玉,我林妹妹呀,你们把她藏到哪儿去了?”
这一问,仿如数九寒天泼下的一瓢冷水,刹那间被冻得死死的。众人都垂着头,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宝玉从他们的沉默意味中,更觉出些蹊跷,只将目光投向水溶:“你们见过她么?对了,查抄园子那天,王爷你也去了。她人在哪里?一天吃几回药?身体可好些了?”一连串问下来,还是没人搭理他,宝玉也不算傻,仿佛有了预感般,反复叨念着,“她死了是不是?你们都瞒着我,对不对?”
“不是。”韩琦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你也别瞎猜了,她活得好好的。”
“她还活着?”宝玉却像没听明白,“她活着为什么不来见我?定是她死了,你们拿谎话来诓我的。”说着呜呜地嚎啕大哭起来。
众人被他闹的头皮发麻,彼此换了几下眼色,还是没理出头绪。终于冯紫英忍耐不住,咳嗽了一下,道:“宝兄弟,你也不必担心,其实她……”
水溶一把伸臂拦住了他,不容他再说下去。
“这有什么可瞒的,索性都跟他说了吧。”韩琦到底也没忍住,转身对着一脸茫然的宝玉道,“宝兄弟,实和你说罢,你就死绝了那份心,她这辈子都不会来了,此后跟你再没什么瓜葛。林姑娘她……在你坐牢的这些天,已经被王爷纳为妾室,如今是北府里的人了。”
“你说什么?”宝玉瞠目转向水溶,几疑自己听错,“这、这可当真?”
水溶避无可避,只好迎上他愤极交加的目光,点了点头。宝玉心如刀绞,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猛地抵在墙壁上,阴潮的墙皮泌进他的肌肤,让他冷冷打了个寒噤。
宝玉双目通红,双手紧紧扼住他的脖子,犹自不解气的使劲:“你骗我,她那么干净的一个人,连你的东西都不肯要,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委身与你?”
“宝玉!”柳湘莲一迭声地叫着,与冯紫英左右两个抢上前来,都去掰宝玉的手。然而他益发动了气,力气大的出奇,铁箍般怎么都扳不开。眼看水溶雪白的颈子上,涨起血色的潮红,那细脉与青筋隐隐都暴了起来。
贾芸也看不下去,生怕真惹出祸来,便在一旁劝解他:“宝叔你冷静冷静,事已至此,你就看开些吧,这其中的缘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清。王爷他,也是为了你好……”
“我不信,你们夺走了她,还口口声声是为我好,天下还有这不公等的事吗?”宝玉看他唇色皆成了惨白,气得连声调都变了,手底下不轻反重,恶声恶气地说,“你根本不配她,像你这种生在王权富贵中的人,只知道经济学问,懂得什么是情,什么是爱?林妹妹的性子,我最了解不过,一定是你逼她的对不对?”
“……我,没有逼她,信不信那也由你。”水溶在他股掌之间,岂能反抗,只低头盯着他满是血丝的眼睛,拼尽全力挣出一个笑,隐忍住喉头的咳嗽,方才缓过劲来。
“没错,我自来什么都不懂,所会的,也是些无情无义的手段。这次的事,我本不打算冒着降职贬官的风险,去搅你们那滩浑水,可她既然开口了,就容不得我不顾忌。你不妨想清楚,这条命是你欠她的,我并不想救你,只是不愿忤她的心意。”
“够了!就算你有千般理由,除非是她亲口说的,我一个字也不信。”
“不信么?”水溶忽而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方白绢,抖开来一看,原来是条旧手帕子,上头的墨迹淡如绛色,还有些斑斑点点的泪渍。
宝玉的脸色愕然变了,他却像全没看到似的,淡定地道:“你既说最了解她不过,那么这绢子——你总该认得出来吧。”
“她……她连这个都……给你了?”宝玉劈手抢过去,由疑惑转为震惊。这帕子还是他挨打那年,托晴雯私下传给黛玉的。那绢上的诗,四句,二十八个字,就是烧成灰他也认得。可山盟虽在,这摧肝裂胆之情又如何能托?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这诗当年,是写给你的罢?”水溶说着回头笑笑,淡静的眉眼垂下去,心里一时有些嫉恨,又有点羡慕,到最后也说不上是什么味儿了。
“你不配提这首诗,你根本不懂她!”宝玉的声音在背后绝响。
水溶转过身来,冷笑:“你又懂她多少?这世上没有几个人配得上,你且问问自己如何。你以为凭你的身份,就能护得住她周全?”
宝玉“卟哧”笑了出来:“是呀,我是何等草芥,怎么护得住她?哈哈!我算什么……哈哈哈……”
☆、廿叁
水溶等他笑声停歇,沉默了一阵子,道:“你知道我为何要这样做?若你真能疼惜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我甚至乐意成全你们。可你能做到吗?能吗?”
宝玉不妨他有这样一记喝问,不由微微愣住。
“你只当陪着她顽笑,吃什么要什么,全都依着她,便是对她好。她那样任性惯了的人,心里想什么,你真的在乎过吗?当初不是我赶得及时,哪里还有她的活路?若是她不幸死了,对你来说又有甚么好处?”
“你说这些,无非是想让我离了她,好成全你的心思。”宝玉转身轻笑,一双眼睛沉沉地盯着他,语气却透着慑人寒意,“我知道王爷想取我的性命,你大可不必如此,我这条贱命,早就不劳费心了。”
水溶移开目光,不由柔和了语气,道:“宝玉,你我什么时候,已到了这个地步。我坏了你的姻缘,自然有悖人情,可就算有千万个对不住你,也该替她想一想,她还那么年轻,今后靠谁来指望,这些你想过吗?”
这话听来仿佛是莫大的讽刺,宝玉没等他说完,便笑了起来:“指望谁?你们挖空心思,不就是想拆散我们两个,先使出那调包计,让雪雁骗我成了亲,好纳她入怀吧,等到木已成舟,也不由得她不答应。只怪我瞎了眼,居然拿你当这世上最亲信的人,哈哈哈,真是可笑至极……”
水溶听出他话里讥讽之意,知道多说无益,敛容道:“随你怎么想,我问心无愧也就是了。”话虽如此,他心里到底还是私德有亏。可又有什么办法,这场三个人的天意,一直都是他在作茧自缚。枉他还自以为性子淡定,做出那些清高姿态,原来未尝不是在欺哄自己,心里微痛。
“放心去吧,我不会亏待她的。”水溶叹了口气,斟酌着说,“你好自为之……”
宝玉抽搐了一下嘴角,慢慢绽出个意味深长的笑:“王爷如意了?”
“没错。”水溶盯着他,老实不客气地说。
旁边的人看他们脸色不对,但见势头不妙,忙上来劝阻:“快走罢,时辰快到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正说着,狱吏已经过来高声催促,水溶见情势危急,也来不及思索,只将宝玉一把拉起来:“快换衣裳,牢里有人顶替你,出去了就别再回来。”
宝玉哼了一声,说话间挣开他的手,“你要杀便杀,这会子倒来充什么好人?”
“宝叔,眼下不是赌气的时候,外头几十条人命都系在你身上。” 贾芸急切地说。冯紫英也有些急了,忙道:“是啊,他们生死是小,要以大局为重呐。”
“我死了,不正遂了王爷的意?”
“你到底想干什么?”水溶几乎是真怒了, “让你死在这儿,我给谁交待去?”
这一声怒喝如雷殛在心口上,慢说是旁人,就连宝玉也没见他发过火,一时也愣住了:“没想到,你还真在乎她……往后她受了半点委屈,我做鬼也不会饶了你。”
众人听他话里有些许松动,都暗舒了一口气,这时柳湘莲找出备好的衣裳,急忙替他换上,又叫那个顶替的死囚犯进来,按原样躺在牢床上。
临走之前,他从兜帽中探出头,与水溶对视了一眼,面上很静,看不出是喜是悲,宛然青灯古刹中的泥尊一般。纷纷扬扬的雪粉,永无停歇地下着,天地间轻寒扑面,正如初见那天,眼睛里仿佛也下着雪。
就在那一瞬间,水溶突然有些自嘲的想:这会是真的如意了吧?
“唉——”破空一声长叹,隐隐中有人念了句佛号,伴着时断时续的木鱼声,由远走了过来。众人放眼看去,只见漫天漫地的大雪中,走出两个虚渺的人影。近了才看清是个癞头和尚,后头跟着个跛脚道人。
“蠢玉啊蠢玉,你尘缘终难善了,还不给我滚回去!”
宝玉似有所悟,喃喃的说:“滚……到哪里去?”
“青埂峰下,归彼大荒之地,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是吗?从来处来,到去处去……嗬嗬啊哈哈哈……”他忽然放声大笑,直笑得眼眶泛酸,泪水毫无预兆地淌了下来。心中不再是恨,而是了然,带着一点快意,却是从未有过的舒坦。
众人看他散着衣襟,一双赤脚连鞋也不曾穿,大咧咧地就往前走,大有疯魔成活之态。柳湘莲想去拉他,却被水溶伸臂拦住,隔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道:“由他去罢,走了也好。”
那癞头和尚听见,斜了他一眼,神情极为轻慢:“这位施主,倒是想得开啊。可惜浑不知自己业障重重,反有心替他人而叹,真是可怜可笑。”
“哦,大师何出此言?”水溶笑了笑,却也不动气。
和尚双手合什,念了声佛号:“我笑施主虽富有四海,心胸不是很开豁,过于拘泥于男女俗事,还不及我这个和尚快活,不是很好笑么?”
“大师乃化外之人,我这凡夫俗子,如何能比得。”水溶淡淡一句,本想敷衍过去。
那和尚摇头道:“非也非也,我看施主的面相,到是个出世的人物。只是宿缘太重,着实可惜了。所谓怨长久,求不得,为了一时的贪欢爱欲,到头来何必何苦?不如放下了,就此无挂无碍,岂不自在?”
水溶安静地听完他的话,不由一笑,道:“我虽不懂,大师所说的佛家七苦。既然是人生肉长,又如何能免俗。恕在下心魔太重,怕是让大师失望了。”
“唉!”和尚看着他,无可奈何的摇摇头,长叹一声道,“你不听也罢。”
说完抬脚就走,随着那跛足道人,追了宝玉而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融在雪影里。
“王爷在笑什么?”韩琦站在他身后,看了老半天,还是没看明白。
“没什么,”水溶吁了一口气,低下头道,“我到底还是不如他。”
待他们回到府邸,已经过了酉时,天色也将黑下来。为了防着外人知道,车马不从正门走,只乘了一顶素轿从西角门进来。小厮远远就看见了,念了声阿弥陀佛,赶着过来相扶。水溶下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