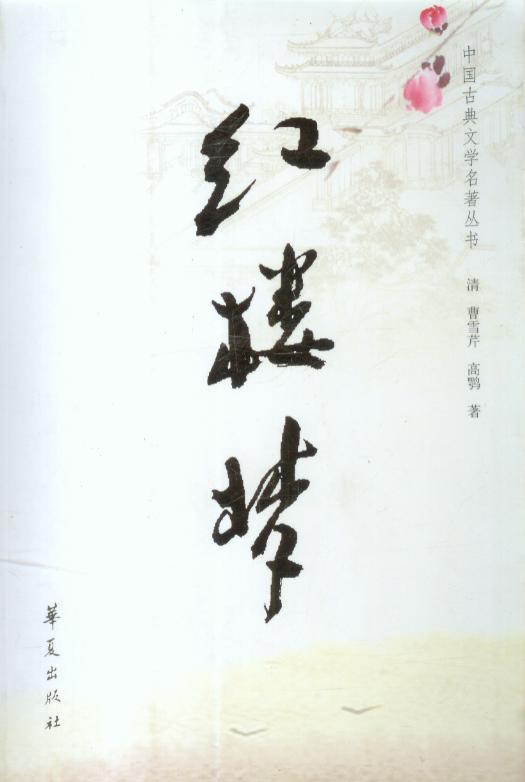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红楼梦同人)红楼·画中人人-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罗氏的闺名叫锦娴。贤良恭谨的比名字还过分,平时不施脂粉,穿戴首饰一应从简,连北静太妃都看不过去,说叨了她几次,才略有改观。成婚三年,水溶对她不可谓不好,只是从来不唤她闺名,连“夫人”两个字也甚少提起。外人看来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只有罗氏心里明白,他从来不曾正眼看过她一回。
有了宰相罗邕的协助,水溶在朝堂上顺风顺水,以前说他结党营私、惑乱朝纲的闲话,竟再也没人敢提。于是他活得越发坦然,闲了便莳花弄草,请些文人高仕到府上来授业清谈。
北静王府素来清简,平时没有觥筹交错、歌舞狎戏,可照样吸引了大把权贵来捧场。就连号称养门客三千的忠顺王府,都难以望其项背。忠顺王是三朝元老,笼络的人脉盘根错节,大有权倾朝野之势。皇上一时拿他没法子,便趁机拔擢水溶,将他推到风口浪尖,才设了与罗家联姻的圈套。
看似天大的恩宠,水溶拒绝不得,只能从善为上与忠顺府刻意疏远。然而官场的道理,他也不是不懂。厌倦了大小官员迎来送往,索性闭门不出,图了清静二字。
众多权贵里,唯一开罪不起的是金陵贾家。贾不假; 白玉为堂金作马。
贾家世代官宦,到了当今这一朝,家声已经煊赫到极点。去年三月,四皇子娶了荣国府工部员外郎贾政之女,封为元妃,贾氏一门愈发荣耀。
同朝之间总是要应酬,女眷们来往,罗氏去四皇子府里拜贺,回来夸元妃如何如何了得。那个叫元春的女子,水溶只见过一次。便是敕封王妃那天,隔着层层纱帷锦幔,她端然坐在后面,鬓上斜插着一支九龙迎凤钗,容貌虽丽,却也无甚特别之处。然而她低头的瞬间,眼角不易察觉的哀伤,让水溶心头一震,无端忆起成亲那晚同样刻骨无奈的冰凉。
原来,都是哀莫大于心死的人。
不知什么缘故,他对贾家渐生出某种特殊的感情,却难以言表。宁国府少奶奶秦氏过逝,他想了想,还是以世交之谊的身份去拜会。
那天长街十里,缟素满天,压地银山般铺盖而来。纸钱洒到水溶身上,像一场微寒的细雪。那是他第一次与贾宝玉见面,隔着漫天的纸花,那么干净的面孔,眼睛里仿佛也下着雪,看久了让人觉得寂寞。
他听见自己心底,低叹了一声,果然是块宝玉。
☆、叁
夜里风吹得紧,借着月光,隐约可以看到后墙上垂挂的绿萼梅。据说江宁巡抚听闻北静王极爱梅,从孙陵岗的梅山上挪了百株,托水运送到京城。此时花苞初绽,正是秉烛赏雪的时节,煞是好看。
水溶白天受了风寒,夜里睡不安稳,王妃罗氏闻声进来,见他披着薄被咳个不停,双颧也泛起一阵病态的潮红。罗氏看了眼墙上的自鸣钟,已是二更天,上夜的丫头们早都遣散了。这会子叫大夫也赶不及,只好匆匆倒了碗热茶,递到榻前。
“怎么病的这样厉害?王爷再撑一阵子,妾身卯时就去请人来。”
水溶浅浅笑了笑,道:“不碍事,我是伤了风寒,每年冬春都要熬这一回,躲也躲不过。吴太医是宫里的人,总不好老是蛮烦他。”
罗氏摇头:“王爷这是说的什么话,您贵为千岁,请他来便是给他赏脸,难不成还要看人脸色。咱们府里虽是清简,这点银钱还打赏的起。”
水溶知道她意会错了,也不愿多解释。如今朝中争斗愈烈,若让人察觉他体质不行,难保不会有人倒戈。忠顺王派吴太医来伺候他,明里暗里做了不少手脚,只怕哪天药里下了□□,他也不会觉得吃惊。
“罢了,自己的身子,还用得着别人操心?去把书案上那方砚台拿来,我写个方子,你让琪官照样抓来就是。”
听到这个名字,罗氏没来由的一震,张了张嘴却不知说什么。去外间取了东西,扶他坐起来,水溶倚着狐皮靠枕,神情淡了下去,遏住几声咳嗽。
握笔的手有点儿颤,墨已经干了,往砚台里续了些水,慢慢研磨开。湖中的紫毫笔,徽州的宣纸,用起来得心应手。
水溶提笔写下两个字“当归”。白纸黑字,遒劲如刀,他习惯中锋用笔,又是擅长的楷书。写了两笔,纸上的墨已经洇成一大片,罗氏扶住他摇摇欲晃的身体,急切说:“王爷歇歇,想说什么,妾身代笔就是。”
“不用了,明天叫琪官进府来,我当面跟他说。”
“有什么话,连我也要瞒着?”罗氏小心翼翼看着他的脸色,“妾身听说,王爷在东郊紫檀堡,为了他置了几处田产房舍。这些妾本不该过问,可琪官毕竟是个戏子,外头流言蜚语的,只怕坏了王爷名声……”
水溶摇头笑了笑,重新提起笔,蘸着墨将写过的字重重抹去。
“我见琪官,不过是爱听他唱几出戏,给他置田产,也是怜他无人照应,除此之外再无别念,是你想多了。”
不等罗氏开口,他已经咳嗽着挥手,“早些歇着吧。”说罢,拥着薄薄的衾被翻身睡去。罗氏在原地站了会儿,觉得气氛如此沉闷,屋内终归安静下来,只有红烛无声垂着泪。烛火微微跳动,照在牙床青色的纱帐上,寂静如死。
罗氏沉默着,某些感情一直深深烙在她眼里,可惜他从来视而不见,她只是年少时攀附向上的青云梯,为他置换名声,招揽权贵的工具。这些罗氏未尝不明白,他这样的人物,是断不能把心思放在儿女情长上。
可她有时候想,若一辈子死心塌地对一个人好,总有一天,他会知道,就像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终归会爬到墙顶的。
天寒地冻,鹅毛般的雪絮打着旋,轻轻弹在纸窗上。
屋里生着炭盆,温暖如晚春,烘的人骨头发酥。暖红的火苗不断蹿高,银吊子里黄芪、当归、枸杞、丹参、赤白勺、川芎细细煎熬,满室药腥味。
床帐垂落一半,束起一半,碧沉沉的天青色,恍惚一潭静水,在眼前荡漾。
十二折的薄纱屏风,遮住了隐约起伏的喘息声。过了许久,少年撑起身子,将湿汗的长发向后拢了拢,露出婉约的眉目来。榻上的男子却是折腾累了,伏在靠枕上,淡淡闭着眼,极其倦怠的神情。
“玉涵,你今年十几了?”
少年哧地一笑,咬住男子纤秀的锁骨,轻轻啃噬着:“ 莫非王爷嫌我老了?我是正月初四的生,过年就十七了。”
半晌没有动静,蒋玉涵伏身过去,以为他睡熟了,却听水溶低声道:“这么说来,贾家的二公子与你同岁。韩琦、冯子英也都不算大。”
蒋玉涵心里吃醋,脸上也带了三分,环手扣住他的腰道:“什么真家假家,贾政如今是工部员外郎,打他家公子哥的主意,怕是白费心机。”
水溶挂着淡笑,手指在他唇边轻轻拨弄:“这也不打紧,宫里漏来消息,皇上怕是不行了,若是熬不过开春,你想想,那么些个皇子王孙,谁能得了便宜?”
蒋玉涵一愣,不由停了动作,恍然笑道:“原来你亲近贾家,是为了四皇子。可我不明白,王爷你在朝中根基不浅,即便乾坤易主,忠顺王也不敢轻举妄动。你又何必屈尊降贵,去讨好一个五品小官。”
水溶仰头闭着眼,呼吸匀净,缓缓道:“ 工部主事虽是五品衔位,兴管土木水利,掌的都是实权。新皇登基,怎么都会用得着他。贾元春又是皇四子的正妃,一旦有机会,难保不会统掌六宫。”
蒋玉涵默然点头,继而笑道:“还是王爷想的周全,奴才愚钝了。”
“你是第一等的聪明人,只管哄着忠顺王高兴,哄的他遂了意,我自不会亏待你。”
阴沉的天光,从窗牗间照进来,屋里罗帐低垂。衬得水溶目光深邃,有种病态的苍白。面上挂着三分笑,一双翦水瞳修长雅致,却是极冷淡的表情。蒋玉涵骤然觉得浑身发冷,揽住他的脖子,将脸埋到他肩窝里:“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守着你。”
“这又犯什么傻?忠顺王待你不好?”
“好?那个老骨头已经不像人了。”蒋玉涵双唇颤抖,撩起衣袖,白细的手臂上满是青紫淤痕。“王爷,他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埋伏在府里那么多年,万一他哪天知道我是你的人——”
水溶只是笑,抚着他披散的发丝,宽慰道:“你乖巧惯了,太慎重反会露出马脚。以你的样貌,这样跟了他,心里自然不痛快,不过既然是逢场作戏,你又何必连个笑脸都舍不得给他。”
蒋玉涵怔了片刻。对面的人,颜若春水心如明镜,眼睛却从来不笑。
“有人心里不痛快,脸上便挂着笑,王爷对我,何尝不是在逢场作戏?”
水溶唇角一动,倒真再也笑不出来。蒋玉涵揽过他消瘦的肩,冷不防从腰底抽出一条大红汗巾子,歪着头说:“王爷若真疼我,就把这条汗巾子赏给小人吧。”
那汗巾子是茜香国所贡之物,皇上清点大内库存时,赐给他的封赏。水溶嫌它颜色俗鄙,一直不肯用,如今蒋玉涵开口,便随意敷衍道:“你喜欢就好。”
半个月后,腊梅花还没开败,宫里就传出龙驭宾天的消息。大殓之日,皇四子于承乾宫继位,原本的嫡传太子随先皇殉葬,也有人说,是被新皇用金屑酒赐死的。
第二年正月,贾元春入主凤藻宫,加封贤德妃,地位仅次于六宫之主。贾府铺张生事,特意盖了所省亲别墅,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煊赫到了极点。
元宵夜,家家鞭炮齐鸣,西洋引进的烟花爆竹,不断在天上炸开。
水溶推开窗,春夜的风依然冷,吹得他的官袍高高扬起。
他抬手揪紧了衣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喧闹的夜,竟比往常更寂寞。
太子死的当晚,月色凉薄如纸,他亲自将那杯毒酒,送到东宫里,向着那满脸惊惧的年轻人,微微一笑:“喝了这杯酒,黄泉路上好做人,保重。”
多年以后,在某些极为静谧的夜里,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倒在血泊里的面孔,金屑摇荡沉浮,沾满了他的手。
转眼春去夏来,天气渐渐噪热了,不觉已到了夏末。
八月初是贾府史太君的寿辰,东西两府齐开筵宴。请帖发到北静王府,水溶不好推辞,虽说与贾家交往甚密,亲自去还是头一遭。
西边荣国府多是女眷,男子不便进去,只安排了王妃公主和几个诰命夫人。罗氏早听说荣府里的大观园风光旖旎,堪比帝王苑囿,一直有心想去。水溶派轿送她到西府门口,自己去了东街的宁国府。
作者有话要说: 这章可能争议大,关于“茜香国汗巾子”事件,我一直都觉得是个伏笔,北静王和蒋玉涵之间,很可能有暧昧关系。清代男戏子叫伶倌,即有陪酒暗娼的习俗。我这里将蒋玉涵设计成,潜伏在忠顺王府里的暗线,后面将有重头戏。
☆、肆
宴席开在露天中庭,东府地方宽敞,轿子匆匆赶到时,已然迟了。
拨开紫光绨的纱幄,水溶欠身出轿,前头两个掌灯的小厮引路,一路脚不敢停,穿过月华门洞,再过十曲九折的抄手游廊,就听见隐隐的歌管之声,隔着老远飘了过来。
戏台设在湖上,因是家宴做寿,特地请了金陵城最红的昆曲班子。夜色里依稀有伶人咿咿呀呀的唱,和着鼓乐笙簧,荡出几分醉意。
才走到廊角下,有人东倒西歪的出来,正和他撞个满怀。那人辨出是水溶,晃了晃身体,站稳了笑道:“可拿住了,今儿这顿罚酒,你可不能逃了。”
水溶见是乐善郡王,微抬起嘴角,露出难得的笑意。席上高朋满座,都是些相熟的面孔,挨着南安郡王和永昌驸马坐下,众人等他来迟了,哄然闹着要罚酒。
早有伶俐的丫头,捧着酒盏跪到他身前。水溶面上温和笑着,接了过来,沾唇抿了一口。席间笑声四起,戏台上的小旦挽着水袖,自顾自地开唱,却已沦为欢宴的背景,无人再听。
一时间觥筹交错,都已至半酣,众人有了醉意,谈笑也放肆起来。
这种酒肉场合,原没什么意思,左边的冯子英和永昌驸马相谈甚欢,说起边关的战事来,声音很大。水溶在旁边侧耳听着,他性子沉稳话本不多,客套过几句便缄默不语,也不插言。
这时候已过了酉时,天渐渐沉下来。台上的锣鼓班子悄然撤去,换上清一色的弦子琵琶。原本喧闹的场面,顿时安静不少,食客们以为出了什么乱子,纷纷探头观望,就见后台的红绸布一掀,新戏又开锣了。
“望晴空冰轮乍涌,步香阶风扫残红,牛女星横断太空,团圞月偏照孤茕……”
水溶听了半晌,才听出是出折子戏,选了《西厢记》里张生琴挑崔莺莺的片段。
唱青衣的是个年轻小旦,功夫不见得有多好,只称得上字正腔圆罢了。那个唱小生的扮相倒十分惊艳,身量不高,眉宇间有几分熟悉。趁着开戏的工夫,两个官员闲聊起来:
“这人是谁,生的这等俊俏,以往怎么没见过?”
“亏你白长了双眼睛,连他都不识得,那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琪官麽!”
“原来是他。从前在弋阳班学杂耍的时候,倒也罢了,这几年没见,竟然成了红角儿。”
“你可莫要小瞧他,人家虽是戏子,吃的可是忠顺王府的俸禄——”那官员话到嘴边,却忍了几忍,眼风偷瞟向右边,不远处的水溶恍若未闻,一口一口品着酒,倒是他身畔的韩琦坐立不安,拿袖子擦着额上的汗。
“这话怎讲,快说明白点儿。”
“你还不知道么,前阵子忠顺府丢了琪官,王爷派长史来贾府索人,宝二爷还为这挨了顿打。你想想看,他若是一般风月戏子,值得贾老爷这样动怒?”官员说着故意压低了嗓音,凑过去嘀咕了几句,那人顿时茅塞顿开,露出惊疑的神色,也不敢追问了。
湖上锣鼓喧天,映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一台戏正演到□□。席间的笑声更厉害,有人醉意半酣,咬着耳朵轻声说笑,竟活脱脱比戏文里还热闹。
这时宝玉从人群里挤过来,边走边笑:“王爷原来躲在这里逍遥,叫我好找。”
水溶抬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