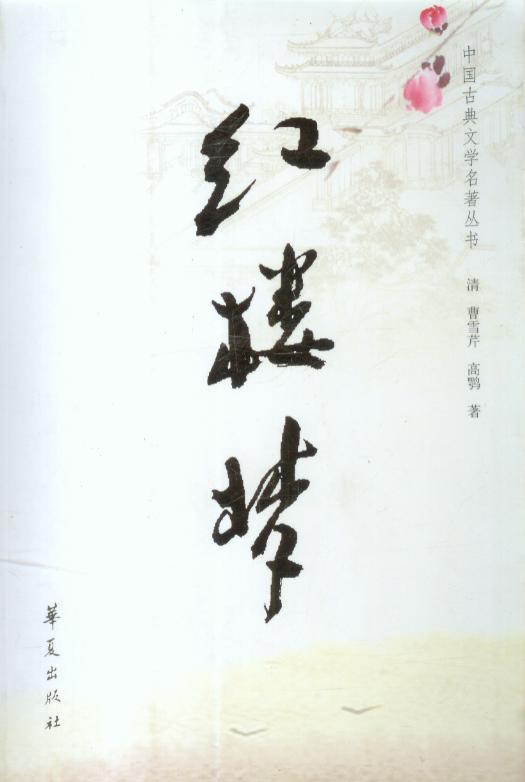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红楼梦同人)红楼·画中人人-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怕什么?”水溶抬眼看她,脸上风波不兴,“你只管让他们闭牢了那张嘴,谁敢泄出一点风声,再弄出什么妖蛾子,休怪本王拔了他的舌头。”
罗氏身子不经一颤,仔细回味他的话,似是森然透着寒意,竟像告诫给她听的。呆了一刻,心里更觉得委屈,匆匆拎起了食盒,忙加紧步子出去。
过了时辰暑气渐消,日头影沉沉地落了。晚霞顺着窗纱漏进来,暮色里一点伶仃微光。只听那墙上的西洋自鸣钟,有一下没一下敲着,仿佛走的没有尽头。
日影绕过曲径回廊,淡的缥缈,窗上新糊的纱屉,是黯黯的松石绿色,又叫软烟罗。黛玉斜靠在床榻上,身下枕着玉色夹纱枕头,瞧着窗影上的芍药花样,只是一阵出神。
到了吃药的时辰,紫鹃拿银吊子篦出来,用瓷碗盛着端进屋里。黛玉身子虚弱,隔了半晌方才借着紫鹃的手吃力的坐起。
“姑娘今儿气色好些了,这王府的药真管用,不像那些个蒙古大夫,只会骗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紫鹃吹凉了,一勺一勺喂到她嘴里。
黛玉咽下药,却是喘得厉害,伏在她肩头歇了会,静静镇着气:“你这蹄子,才吃人家几顿白食,就忙着帮人家添好话了。”
喂完之后,紫鹃掏出事先备好的绢子,替她拭净唇角:“虽是白食,总归要还的。我看这王爷心气极高,不像个菩萨心肠的人,谁知竟对姑娘这般好。就是宝二爷当初,未必想得这么周全。等姑娘养好了身子,也该去道一声谢。”
听见她提宝玉,黛玉只颦着眉,也当作没听见,怔怔的唯有两行泪,悄无声息的滑落下来。紫鹃自察失言,只能闷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不是我劝姑娘,宝玉虽好,到底是成家了的人。姑娘还这样年轻,把心放宽些,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黛玉盯着窗外的余晖,喃喃自语:“紫鹃,你说我这病……还能熬多久?”
紫鹃听这话不像样,只觉得心酸加剧,眼眶烫的要逼出泪来。自她病重以来,脸上消瘦的厉害,人已经不成样子。紫鹃怕她多心,将所有的面镜藏起来,有时清晨洗脸,她从湛碧的水影中照见自己的形容,总是怔着不说话。夜里翻来覆去的咳嗽,那么多痰中带血,都不是好兆头。
“姑娘快别怄自己,常言道病来如山倒,你只管好生养着,总会好的。”紫鹃一面温言开解她,一面将话引开,拿来新攒的牡丹绣样看了会儿,才服侍她躺下。
天外暮色渐浓,凉风袭袭吹送,这屋子临湖而建,开着半湖新荷,蛙声也远了。
紫鹃伺候主子吃了药,坐在外间里,临窗作针黹。心里惦记着黛玉的病情,手下不防事,猛然指尖一痛,鲜红的血珠子冒出来,晕染在牡丹花瓣上。
她痛的直咬牙,生怕屋里的人听见动静,放到唇边抿了一下,方才止住血。
帘外悬挂的缨络穗子动了动,紫鹃心生狐疑,隐约瞧见一抹人影,印在碧幽幽的窗上。自从搬进王府,她们被安置在这个极僻静的院落,平时甚少有人来。此时又快到了宵禁的时刻,更不该有客才是。
“谁?”紫鹃胡乱撂下针线,低唤了一声。待看清楚是谁,不由暗自吃惊。来人脚步轻不可闻,隔着细密的青竹帘子,一张脸庞甚是俊美,说不出的风华。
“怎么?紫鹃姑娘不肯赏光,请本王进去坐坐。”
紫鹃呆看着笑如春山的水溶,好半天缓过神,忙争着打起帘子:“王爷真是折煞奴婢了,您是主,我们是客,怎好暨越了分寸。”
水溶见她言语合度,是个懂规矩的人,心下里喜欢,微微一笑进了去。屋里陈设简单,两墙通壁的博古架,磊了满满的书。桌案上放了两条镇尺,一只宋代的定窑梅瓶,插了束野姜花,映着滟滟的兰膏明烛,一室洁净如洗。
“你家主子呢?吃药了没有?”
紫鹃笑道:“姑娘今儿好些了,只是没胃口,除了顾太医给开得药,旁的什么也咽不下。估摸着刚睡,既然王爷来了,不如陪着她这会子说话解闷儿。”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计,就要去叫醒黛玉。
水溶在背后唤住她:“既然睡下就算了,本王只是顺道路过,看她一切安好,也就放心了。”又觉得这话太过暧昧,却是鲠骨在喉,容不得他再说下去。
屋里掌着灯,烛红半明半灭,摇荡沉浮。映在那天青色的床帐上,投下朦胧的暗影。帐里的黛玉,静静仰面躺在枕上,恍惚什么都听见了,又什么都没听见。
多像十四岁那年,也曾这样昼夜躺着,想到心事,不禁拿袖子盖了脸。
年复一年,那么多难喝的药,可她并不觉得苦。日日对着菩萨发愿,保佑她能长长远远地活着,活到宝玉娶她的那一天……
只是这缘分,想必都是前生注定,命合使然,终究强求不得。
那个人坐着大红轿辇,毫不留情地抢了他,她趴在窗前看着,乌黑的眼里安定明澈,后来时常想,那时候其实是想哭的罢。
她疲惫地合眼,忍了许久的泪慢慢淌下来,渗入玉色夹纱枕头里,是温热的。
碧色的纱帐沉沉垂着,似一道墙,划出苍凉的姿态。
作者有话要说: 对不起各位看官大人,我确实更的很龟速……
谢谢你们在等,还有写长评的朋友,俺很感动~总之不会弃坑的
有朋友抗议说写的温情一点,这我很赞同,走边虐边甜蜜的路线,会有惊喜的
嗯,那啥……大家能接受带鱼有鸡情戏吗。。。
☆、拾壹
夏夜里闷热难当,黛玉歪身躺在凉塌上,听见外间安宁,有极轻的脚步声踱来,隔着床帷站了阵子,挟着清郁浮动的幽凉香气。她渐渐生出倦意,竟真的睡着了。
一觉醒来,案头掌着灯,紫鹃坐在帐前做针线,手边放着柄白麈尾,不时拿起来赶蝇子。黛玉猛地坐起,汗透重衣,紫鹃掀开帐子问:“可是又魇住了?”
黛玉脸色发白,过了片刻,才将散发捋到耳后:“这几日睡不安稳,想是犯了认床的毛病。外头几更天了?”
紫鹃掏出绢子替她沾冷汗:“卯正二更,王爷才来过,看姑娘睡的紧,也不敢搅断,只问还缺什么,等姑娘夜里想着了,明儿再打发人送来。”
黛玉想起这两天频频来送东西,不是暹罗茶,就是梅片雪花洋糖,她又是个心细如尘的性子,便觉得不自在,背过脸道:“无亲无故的,已经够让人多嫌了,何必再承他的情。”
紫鹃叹道:“姑娘又多心,我瞧那王爷人倒好,自咱们搬进来,吃穿用度不操心,什么烦难委屈也没有。素日在贾府里,吃几顿燕窝都闲言冷语的,倒不比这里多嫌?”
黛玉低眉不语,静了一刻道:“你当这里真是白住的,如今沾了人家一分半斗,往后还不得挟恩以报。我左右是这样了,拿什么赔给他?还不如死了干净。”
紫鹃生怕她胡想,顺着话儿说:“姑娘既有这心,何不替自个寻条活路,宝玉已是不中用了,眼前不正有个知疼知热的人?”
话音未定,黛玉不知何故,将手里的麈尾一掷,腾地站起来:“大半夜的,你想怄死我不成……”只说了半句,额角便沁出冷汗,手攥着床帐支撑不住。唬得紫鹃忙丢下活计,几步过去扶住她:“姑娘别气,都怨我不知分寸,说错了话,你莫往心里去。”
想到如今的境遇,黛玉心上不由大痛,转身伏到枕前失声哭起来。夜里风吹罗烛,一轮冷月成朔,映着窗上斑驳的剪影。
水溶站在阴影中,单薄的侧脸融进月华,长吁了一口气。伴着烛火残烬,转身离开。
翌日天明,罗氏侍候水溶起来,盥洗事毕,轮到服侍他更衣。依旧是惯常的便服,三重领口层层交叠,露出里头素白的单衣。围好了腰带,罗氏不禁拿手量了几扎:“这倒奇了,王爷最近食量不减,怎么瘦得这样厉害?”
水溶转过脸去,镜里的人越发清瘦,气质却是愈见凝练,到底是老了。
“今天冯唐将军做寿,说好了去他府上赴宴,午膳不必等我。”
罗氏微笑:“知道了,王爷去了悠着点儿,可别贪杯。”
水溶起步向外走,走到门边,又停步回身:“我案头存的那方砚台,打发人给紫鹃送去。就说我看她家姑娘的砚磨旧了,特地给她留的。”
罗氏的笑僵在脸上,好半天才说了声“是”。
车驾出了王府,没有去城西的冯宅,而是一路向南,策马拐入城里最红的烟花巷。金陵素以秦淮脂粉闻名,从苏吴一带选了雏女,蓄养成色艺双绝的名妓。招揽了不少官绅商贾,有人乐意花钱,有人乐意砸钱,风气长盛不衰,久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宵金窟。
到了锦香院门口,小厮打开帘子,水溶欠身而下。街前招揽客人的鸨儿偎上来,见他衣着平常,不像为官为宰的模样,车内的青油帘却用得黄缎里衬,甚是奇怪。
“呦,这位俊爷,大清早的奴家哪来的福分……”
小厮伸臂挡住鸨儿,掏出事先备好的荷包扔去:“这是我们爷打赏你的,冯大人包的是哪间阁子?”
鸨儿拆开来,荷包里装了满满当当的碎银窠子,当即喜得眉开眼笑,让堂倌将他们引进去。正厅鱼龙混杂,满屋子都是酒客,沿甬道上楼,径自进了二层雅间。
堂倌推开门,传出一阵调笑声,房里正玩到兴头上,几个薄衫娘子扭股糖似的往男人怀里钻。水溶皱眉,目光却是出奇的冷淡。正眼扫过去,蒋玉涵推开怀里的窑姐,猛地坐起来。
气氛顿时紧张,众人都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还是冯子英缓过神,给花魁递眼色:“芸娘子,大主顾来了,你还不去敬酒?”花魁媚笑着迎来,见水溶年轻面嫩,便强扯着他入席。
“这位爷好生俊气,头一遭来,还不懂规矩吧?”说着整个身子偎过去,春葱似的纤纤玉指在他胸前揉搓,“奴家给爷唱支新样儿的曲子,爷把这两坛酒都吃了?”
新晋状元陈也俊喝的半醉,斜眼笑道:“两坛如何使得,你快唱来,爷这里多得是银子。”
花魁这才抱了琵琶,顺势倚到水溶怀里,轻拢慢捻起来:“春日宴,我有五重深深愿,一愿且图久远,二愿恰如雕梁燕,岁岁得相见,三愿薄情相顾恋,四愿永不离散,五愿奴留收因果,做个大宅院……”
好好的冯词,改的俗鄙不堪。水溶忍了忍,虽早已尝男女□□,他对这秦楼楚馆并无兴趣,更是无动于衷。一双眼睛直盯着蒋玉涵,看得他浑身不自在。
冯子英揉着鼻子,心说这两人分别月余,还不知烹油烈火的急成什么样子。
花魁娘子是个聪明人,在风月场混迹多年,什么恩客都见过。调弄了半天,见水溶仍是没有动静,索性去解他腰间衣带,柔荑般的酥手探进去,胡乱摸索着:“爷身上真凉,让奴家给您暖暖身子……”
水溶轻推开她,站起身道:“琪官,你跟我过来。”
蒋玉涵放下杯筷,蓦地涨红了脸,只好离席追过去。目送两人进了隔壁的独间,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一笑,唤评弹的小厮上来,继续吃酒听曲儿。花魁败了兴致,咬着绢子恨恨骂了句:“兔儿爷!”
推开紫檀大门,这么宽敞的厢房里,只摆了一张床。蒋玉涵站在门外,紧张地有些不知所措。却冷不防被人攥住手腕,一把拖进去,门在背后重重关上。
他站立不稳,险些撞到榻前,扶住床沿强笑道:“王爷今天这般性急,是怎么了?”
“怎么了?”水溶声音寡淡,却像刀子一般的冷,“你自己做的好事,心里该明白得很。”
蒋玉涵颤了一下,避开他审视的目光:“王爷…是嫌我伺候的不周?”
“还要本王提醒么?”水溶勾起唇角,细密的睫毛下敛着极深的寒光,看得人遍体发憷。“忠顺王搜罗贾家的那些罪状,你在背后出了多少力?贾家到底哪里对不住你,让你非要置之死地才后快?说啊!”
蒋玉涵的脸立时白了,笑道:“王爷以为我有这么大本事?罪是死,人是活,贾家若不伤天害理,何以落到家破人亡的田地。当日在紫檀堡,贾宝玉为求自保,不惜出卖我。我不过是以牙还牙,苟全自己这条贱命罢了。”
“好……”水溶连连点头,“一石二鸟,既报复了贾家,也报复了我。玉涵,我以前当真看轻了你!”
“何必这么说,我在王爷眼里,不过是枚无足轻重的棋子,下贱的玩儿物。你本不好男色,却假意帮我赎身,那些床笫间的温存,不过是哄着我骗着我,目的达到了,再一脚踹得远远的。你从不曾把我放在心上,只是敷衍应付,可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既然明知得不到你的心,何妨坏了你的好事,让你记恨我一辈子!”
水溶闻言抬眸,愕然看着他,蒋玉涵眼中盈满泪,某些感情一直深深烙在眼底,可他视而不见。
“我知道王爷心高,看不上腌臜的戏子。你能给得都给了,原是我求的太多。”
水溶心头浮起歉意,一时无言以对,下意识去碰他的手。
蒋玉涵断然将手缩回,背过身说:“你我各取所需,都为一个利字,算不上谁负谁。玉涵已经成家,王爷也早有妻室,从今后两不相欠,以前都不作数了。我只想劝一句,王爷府上藏的人,忠顺王暗中已得到线报,若是大理寺彻查此事,只怕有惹不清的麻烦。”
水溶踟躇片刻,不露声色道:“你听了什么谣言?我府上只有家眷,哪来窝藏的嫌犯?”
“你到今天还想瞒我?当日廷尉周纶亲自立下契据,白纸黑字岂容抵赖。他早料到王爷不认账,所以偷匿了一份,现就存在刑部衙门。那林家姑娘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挖空心思护着她?”
蒋玉涵逼视着他,声音如一刀贯穿他的心肺,水溶动了动嘴唇,嗫嚅道:“我不指望她什么,只要她活着,活着就好,有些事你不会明白。”
“我明白得很!”蒋玉涵被戳到痛处,一把揪起他的衣襟,“这么些年,我为你忍辱负重,伺候那个腌脏的老头子,什么委屈都往肚里咽,你可曾明白过一分?我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