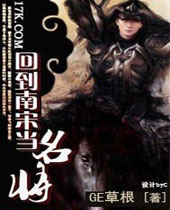猎美南宋-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那么黑,我又不认识你哥!”
“别废话,我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是!”
“我跟你拼了!”
孟兴郊说着就冲了上来,我手里拿着钩月枪,但怎能跟我的兄弟动手,把枪扔到了一边,他一下就摔了我个跟斗!
我站起时,他又摔了我个跟斗。
众人上来劝架,但只是嘴上劝着,没人敢上前。
孟兴郊打了我一拳,将我再次打倒,我眼冒金星,鼻子里流出了血,只听孟兴郊喊道:“起来!给我起来!”
孟嫂道:“兴郊,不得无礼!”
兴郊怒喊:“没你的事!我宰了他才解恨!”
我躺在地上又听得一阵乱。
好像几个缉捕一番打斗终将孟兴郊拿下。
只听顾知县道:“你这厮,好生无礼,你哥本是盗贼,我还没问你们的罪,你倒报复起牛英雄来。牛英雄是杀贼有功的勇士,你怎敢对他无礼?”
小朵帮我止了血,擦拭一番,扶我起来。
只见孟嫂扑通跪到顾知县面前,“大人!我弟无礼,得罪了这位牛英雄和官人,请大人恕罪!”
孟嫂说牛英雄时像是在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杀了她等了好久的丈夫,她总是要恨我的。
“我放了他,他要行凶怎么办?”
我走上前道:“大人,他的哥也是我的哥,我们是结拜的兄弟,毕竟是我杀了他哥,他怎样对我,我都认了。”
“既然牛将军讲情,他就交给你处置了!”在顾知县又对妇人说,“你也起来吧。”
妇人站了起来。
孟兴郊指着我骂道:“你别跟我假仁假义!我不需要你讲情,就是关了我又怎样?”
我走上前帮他解了绳索。
孟兴郊拔出了柳下安的剑,刺向了我。
我眼一闭,说道:“随你吧!”
孟兴郊抖了抖了剑,只听一声大喊:“住手!”
焦兴梦和大个子来了。
焦兴梦说:“三哥,你好糊涂啊!你让大家伙说说,这事儿愿得着大哥吗?这群贼劫了草花不说,又劫了另一位姑娘,要不是碰到大哥拔刀相助……“”
大个子也说:“兴城虽是咱的哥,但他怎么说也是一个贼。这些贼不知祸害了多少人,还要祸害多少人!你为一个贼去杀一个杀贼的,让别人怎么看你!”
话不怕说,就怕绕,大个子这么一绕,绕得孟兴郊扔了剑,要去抱他大哥的尸体。不想被几个缉捕拦住了,一个道:“不行!大人说了,要在当地焚烧。”
我赶紧对顾知县说:“不如大人开一面,让我兄弟他们带回家好生安葬了吧。”
王员外说:“这贼虽死有余辜,但他或许也是被迫的,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他老娘也找了他好长时间,活面见不了,怎么说也得让那老人见见死面吧!”
众人也都帮着说情。
顾知县朝几名缉捕摆了摆手道:“让开吧!”
我对冯秃子说:“你不如送他哥回家吧!”
冯秃子说:“什么事我都依你,这事儿可不成,我只拉活人不拉死人!多不吉利!”
孟兴郊抱着他哥离去,妇人哭着紧跟其后。
我对大个子说:“我还有事儿,你和兴梦快去兴郊家吧,帮他料理一下他哥的后事。我随后就到!”
焦兴梦问:“大哥,你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我说:“放心吧。”
大个子和焦兴梦离去。一些人也相跟着离去。
我和王员外等人跟着顾知县在小朵的带领下去了另一个出事儿的地方。
找了半天,这小朵只找到了她相公一截带血的衣袖,可尸体却是不见了踪影。
小朵拿着这截血袖哭了半晌。
四处寻找找不到,王员外说:“不远处有个道观,我们不如去问一问。”
没多少工夫,一道观在穿过林木后隐约可见,近前可知是“贞玄观”,又见四周景致似曾相识,我拍了拍头,方想起前不久的梦里所见的也是此观,不由一惊。心下暗忖,今日莫不会要见到那位梦中**的女真人?
门被敲了半天方开,一小道姑未说话先笑着露出白牙,长得的确很像死去的鸭蛋,当然,我细看了看,并不是鸭蛋。
“进来吧。”小道姑说完转身跑开,边跑边喊:“师父,王员外来了。”
顾知县道:“看来老王你也是这里的常客!”
王员外笑了笑:“大人说笑了。我只不过经常出些香火钱,自然便对这里熟了些。这里的邱道长还是还不错的。”
正说着,一位道姑出外相迎,引我们进了厂厅。正是王员外所说的邱道长。
未等我们开言,邱道长说:“今日我的徒弟们去担水时,见路上一具尸体,便喊我过去看。顾大人,你们可是为此而来。”
顾知县道:“正是。如今在哪里?”
邱道长说:“跟我来!”
我们相拥而去。
第047章 贞玄观里卜今生()
草中惊飞鸟,蝶舞入花丛。
曲径通幽处,人行乱匆匆。
邱道长说道:“我见那人躺在路边血乎乎地好生可怜,便没有报官,将他净洗一番,草席一卷便埋到云蒙山上。不瞒大人说,我们附近经常有人被害,一开始我们也曾报过官,但总也查不出什么,后来索性就不报官了。”
王员外道:“顾大人初来,你们放心,他肯定会捉拿那些盗贼的。”
我问道:“邱大师,那你们住在这里不害怕吗?”
邱道长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发现她脸上有一些麻子,因为脸白,这麻子更是明显。
邱道长笑笑说:“我倒不怕什么。只是小徒在前两年总是心惊胆战的,时长日久,我们这道观倒也清静,她们倒也不记挂在心上了。”
顾知县问:“邱大师可曾见葫芦贼在这里出没?”
邱道长摇了摇头。
一路闲话,不觉到了两山相环之处,平地乱起数座坟堆。
邱道长指着一座新坟道:“那便是。”
小朵扑上去哭天喊地起来。
众人随着顾知县拜了拜。
邱道长说:“万物有生有死,皆有定数,死也非死,或为新生,用不了几日也便超脱而去!”
“邱道长说得极是,姐姐不必哭了。”说着柳下安弯腰去搀小朵。
顾知县道:“既然已经埋了,入土为安,也便没了验尸的必要。不如先回去再做商议。”
大家又回了道观,顾知县就要离去,“多有打扰!顾某衙中事紧,先行告退!”
王员外说:“不急不急,我已叫人备下酒菜,不如就这宝地吃个便饭再回也不迟。”
大家又回厂厅去坐,不同的是,墙上竟添一幅新画,名曰《牧牛图》,大家近前观看,凭头论足,端端是活灵活现,意蕴深远。
大家在看画之际,我偷看着邱道长,觉得那夜梦中之人与她一点也不像,不知那个叫师师的道姑是不是就在这观里?
我把目光转向了那个长得像鸭蛋的小道姑,她正在偷看柳下安,越可越觉得这小道姑清纯可人,不想,她嘴角竟流下了口水,真可谓“桃花流水三千尺”!
小道姑忙用帕拭去口水,朝我笑了一笑,脸上倒无一点羞色。
众人落了座,邱道长喝道:“雪琴,还不快去点茶,不知在呆看啥?”
这长得像鸭蛋的人便去端茶具。
顾知县道:“这《牧牛图》画得真叫好。这个宫素然是个什么人物?”
我走到画前看了看,落款果真是宫素然。
宫素然,跟鱼玄机一样,这么好听的名字,莫非也是一个才色俱佳之人。
邱道长饮了口茶道:“不是别人,正是小徒。”
顾知县道:“徒弟就能画成这样,道长若是出手,那牛还不得要飞出来吗?”
邱道长道:“人皆有长,论修行,她不如我;论写诗作画,我真不如她!”
王员外道:“这个宫素然可否让我们一睹芳容。”
王员外正好说出了我的想法。
邱道长说:“实在不巧,小徒近几年也是四处云游,我也不去管她,尽着她的性子来。前些日子回来不久,又被王贵将军请去作画了。”
顾知县说:“这王贵将军可是岳飞帐下的那个吗?”
邱道长说:“正是。王贵收复了邓州,就派人将小徒请了去。”
柳下安说:“看来这个宫素然也是见多识广之人,世间奇女子还真不少。”
邱道长说:“不见则奇,见则也非成仙成道之人,不过是凡身俗体。”
王员外问:“都说道长会看相,可知我们顾大人何时会有升迁?”
邱道长笑道:“恕为直言,顾大人若能清白一世,倒能落个好名声,若糊涂一时,非常之事不得不防!”
顾知县不悦道:“谨记道长教导!”
王员外见邱道长这等说,觉得脸上挂不住,指着我转移话题道:“这是牛皋的部下,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很像一个将军?”
我直摇头道:“哪里哪里,我也是凡夫俗体,不值一看。”
众人看了我一眼便把目光挪开,那邱道长却盯着我看了半天,也不言语,大家也便把目光又扫向了我。小道姑给我来倒茶,也偷偷地瞄着我。
邱道长啜了口茶,终于开了金口:“乍看凡身俗体,细观仙风道骨。人生遇险历奇,总能化险为夷。人生得意有东西,人生失意无南北。失意不气虚,得意不气妄!小道即让,大道即得!”
冯秃子道:“大师说得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邱道长望着冯秃子说:“他的身世我不便道破,但绝非等闲之辈,必是福将!”
王员外大笑道:“哈哈,我就说牛将军非等闲之辈吗?看来我这凡夫俗子也会看相啊!”
邱道长又极为严肃地望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对我说道,“只是这位官人近日有大难,不得不防啊!”
王员外紧张道:“既如此,可有化解之法?”
邱道长摇摇头:“贫道法力不够,只能看个一知半解!”
柳下安说:“你都说了,既能化险为夷,又怕什么呢?”
我心里难免紧张,挤出笑脸说:“哈哈,凭天由命吧,说不定也会死于葫芦贼之手呢?”
邱道长说:“全当戏言,也不必记挂在心,走,贫道带你们饮上几杯。”
邱道长领我们到了另一房间,又是另一番摆设。不一时,便大碗大盘的摆上两桌,大家依次而坐。柳下安示意小朵坐在他的旁边,那小朵犹豫了一下,竟挨我坐下。
邱道长举杯说道:“若不是此等因缘,顾大人等各位官人还不知我们这等小观,今日相聚于此,也是天定的缘分,来,我们干一个。”
大家举杯饮尽。
王员外道:“这观以前我倒是来过,好不破败,只有一个道人,竟然是断了两只手掌,也不爱和人说话,后来也不知这道人去了哪里。多亏邱道长来到这里,又才续上了香火,好不兴旺。”
邱道长说:“也多亏了王员外你们这些大善人,不然的话,这小观也不会有今天。顾大人到此,更是蓬荜生辉,小徒宫素然若在,贫道定让她将今日兴景画下来,也是我们的荣耀不是?”
王员外道:“那赶紧敬顾大人一杯。”
“那是自然!”邱道长和顾知县举杯一碰而尽。
邱道长说:“说起来这道观倒有些年头,最早叫青台观,陈抟老祖还在这里修炼过。兴兴衰衰多少年过去了,女道士刘德妙来到这里将此处收拾一新,改作贞玄观。”
我问道:“这刘德妙莫非就是真宗时经常出入丁谓家里那位吗?”
“正是。看来,这位官人知道得挺多。”
“那倒不是,我只听岳元帅给我们讲过一些。”
邱道长继续讲道:“这刘德妙经常出入丁谓家中,丁谓就让她假托老君说祸福之事。她在丁家设神像;晚上在园中设坛祭祀,大家都很信奉,就连与丁谓暗中勾结的宦官雷允恭也多次来祈祷。等真宗皇帝一死;雷允恭引她进入禁中。后凿地得龟蛇;丁谓令刘德妙拿入内宫;欺骗说出自丁家山洞中;皇上问她;所奉侍的怎么知道是老君。刘德妙说,宰相不是凡人;应当知道这事。丁谓事败;官府逮捕刘德妙;才知道有些话是丁谓教刘德妙说的。丁谓家老三丁玘又犯有与刘德妙通奸罪;也被发配了。”
我问道:“这个刘德妙后来又怎样?”
邱道长说:“很可能是被监禁了,当然后来究竟怎样,也无人得知。这座观虽小,但又不知住过多少人,兴兴败败得也不知多少年了。”
邱道长虽是女流,倒是能说能饮。
“丁谓?我怎么没听说过呢?”小朵问道。
我说:“官可不小,当过宰相!溜须拍马我们都会,其实这溜须还是从丁谓那儿来的。一次,他跟寇准一起吃饭时发现寇准的胡须粘上了菜汤……”
“额!”王员外使劲咳嗽了一声,朝我摆了下手,我才知犯讳了,怎么竟面对顾金汤知县说了个“汤”?顾大知县果真拉下了脸。知情者皆表情肃然。
“这有什么啊!我经常看男人胡子上粘着东西。”小朵这样一说,有胡子的都去摸胡子,顾大人紧握着杯,手在抖……
我拧了小朵一把,赶紧说道:“我记错了,是这样的,他俩一起吃饭时,一个饭粒粘在了寇准的胡子上,丁谓便起身替寇准擦拭胡子。寇准笑着说,你是国家的大臣;是替官长擦胡须的吗?丁谓十分羞愧,从此跟寇准不对眼不说,还老排挤陷害他。”
王员外笑着说:“就是我这胡子粘了米粒也不会有人溜须的。”
顾知县看起来还是不大高兴。
小朵一开始也不爱言语,但一说话竟让大家变了色,便可能知道我俩是说错话了。毕竟她是久经酒场之人,不一时,轻笑巧言,竟劝得顾知县眉开眼笑,连喝了好几杯。
顾知县高兴大家就高兴。
这个一杯,那个一杯,尽兴时小朵还唱了一首柳三变的《采莲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