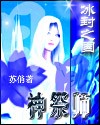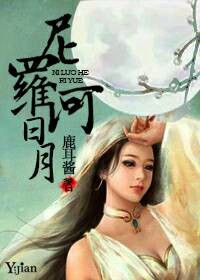日月当空照中华-第7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阴当时的县令已经投降,但是面对满清朝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江阴百姓群情激奋,宁死不降。
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的阎应元,由于在典史任上威望素著,兼且拥有过人的智谋胆略和出色军事组织才能,很快就被江阴百姓拥戴为抗清领袖,然后就开始了历时八十一天、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江阴抗清守城之战。
就这样,阎应元带着十万江阴老百姓,对抗二十四万满清军队,居然守城八十一天,让满清军队付出了七万多人的伤亡代价,不能不说阎应元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领导能力的乱世豪杰。
虽然此时的满清军队,多数都是投降过去的汉军绿营,但其中的真正满洲鞑子也有不少,而这也正是江阴城破之后,满清军队屠城的原因之一。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后世之时,每当读到阎应元历史上在城破当日,拿血写在城墙之上的对联,就感动不已。
阎应元的那首对联是这样写的:“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这样忠肝义胆、武艺绝伦而且能力超强的人物,如今出现在了顺天府上报的武举名单之中,知道这些历史故事的崇祯皇帝又怎会不欣喜若狂呢?!
当然了,这位崇祯皇帝不知道的是,如今都是二十六七岁的阎应元和王来聘,相互之间不仅认识,而且关系还不错,素来以兄弟相称,毕竟两个人都是京师地界的豪侠人物。
京师说大也大,但是说小也小,舞枪弄棒的练武之人虽然多,但是真正练成了本事的人,却也屈指可数,相互之间以武会友的事情,自然也不比当时的士林秀才结社作诗来的少。
其中,王来聘自幼习武,自然是希望有朝一日货与帝王家,走上仕途,不仅光宗耀祖,而且可以为国效力。因此,在天启五年的那次武举考试中,王来聘就已经中了武举人。
阎应元则是出身吏员世家,所以父死子继,十八九岁就在通州县衙里当了捕快班头,也因此他尽管精通兵法,武艺高强,才干出众,但在原本的历史上却失去了参加武举会试改变前途命运的机会。
虽然历朝历代都是官吏并称,朝廷六部第一部也叫吏部而不叫官部,但是在明代官与吏之间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而且是几乎无法跨越的鸿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吏员,努力一辈子也跨不过这道鸿沟。
而且一个人一旦身为官府吏员,就会如同卖身为奴而入奴籍或者贱籍一样,从此失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基本上是一日为吏则终身为吏。
所以,阎应元虽然在历史上武艺高强、才华出众,而且属于那种军政皆优的人才,也并没有机会通过考武进士而出仕任官,因此一直在吏目的阶层上打熬岁月。
直到年过四十,政绩突出的阎应元,才有了那么一个到江阴县出任典史的机会。
而如今崇祯元年的恩科,不仅增加了武举会试,而且大开科禁,不论出身,只凭本事,不管你是微末小吏,还是连微末小吏都不如的边军士卒,甚至三教九流,只要有本事,就可以参加武秀才、武举人乃至武进士的考试。
如此一来,原本没机会的阎应元,自然是一考一个准儿,以顺天府武举第一的名次,异常顺利地进入了武会试的名单,同时也终于进入了崇祯皇帝的视野之中。
阎应元的事迹不需再多说。如今既然进入了崇祯皇帝的视野,那么考上武进士也就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另外一个令朱大明感到意外惊喜的人物,就是那个陈奏廷了。
陈奏廷是谁,即便是后世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巧合的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后世之时就对历史人物李岩非常感兴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后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陈奏廷究竟是何方神圣。
陈奏廷的母亲,正是李信的姑姑,因此陈、李二人,正是一对亲姑表兄弟。
历史上,李信之所以最终投奔李自成,跟这个陈奏廷也有着不小的关系。
李信与李侔兄弟,以及陈奏廷,自幼皆喜爱习武,曾经同时拜怀庆府河内县千载寺里的一个僧人为师,学习枪棒武艺和内家功夫。
三人既是表兄弟,又是师兄弟,感情自然是非比寻常。
历史上的崇祯四年,大明朝廷大开武举,二十八岁的陈奏廷,赴开封参加武举乡试,李信李侔兄弟自然是陪同前往。
陈奏廷刀枪剑戟弓马武艺样样精通,本来以为肯定中举,结果在校场骑射一项上发挥太好,一马三箭,射了个“凤夺巢”,结果报靶人误报,说他两箭脱靶,考官遂判其落榜。
李信、李侔兄弟皆是怒不可遏,最后大闹考场、痛扁考官,而陈奏廷更是在激愤之下打死了校场报靶小吏。
结果陈奏廷不仅没有考上武举,而且从此只能隐姓埋名,不敢露面。也是由于这个事情,李信李侔兄弟也断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后来李自成打进河南之后,怀才不遇又不甘埋没的李信,在其弟弟李侔及其表兄弟陈奏廷的极力鼓动下,最终选择投奔了李自成。
之后由于李信的举人身份,加之武艺高强,又深通谋略,李自成见之大喜,马上给以重用。李信于是改名李岩,开始了他虽然光辉灿烂但却注定悲惨的闯将生涯。
李侔最后跟着改名李岩的李信一起,被李自成设计杀害,而陈奏廷则在李信、李侔兄弟被杀之后,凭着自己的过人武艺逃了出来,回到河内陈家沟老家,从此隐姓埋名,隐居不出。
而这个陈奏廷,还有一个名字在后世广为人知,这个名字叫作陈王廷,正是历史上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
第一二七章 状元及第()
如今的这一世,发生在李信、陈奏廷等人身上的历史故事自然不会再发生,因为至少李信当前已经中了进士。
而陈奏廷也经在邱兆麟的亲自主持下考中了武举人,被保荐到了京师参加武举会试。依照崇祯皇帝对他的认识,考中武进士自然也是毫无问题。
果不其然,人才就是人才,正如是金子就总会发光一样,只要你足够优秀,再加上一个稍微公平公正一点的环境,你就会很快脱颖而出、崭露头角,从而出人头地。
崇祯元年的武举会试,终于在七月十一日落下了帷幕。近两千名来自天下各地,包括九边各镇的武举人,汇集在位于通州的皇明忠义讲武堂内,经过连续九天的比武考试,终于评出了高低,排出了大榜。
七月初十辰时正,二百名中了式的武贡士们,在军机大臣孙承宗、张惟贤、李邦华的引领下,与文科进士一样,走正门,进入了皇宫大内的建极殿,参加由崇祯皇帝亲自主持的武举殿试。
这自然又是华夏历史上的头一回。事实上,崇祯四年的那次武举,就搞了一次殿试,取中的一百人排了三甲三等,头三十名就是由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选定的。
虽然在崇祯皇帝之前,武举考试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是把武举的地位,完全提高到与文科进士一样的高度,亲自在通过殿试排定武进士的名次,在中国的历史上,崇祯皇帝确确实实是第一人。
武进士们毕竟多数都是武夫出身,文武全才型的人物,毕竟还是并不多见,所以崇祯跟皇帝给出的殿试题目也很简单,就是解读孙子兵法的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些东西都是武举考试上来就要靠的兵法之中的内容,自然是人人滚瓜烂熟。
然而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能说出新意就更难。
但是崇祯皇帝的目的,不在于给这些武举贡士们制造难题,而在于给所有的人一样的机会,在试探出深浅之外,保证每个人都不会出现完全答不出来的情况。崇祯皇帝的目的当然是达到了。
看着建极殿中埋头写字的新科武贡士们,崇祯皇帝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特别是看着一群人中间显得极为沉稳干练的阎应元,以及显得有点紧张兮兮的陈奏廷,如今的崇祯皇帝,终于有了一千年前唐太宗李世民重开科举时的那种感觉了,也就是那种天下英雄皆入掌中的感觉。
阎应元表面上不动声色,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样子,但是心中的激动,却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个月来,阎应元就像做梦一样,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就这样随着一个新皇帝的登极而极其顺利地实现了。武进士没有文进士值钱,但毕竟也是进士出身啊。
不管跪坐在建极殿中的阎应元,内心是如何的澎湃,至少此时此刻的他还是表现的非常沉稳。
不过这个沉稳,到了当天下午考试结束的时候,就彻底绷不住了。
因为皇帝最后在三位军机大臣联合推荐上来的前三十名新科武进士之中,亲自选中了一甲的三个人和二甲的头两名。
一甲三人分别是阎应元、王来聘、翁之琪,二甲头两名分别是陈奏廷、徐彦琦,头三十名中的其余二十五人,自然皆在二甲之中。
另外的一百七十人,则维持综合成绩的排名不变。
当年轻的皇帝亲口说出崇祯元年恩科武举的状元,就是自己的时候,一贯沉稳的阎应元,瞬间就泪崩了,不仅当即踉踉跄跄地出列,然后跪地不起,一边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边情不自禁地涕泪横流,根本控制不住,就差嚎啕大哭了。
看着在后世自己万分崇拜的民族英雄,如今在建极殿中如此动情,崇祯皇帝也是内心感动,亲自走下御座,上前将之搀扶起来,看着他深深地点了点头。
对于阎应元这样的情况,拥有后世阅历的崇祯皇帝,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有时候一个人极度高兴之时与极度伤心之时的外在表现,是很难准确分辨出来的。
通过阎应元在得知自己中了武状元时的真情流露,朱大明至少可以保证一点,那就是阎应元这个人,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忘了自己崇祯元年武状元的身份,而且从今往后,这个人也必定会成为他这个皇帝的铁杆打手。
与阎应元这一刻的表现截然不同,陈奏廷倒是终于放松了,平静了,除了跪地谢恩高呼万岁,其他的与在场其他武进士并无太大不同。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这两个人的性格差别,阎应元是举重若轻,而陈奏廷则是举轻若重。
第二天,二百名新科武进士的名单,就张贴分别到了兵部衙门和皇明忠义讲武堂的南大门外,除了阎应元等一甲三人和陈奏廷、徐彦琦这两二甲头两名,广东顺德的朱可贞、陕西汉中的潘云腾、江西德化的卢元定、南直江阴的王公略等等,这些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武举人们,也都没有白来,一个个都是榜上有名。
与大明之前的历科武进士及第之后的安排不同,崇祯元年的新科武进士们,不管是一甲进士及第,二甲进士出身,还是三甲同进士出身,都没有直接授予武将职务,而是按照皇帝的旨意,集体进入了皇明忠义讲武堂,作为讲武堂成立以来的第二期学员,开始了他们为期三个月的炼狱生涯。
新科武进士中的大多数人,尽管一个个武艺高强,十八般兵器样样都行,但是在讲武堂里根本不给你机会练这个,包括弓马骑射,都很少有机会操练,毕竟弓马骑射是讲武堂第一期骑兵科的学员们练习的科目。
而他们这些武进士,虽然说起来是武进士出身,但到了讲武堂,就是十足的新兵,包括那些后来从各地卫所推荐而来,经过五军都督府考试合格,然后又通过武举会试而成为武进士的人,也一样要从头学起。
学习的内容,有本朝太祖高皇帝的《讨元檄文》,有军机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联合刊印的皇明新军操典,还有大明律中的兵律军法,以及大明军中各种各样的金鼓旗号。
每日里学完了这些,就是沿着讲武堂周长五里的大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跑步。
而最折磨人的,还是那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进行的、极其枯燥乏味的队列操练。
第一二八章 燃情岁月()
新科武进士们自从进了讲武堂,简直就像是突然间从自己的人生巅峰上摔了下来,而且还是摔了一个狗啃屎一样难堪和难受。
这些人本来以为自己从此鱼跃龙门、今非昔比了,没想到突然之间又变成了仿佛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的新兵。
每日里各种学习训练没完没了,同时还要忍受讲武堂第一批学员们各种各样的嘲讽和讥笑。
尤其是队列操练的时候,这些武艺出众的武进士们,有的连着训练了几天,还是一不小心就会行差踏错,而每当出错的时候,总是免不了要遭到临时充当队列教官的第一期学员们肆无忌惮的嘲笑。
为此,年轻气盛、脾气火爆的新科进士第五名徐彦琦,还差点与同样脾气火爆的临时队列教官黄得功当场拳脚相向。
而与教官对着干的下场,就是绕着讲武堂周长五里的大操场,不间断地跑上十圈,否则就要承受三十军棍的刑罚。
颇识时务的徐彦琦,当然是很自觉地选择了跑圈,并且在跑过了十圈之后,接下来的训练日里,不管遇到哪个正式的教官或者临时充任的教官,徐彦琦都是恭敬有加,让干啥就干啥,充分表现出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觉悟。
而那些早入讲武堂一个月的老兵油子们,自然也是早就领会了讲武堂那些条条框框的威力,在各科教习讲官,包括那些红毛夷人教官的面前,一个个都表现的十分懂礼貌。
即便是最为桀骜不驯的那几个人,比如东江镇的毛有见、淮安来的许定国、大同镇的祖泽远,以及延绥镇的猛如虎等人,刚入学的时候一个个牛逼的不行,走在路上都是鼻孔朝天,一副谁也看不上、谁也没他强的样子,然而挨过了几次收拾,甚至只是关了几次禁闭之后,这些人全都变了,在讲武堂的那些总教习、主教官们面前,甚至一贯歧视的红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