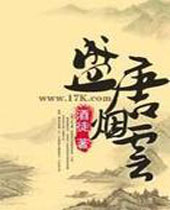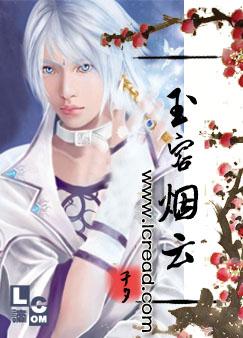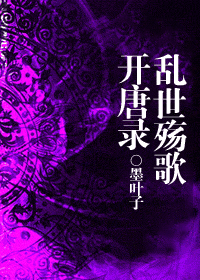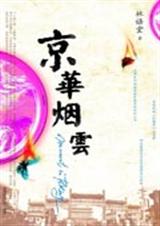��������-��2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Ժ�ij��������������ƾ��ǣ����Ƽ����������һ������塢���壬���ŵ���������ʹ�ö����˵�˼ά��ʽ��Ҳ�����������Ȧ����һ���̶�����������ֻҪ�Լ�˵��ȷ�е��������˽ײ㣬�����ͻ�����µ�˼�룬�ⱾҲ�Ǵ�����ѧ�ɾͻ����֮�ߵĸ���ԭ��һ����յģ������˵�˼�룬�������������ɵ���ᣬ��ôҲ�����ܲ�����������Ӵ�����ʵĻͻ;�����
�������������л��һ�۾Ϳ����˶���������֮�ϵ����ڡ�
�����������µ�������Ȼֻ����ʮ���꣬���ǿ�����ȴ�������ϡ�����ܻ�Ҫ���ϡ�
�������������룬�侭���˾��ĵĴ�����ȴ���������ϵ�Ƥ���ɿ����壬���絶�̡�˫�����������۴����ѻ��������������������������������ɫ�ͿյIJ���������������׳־������������Ծ���ﵶ�Ľ�˶���塣
�����������������ڴ�������ǰ����λ�����ɾ�������л�������������ӣ���������ȴ�ǵ�һ�ο�������òȡ�ˣ��Թ���֮�����ο�������ϲ��������Ů�������ˡ�������ǰ��ü��Ŀ���������˰�֮ò��л�������ڲ��ɰ���һ������ͷ��ϲ�����ݼ���֮�£����������ġ����ʡ����Ƕ��˼���ϲ����
��������л������������̶̵Ľ���֮����ʱ���ڵأ�����л��ߵ�����¡���
������������Ц�����������ɣ��������װ�֮����˼Ľ���ӣ�����һ������������Ӣ�ţ���ΰ�ɷ����Ҵ�����Ҳ�����ˣ���������
������������л���¡���
�����������˻������䣬�������̰�����������ϯ����֮�������ž�������ߡ�
�����������˼�״�����ж�ʱ��Ϊ֮һ��л�������Dz�ѧ�ٸߣ��������죬����Ҳֻ�ǰ�������������ͺ����������ھ�Ȼ������λ���ŵ���˿�ǰ�������������ܺ͵�������λ��֮�£��ѵ����ھ����Ѷԡ����ʡ��Ͽ�����
�����������˲��ɱ���ؿ�ʼ�����д��������ڵ���˼����ֻ��һ˲�䣬�������ϵı��鶼������粻����
����������ʱ�����������ڵ��������ˣ������������ˣ���Ϳ�ʼ�ɡ���ʿ����
������������ʿ��ʱ�������������ڡ���
�����������ڵ��������˽�����䣬�������ʡ����ŵ��������ǧ�������С���
���������˻����ų��ڣ�����ʿ��û���ü���Ӧ���Ϳ������֮�У�һ����ʮ��������ߣ��ڵ�һ����վ�������������²��ɣ��������Ի��ڡ��������������������֮��Ҳ���ϲ��ɷ��ŵ��������С���
��������л����ʱ���һ�飬���ñ�Ӹ����ã�������Ҫ���飬������Ҫ��������·���ư���
�������������ߣ�л����Ȼ�Dz���ʶ���������ڵ�ͬʱ��л����������֮���ڵ�λ�ÿ�ȥ��
����������Ҳ������֮ǰ���ͺ�����֮�����õġ�
����������ʦ�����Щ��èè����������붼����ʶ������֮ȴ��֪����һ���������ν֪��֪�ˣ���ս����������������������ָ��ģ��������������ʷ���������ģ�ֻҪ֪���˶Է�����������֪��ʷ�����������Ͼ���֪���Է��ĸ��ס�
��������������֮��л�������Լ���ʱ�����ֵ���ָ���Ϳ�ʼ�������ϣ��н���ؿ�ʼ�û�������˵���Ȼ����Ħ˹���롣л��Ϊ�˽������ս���������������ҹ��
���������ܿ죬����֮���û�����ˣ�л��Ҳ�õ����Լ���֪������Ϣ�������ԡ�
�������������Լ���Ȼû����ʷ��������ʲô������������ȴ�Ǵ���������
����������Ȼ���������ָ�ò�������һǧ�������ʥ��ʦ���ӣ���������̫�游����ӱ�
����������ѧ���������ϱ����ķ�չ�ݱ䣬�ҷ����죬�����ڶࡣ
���������ں����н��Ĺ���֮�����ҷ�ʦ��֮�𡣶���ĩ�굽����֮�䣬����֣���������֣��֮�����ϱ���ʱ�ڣ��������εķ��룬�ֳ�������ѧ�뱱ѧ������������ѧ�ڲ�Ⱥ����˵����ʦ���ۣ����Dz�����ʮ��ǧ�����ֹ۵㣬�����������۲��ݣ�����ˮ����֮�ƣ���ʹ�徭Խ��Խ�ң�ʥѧԽ��Խ��֪���ƣ��������˸����Ͳ�֪��������˭˵�öԣ�˭˵�ô���
����������ʱ��ӱ������ˡ�
�����������ඩ���徭���塷���ų���ѧ�ڲ��ļҷ�ʦ˵���Ż�֮��������ѧ�����Ŷ���������Ա������������ϱ�֮ѧ�ĵ���ƫ�������ݰټң��ں��ϱ����ֽ����������ľ�ѧ�ɹ����б��棬ʹǰʦ֮˵�������𣬺��ѧ��������������ν��κ���ϱ���������ѧ֮��ɡ�
�����������徭���塷����֮��̫��ʢ�ޣ���گԻ������Բ��۹Ž�������Ǣ����ǰ��֮��˵����ʥ��֮��ּ��ʵΪ���ࡣ��
�����������徭���塷���Ƹ�������������У�����ȫ������Ϊ�˿ƾٿ��Եı���һֱ�������γ���
���������������Ե��游���ף�Ҳ�����Ƿ��ˣ��Կ�ӱ�↑ʼ���︸����������ι���˾ҵ��ʱ�˴�Ϊ��̸��
�����������������ֳ������ԣ���Ȼ�ڹٳ���û��ʲô��Ϊ������Ҳ�Ǻ������Ӻ��������ɵ�ʼ�档
��������������һ���ˣ���Ȼ���ʸ�վ������ָ��л����
���������Ҳ�˵����������������ѧ�ļȵ������ߣ�����л���ڡ����ʡ��в����������ڵ����ۣ��Ʒ���̫�游�۶ϵ���Ϊ����ͷҲ����ס��
���������������ԣ���ü�����������ʡ�һ�飬��Ҳ��������Լδ����ЩΣ�������ˣ��װ�������ô˵����
��������л��վ���������������ڹ���һ�������粻�壬�����粻��������ʱ�ڣ��ټ������������ī���������ޣ���˼��֮�貣�Ӱ��֮��Զ������˸������һ��һ��������֮���⡣��ʱ���Ӱټң��������������һ�ˣ��������ƣ����ڦ���˴�ڵ�ѡ���Ȼ���ǿ����ǿ������������ȴҲ�������ᄎ����������������������ʹ��������̡����̵�������ӱ�������õ��˼���ط�չ����
��������������ʱ�ڣ����н��Ĺ���֮�����ҷ�ʦ��֮�𣬺�����֣���������֣��֮���������ɱ粵������֮ʱ����ѧ֮ʢ��ȴҲ�ǹھ��������ϱ���ʱ����ȻȺ����˵����ʦ���ۣ�����������Щ���۲��ݵ�ѧ˵�������С��徭���塷�Ĺ�ɲ��ۣ����ݰټң���
���������������������������������徭���塷��������˵������ȡʿ�����Դ�Ϊ����Ȼ��������ѧȴ˥����˹���������������ƴ���ߣ�Ψ��ӱ��һ�ˣ��ν⣿�˹̲��Է⡢������·֮��Ҳ������������������ɼ�֮�ˣ�����������ʥ�ͣ���ȡ��֮��Ҳ�����ھ�˼֮����
��42�¡����ۡ���������
�˻�һ�������������£�����ʼ��ü��˼����������ȴ��ߵ��������ֺαع����Ҷ��������Ϸ��ʱ˵�����ɱ��ˣ������˵���������ڴ˵��б��Ҳ�Ͱ��ˣ����ɽ�а�鷢�ŵ����ӵ����У���
��������л����Ȼ���������˵������һ�˿ɴ��������Ӻ�����
����������������Ц�������Ϸ�һ�ˣ���Ȼ���У�Ȼ�˵��У�����������ɴ�֮�𣿡�
��������л��Ц��������Ȼ���С������ʡ�����������д�����ȴ��ʥ��֮�ԣ��ǷǶԴ���ֱ��Ӱ�쵽���ҵ��˲�ѡ�Σ�ʩ�����룬����Ӣ����������£�Ҳ����һ�˶��ϡ����£���������֮���£�����ŵ���ǰ����λ��ߣ�ȴҲ�����Ը�λ������������֮��Ŀ�����ҵ���ʥ����������֮�ĺ��������ҵ����ⷽ��֮�أ�̽�ֳ����Ķ���������ζµ�ס�����˵�����֮�ڣ���
����������������Ц������������ɫ��л���˻���Ī����˵�ҵȽ������������Ѻ�����
��������л����Ȼ���������ң�Ϊһ��ı���ޣ�Ϊ����ı���ǣ�������Ȼ���ţ�ȴ֪������������ƥ������ĵ�����������һ��ֻ֪ά����ѧ����Ӫ������λ���������˥�����Ҵ��������ˣ��˵�С���о���������Ϊ���ݡ���
�������������Զ�ʱ�����Ǻ죬�������촭�������ˣ������ϵ���̨����л�����˹�ȥ������ë���ӣ��Ϸ�ɱ���㡣��˵��˻������뿪������ɱ�����ڵس���л���ķ����ȥ��
����������Χ�ļ��ˣ���æ����������
��������л����վ��ûվ������һ�����������Ϯ����̨�������̼������������Ե������Ӷ��ڲ����֣��������Ǽٵ�ѧ����С�ˣ������������
��������������ŭ���������λ����֣��Ϸ�Ҫɱ��С������
��������л������վ�����������ڵ��������ǿ���Ҫ��ȭ���Ϸֳ�ʤ��������Ψ�з��㵽�ף���ſ������ǡ���
���������������ԣ�������Ǿ���һ�顣л����������һ�װ˼����긻��ǿ�����ۿ����ԣ����߲���һ������������˥����Ҫ�������������Թ���һ���غ϶���ֲ�ס��
�����������������ǿ�������λ�������µ����꣬��ͬѰ����һ�棬̫������·�����ˡ�
�������������������У�ȴ��¶��һ˿���ͣ�������ϲ���������Զ�Ϊ����������������ɣ��·������������������������һ�һ˿���յĻ��������顣
��������������������ɫһ����������ˣ�̫�����ˡ���
�����������Դ��ԣ������Զ�ʱ�������ˣ���л��˫˫���ڵأ����������
���������������һ�����������ɣ������´Σ��������ģ���
������������վ��������������������һ���£��ž���ͻȻ���ڵ������װ��Բ�Լı����˽��ȴ��֪�װ���־�����Σ���
���������������ԣ����ж���һ��������л���Լ�������һ㶣��ž��������ж�л���IJ�����������ɵ�Ӷ����ó�����
���������ž�����Ϊ��̳�����������壬���������������ӵ����䣬�������dz���֮�У��������ϵ��������������������ʱ��ʵ����̫��Ҫ�ˡ�
��������л������Ц������ĩѧ����ѧdz��������־��Ψ������ϲ�����Լ�����������֮�Ƕ��ǣ�������֮�ֶ���Ҳ����
���������˻�һ˵��������Ȼ����������Щ�����ʡ���л������ܴ��ý�������ҵ��ˣ�Ҳ���ò�����л���ļ�˼���IJš�
�����������ã���һ��������֮�Ƕ��ǣ�������֮�ֶ��֣��˽���֮��Ҳ����ʿ�������飡��
�����������Զ�ʱ�ͼ��ˣ������£����ɣ���
����������������ؿ��˿���һ�ۣ����������Ѿ��飬������ԣ���
�����������Կ������ڱ��������ʱ������������Ҳ���ҿ��ڡ�
����������ʱ�������������ֿ��ڵ����������жԡ����ʡ�һ�飬���������ߣ��ɳ������װ�߳�ʡ����ã���������¼�������۽���֮�����������ǧ���Ӿ��ϡ���
���������������ԣ�վ���������ߵ����֮�У�����ڵأ�����������ּ����
�������������Թ�Ȼ�ֳ䵱�˼��ȷ�Ľ�ɫ����л���ڡ����ʡ����Ե������Ա����ƶ���֮���ƣ���֮Ϊ��Ȼ�������ƣ�����֮��Ҳ����ˮ֮����Ҳ�������в��ƣ�ˮ���в��¡����ˮ������Ծ֮����ʹ��������֮����ʹ��ɽ������ˮ֮���գ�������ȻҲ����֮��ʹΪ���ƣ�����������Ҳ������л�����ν⣿��
��������л��Ц����������������Ϊ�٣����ڻ�����Ϊ�ס�����ͬ�֣�ζʵ��ͬ�����ʿ����˺ι�Ҳ����
��������������Ȼ֪����ˮ����ͬ��Ȼ���˿�ȴ���ҽ��˻�˵���ڣ�ֻ����ߵ������������˰�����ȣ���
��������л��Ц����������ˣ������پ�һ��������������������һĸͬ�����ֶַ���֮��һ�������������ң�һ������������֮�֣���ʮ������˳�����ˣ��������
�����������Կ��ڵ���������֮�ģ��˽���֮���߶�֮�ģ��˽���֮������֮�ģ��˽���֮���Ƿ�֮�ģ��˽���֮����������������˵�����˽Կ�Ϊ�ƣ����ֵܶ��ˣ�����֮��һ��һ�������ܹ����������ı��ʣ���
��������л��Ц����������֮�ģ���Ҳ���߶�֮�ģ���Ҳ������֮�ģ���Ҳ���Ƿ�֮�ģ���Ҳ����������˼���������ǣ���������֮����
�������������ư�������ȻҲ����
��������л��Ц�������������ӝ�ˮ֮ʱ�������������ң�̸��һ�����¡�ʮ����ǰ�����ڵ����踮����һ��Ӥ����������ɽ�֣�Ϊһĸ�ǵ��ߡ���ʱ����ĸ����ɥ���ӣ�ĸ�����ģ�����û�гԵ��Ǹ���Ӥ��������֮�����ӣ�����֭���丧����������ǰ����Ⱥ��ɽ��ͻϮ�����dz�������Ӥ����ë���ݣ���ֹ���ǣ���ë��Ѫ�����˶��ɣ����˽Գ�֮Ϊ�Ǻ������ʿ���������Ϊ�����������죬���������Ǻ��ڣ���
���������������������˵ȷ��䴫�ԣ������֮����
����������һ�أ�л����û�п��ڣ����ָ��͵��������²��Ƿ��䴫�ԣ�����ȷ�����¡���ʱ�����踮���������࣬���»���������ģ��ŷ��踮ȫ���ô��Ǻ���Ѻ�;�ʦ����
������������һ�����������ڻ��룬�������ž���������Ϸ�Ҳ�����ˣ������챦���꣬����ʫ��֮������飬��ʱ���£������ϳ��ἰ�����¡���
���������������ԣ���Ż���������Ц���������������������ˣ�ȷ������һ����ֻ��ϧ���շ��踮�������ģ�ֻ��һ��ʬ�塣��
��������������ôһ˵�����ǽ����¸ǹ����ˣ�˭�ҵ�����������˵�ѣ�
����������л����ʱҲ��ᵽ���ž�������⡣
���������������֮�е����ƣ�ȷ�Ƕ��Լ��dz���������ʱ��ȥ��������֮�⣬��λ��������ͺ���Ҫ�ˡ�
���������ž���������ʱ������˶��Լ��IJ����������������ָ�������һ���źţ��������Լ�����ͬ������Ϊı�������ָ���������£л��������ѩ����̿�Ļ��ᣬ��������ס������ȵ�ʲôʱ��
�������������ָ�ȷʵҲ�����ˣ���ǡ���ô���ʱ���ֳ����Լ���л����֧�֡�
�����������ʱ�������ܵľ�Ҫ������ˣ�����Ȼ��ѧԨԴ�������ǺóԵ����ľ��ҷ���������ȷʵ�����Դǣ����ƻ��䣬��ʱ��л���ٳ�������ӣ���ʱ��Щ�����룺��л������˼����ʥ�˴��ˣ���
��������л��Ц��������֮ʥ�ͣ������ǿգ����أ��������飬��˼�Ǽ�����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