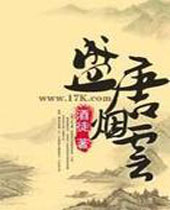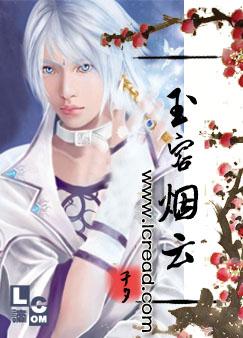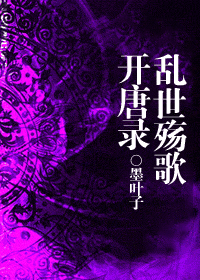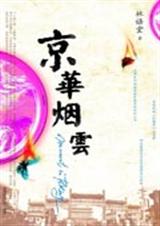开唐烟云-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宪笑道:“李祭酒此言甚是,韩郎才思敏捷,文采斐然,那柳姬眼光倒是不差,所托幸人也。来人,满樽,赐金百两。”
三题演罢,谢轩的心里却掀起了滔天骇浪,答题的这四位仕子,他竟然全都知道,俱是留名于后世。
史书古籍中对张彖倾注的笔墨虽少,但是其是天宝年间的进士出身,又以学识渊博、经纶满腹闻名远近,后世的成语冰山难靠便是出自于他的典故,以一语而名垂青史,自然不可能是普通人。
而钱起和郎士元亦同为进士出身,两人均在大历十才子之列,齐名于世,时人有“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之誉。史料记载,其时,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无钱、郎赋诗送别,则为时论所鄙,由此可见,其二人诗才之盛。
而韩翃可就更有名了,抛开其大历十才子和进士的出身不提,他可是传奇里面的人物,一篇《太平广记•柳氏传》,章台柳的故事,后世谁人不知?
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一届樊川诗会,随便遇见的便都是这等的人物,强汉盛唐,果然是名不虚传。这巍巍大唐,简直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谢轩这一边心中波澜壮阔,而爵室之内,一切却都按部就班,接下来便轮到张九龄出题了。
张九龄正想要开口,却不想被李宪打断道:“张公且慢,老夫与两位宰辅已出三题,然我观幼安却安坐于榻,岿然不动,莫非是嫌老夫与两位宰辅所出的题太易不成?”
谢轩心道:“这真是标标准准的躺枪!”他心中虽然这么想,但是表面上却不敢流露出分毫,“大王明鉴,末学才疏学浅,资质愚钝,非是不答,实是不能也。”
李宪笑道:“幼安太谦矣,以汝之才学,些许小道,岂非是信手拈来?”说完这话,他又看向张九龄道,“张公亦是文坛巨宗,这令题可不许出得太易了,不但难度要大,亦且要博古通今,妙趣盎然,张公以为如何?”
张九龄拱手笑道:“大王有令,子寿安敢不从?”
李宪又转向谢轩道:“我素知幼安才情高远,是以这答令的时长,也要有些限制,幼安你看如何?”
谢轩躬身道:“即是大王有令,那末学也只能抛砖引玉,投砾引珠了,还请大王赐教!”
李宪笑道:“抛砖引玉,投砾引珠?此喻甚妙,幼安果真是出言有章。”顿了一顿,他又道,“古有曹子建七步成诗,我观幼安之才不下于子建,不若就以三息为限。若是超过时限,即便是答出了,幼安与这美酒也要无缘了。”
众人闻言神情都是一变,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李宪此举是为了替谢轩扬名,然而要求却殊为苛刻,如果谢轩在时限内,答不上来,反而会弄巧成拙,沦为笑柄。
张九龄虽是对谢轩的文才充满信心,心中却仍是不可避免地替谢轩感到担心。这实是因为关心则乱,因为一个不可与人言说的原因,使得他对于谢轩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不过以他的文学造诣和心胸城府,仍是可以做到不着痕迹地替谢轩争取到思考的时间。
张九龄看向谢轩笑道:“幼安,老夫这里已然有令了,此令开句以一种花落地无声,次接一名与之相关的古人,此古人又须引出另一个古人,前古人问后古人一件事,后古人以诗文二句作答。”
在座的诸人不由地拍案叫绝,此令的规则立意新颖,妙趣横生,不愧是出自文坛巨宗张九龄的手笔,但是另一方面众人却又为谢轩开始担心起来,此令的难度,不言而喻,谢幼安真的能在三息之内,对出佳令吗?
张九龄笑道:“幼安,听好了,老夫的令题是雪花落地无声,抬头见白起。白起问廉颇:为何不养鹅?白起曰: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就在在场诸人还在沉思之时,谢轩连一息都没有用到,就直接开口道:“张公,末学有对了。”
此言一出,满座骇然,就连对谢轩充满着信心的张九龄也是讶异不已:“幼安不妨对来。”
“笔花落地无声,抬头见管仲。管仲问鲍叔:如何不种竹?鲍叔曰:只须三两杆,清风自然足。”
李宪立马拍案而起:“好个只须三两杆,清风自然足,道出了我大唐文人的浩然正气,一身傲骨,此对堪称妙绝,妙哉,妙哉,妙哉!”
在场众人也都是识货的人,其余暂且不论,张九龄以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来答为何不养鹅,稍显勉强;而谢轩以只须三两杆,清风自然足来答如何不种竹却是妙到毫颠,堪称神来之笔,就更不要提尽抒文人意气的一句清风自然足了。
众人叹为观止,谢轩却是心知肚明,在原本的历史中,此令题是由几百年后,同样是文坛巨匠的苏轼所出,而答令的秦观、黄庭坚、佛印和尚亦都为文采斐然一时,名传后世的文学大咖。这样的阵容再加上酒令本身,想不留名千古只怕都难。
谢轩虽然不知道这条酒令为何会提前几百年,由张九龄之口说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拿来应付危机,糊弄差事。
这时,李宪突然又开口道:“幼安果真高才,可否再应一对,以飨我等?”
众人闻言,心中顿为谢轩抱不平,如此酒令,急切间觅得一对,已是难得,宁王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不想谢轩却是张口就来:“蛀花落地无声,抬头见孔子。孔子问颜回,因何不种梅?颜回曰: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满座皆是赞叹之声,李宪长叹道:“好个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我观幼安所应二对,收尾诗句,皆未流传于世,莫非是急思间所得?”
谢轩躬身道:“末学才疏学浅,让大王见笑了。”
李宪长叹道:“幼安才学,真是让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啊,奇才,真奇才也。”然后,他话锋一转,“坊间相传,幼安半载以来,客居潏水渔舟之内,老夫心实痛之。老夫在曲江池南岸有一处别院,幼安若不嫌弃,便赠予幼安了,聊表一些心意。”
谢轩闻言,正想开口婉拒,却被李宪伸手打断了:“幼安不必多言,皇朝盛世,大贤囿于渔舟方寸之地,我等臣子之罪也,不知则已,既已知晓,安能无动于衷?弃明珠于市井,遗贤才于荒野,幼安莫非是要陷老夫于不忠不义乎?”
这一顶大帽子一扣,谢轩也不敢多言了,当下只得俯身称谢。而在座的文人仕子,也丝毫没有产生出妒忌之心,实是在他们的心中,以谢轩的文才,这一切都实以当之。
以文才闻名当世,得宁王以国士相待,身为文人,只会与有荣焉,而绝不会产生丝毫嫉恨之心,这与后世的文人相轻,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有此佳令开局,宴席间的气氛顿时就热切起来,一时间,爵室内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第9章 樊川诗会 四()
转眼间,亥时已至,皎月星河之下,一河潏水泛银,数声鼓乐演毕,李宪站起身来,双手抱拳举在左胸之前,面朝皇城方向,朗声道:“请贡卷!”
所谓的贡卷,乃是用宣州贡纸所制作成的书卷。这种纸张在唐代的时候,品质最为顶尖,市面上,即使是重金也求购不到,历来为皇家内苑所专用,除此之外,也就是历年的科举考试和这樊川诗会才有资格特例使用。
而有资格进入爵室的十位青年才俊,所用的则是翰林学士起草制书所专用的黄绢,规格比之贡纸,则又是要高上了不少。
随着李宪的这一声令下,守候在甲板上的那些奴仆,立刻将早已准备好的纸卷连同墨砚、毛笔一干物事逐人分发。唐代还没有后世那样装订成册的制式书本,而是像后世的书画一般,翻卷成卷,家庭富庶者还常有装裱,贫寒者,往往是将拼贴起来的纸张一卷了事。是以,分发到人手的纸卷,在食案上长长铺开,倒也是蔚为壮观。
爵室内,黄绢分发到各人手中,众人均是开始研墨、润笔,须臾间,便开始奋笔疾书。樊川诗会历年来的重头戏便是以诗咏月,这么多年来也未曾有过改变,在座的众人为此已经准备了一年乃至数年之久,佳作早已是在胸中酝酿日久、倒背如流,自然不可能会有文思凝滞的情况发生。
不多时,众人便已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在黄绢上书写完毕,待墨迹一干,便小心翼翼地将之卷成书卷,放在食案左上角的托盘之上。
侍立在一旁的奴仆见状,则是拿起食案上的托盘,恭恭敬敬地将其送至李麟的案前。
这同样也是有着规矩的。此届樊川诗会的主事虽然是宁王李宪,又有当朝的三位宰辅亲临,但是推选诗魁的权力依然是掌握在国子监祭酒李麟的手中,而其他人顶多也只能拥有建议权。
国子监祭酒推选出诗魁之后,诗魁所作的诗文同样要在楼船上张榜,以子时为限,有自觉诗文胜于诗魁者,可以举卷自荐,若是诗文确实出彩,则诗魁之名便会易于其手。
但是这种情况,樊川诗会举行了这么多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原因也很简单,唐代虽然诗文鼎盛,才子辈出,但是其中的佼佼者,或多或少,都已经打响了名气,很少有沧海遗珠的事例发生。因此能有资格最终进入爵室的,无一不是有真才实学,文采斐然的才子,诗魁之名自然不太可能会旁落他处。
而历届樊川诗会的诗卷,最终又都是要封存入库的,其后会有专门的官员对所有的诗作进行核查。以现如今朝堂三足鼎立的局势,无人能够大权独揽,自然也就没有人敢在此事上徇私舞弊。否则,一旦被政敌抓住痛脚,轻则罢官,重则丧命,一世英名附之流水,终究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李麟将面前的黄绢一一打开,观赏完毕,突然长叹一声:“吾今日始信盛名之下无虚士!幼安之才如清风朗月,高山流水,当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自惭形秽,吾不及多矣!”
众人闻言,知是谢轩又出了佳作。李宪迫不及待道:“拿来让老夫一观。”
李麟闻言亲离坐席,将手中黄绢送到李宪面前。李宪展开黄绢,迎着烛火展开,心中诵读完毕,同样长叹道:“此世间真有生而知之者邪?”
两人的表现顿时让众人的心中如猫抓一般,张九龄身为文坛巨匠,就更是心痒难耐:“大王。。。”
李宪顿时就明白了张九龄的意思,转头对身边的侍者道:“拿去送给张相。”
张九龄接过黄绢,急切地展开一观,顿时也长叹道:“有此珠玉在前,只怕以后的樊川诗会,这咏月的诗文怕是不好作了。”
身边的李林甫闻言,急忙将黄绢讨要了过去,又经过杨国忠之手,最终回到了李宪的手中。
李林甫和杨国忠虽然自己作不出什么像样的诗文,但是好坏却还是分得清楚的。谢轩今日一系列的表现,已经深深将二人折服,心中都不免升起了将其收入麾下的心思。
这时,李宪对着身边侍立的侍者开口道:“念于众人共赏。”
侍者接过黄绢,朗声诵读:“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诗词念完,满座寂然。良久,也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声,爵室之内,顿时喝彩声一片,不时有人复诵其中的佳句。
盏茶之后,爵室中重归寂静。
李宪开口道:“老夫以为,可以张榜了,三位相公,李祭酒以为如何?”
面对此咏月的千古佳作,四人自然不可能会有反对意见,齐声道:“大王此言甚是。”
几人达成一致,国子监丞立即就去安排张榜事宜。
不想此举,却顿时让甲板之上的文人仕子一片哗然。只因樊川诗会举行了这么多届,像这一次一刻之内,决出诗魁的还是首次。虽然此时谢轩的诗才已经名满京师,夺取诗魁早已是没有悬念,但是这种速度,依然是让人感到惊讶,难免会产生质疑。
然而随着谢轩所作诗文的传开,这种质疑瞬间便荡然无存了,众人的心中只剩下了钦佩,同时还是浓浓的羡慕。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鱼跃龙门。以玄宗对诗文的喜爱,以谢轩的才学,只要不像李白那样肆意张狂,只怕不出几年,朝堂之上,便会多出一位新贵。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子时已过,这一届樊川诗会的诗魁推选总算是尘埃落定。众人送走宁王李宪之后,宴席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却少有人散去,这其中,自然是有不少人是想要留下来,结识谢轩这位未来的新贵的。
但是,这时建宁王李倓却站了出来。李倓本身就贵为亲王,又是太子的子嗣,他这一出面,便是三位当朝的宰辅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反正也是来日方长,也无须急切在这一时。
离开楼船,坐在李倓自家的游船之上,李倓一边给谢轩倒酒,一边道:“谢兄本就以诗文誉满京都,今夜更是如潜龙在渊,一飞冲天,夺得诗魁,只怕不久就要被阿翁召见,前途可期,真是可喜可贺。”
谢轩淡然道:“李兄过誉了,只是侥幸而已。”
李倓笑道:“何言侥幸?谢兄过谦了!”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噗嗤一声笑出声来,“谢兄可知,那杨奕为何要故意找你的麻烦?”
谢轩惊讶道:“在下只道其人纨绔而已,然听李兄的意思,竟然并非是如此?”
李倓笑道:“自然不是,杨奕虽然其蠢如猪,但是幼安你誉满京师,声名在外,若只是看不顺眼,他还不至于当众做出这种蠢事。”
谢轩奇道:“听李兄的意思,难道是在下无意间得罪了他?”
李倓道:“说是得罪倒也不算是错,其实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女人争风吃醋罢了。”
谢轩道:“李兄莫非是在说笑,消遣于我?在下于渔舟之上,呆了半年之久,连潏水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