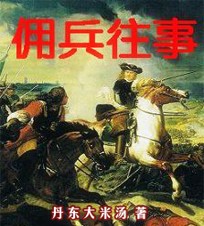清风吹散往事如烟灭,续-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惠芬见是当地找来做粗活的女奴,也没在意,自去取了脸盆来舀水。
楚言怪道:“阿依古丽几时听懂汉话了?竟知道我在叫水!赶明儿,可不能背地里乱说话了。”
惠芬有些好笑,正想说不过是碰巧正要送水进来罢了。
却听那个蒙古女奴说道:“回禀公主,是奴婢告诉她的,奴婢是汉人。”
楚言和惠芬都是一呆。
那女子上前几步,跪倒在地:“请公主救救我的女儿。”
楚言回过神:“起来吧。慢慢把事情告诉我。”一边仔细打量这名女子,面颊黑红粗糙,就是一个粗作的下层妇女,五官却比突厥人蒙古人纤细柔和,听口音象是中原一带的。是被人口贩子千里迢迢卖到大漠来的?还是被强掠来的?哈密有清军驻扎,干什么了?难道官匪勾结?还是,象郭靖他妈一样,家庭发生变故,辗转流落到此?那样的话,她女儿不就是女郭靖了?
那女子一张口,未出声,先落泪。
惠芬见楚言半天没吭声,猜想是那走神的毛病又犯了,柔声对那女子笑道:“要公主救你女儿不难,可你总得先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没头没脑的,让公主怎么帮?就从你叫甚么名字,家住哪里,怎么到了这里为奴说起吧。”
“是。奴婢娘家姓韦,唤名芝华,祖籍关中。”喉间哽了又哽,方才艰难地说道:“奴婢命薄,遇人不淑,以至沦落为奴。”
惠芬不满道:“你既央求公主相助,却又言语闪烁,遮遮掩掩,不肯吐实。这么藏头藏尾的,无处查实,谁知道你是不是别有居心?”
韦芝华急忙顿首:“奴婢不敢,奴婢说的都是实话。”
想她原是好人家的女儿,一时糊涂,做出有辱家门之事。这些年来辗转漂泊,孤苦无依,历经苦难,曾几次寻死,只是放不下女儿。回想当日,就觉得种种磨难都是当初杵逆父母的报应,无颜再见父老,心中唯愿爹娘以为她早死,不愿再令家人伤心屈辱,甚至刻意隐藏家乡来历,就是对女儿也不曾说过。今日,听说大王子与王妃路过,想起曾听说这位王妃是大清公主,不由触动她长久以来的思虑。她这一辈子,无论怎样,都是活该,可女儿是无辜的。她的命运不应该重蹈于女儿身上。避开主母,她主动对主人,也是她现在的男人,提出愿意过来服侍,又抓住机会引起了王妃的注意。这样的机会,不会有第二次。
韦芝华拿定主意,最要紧的是取信于公主,让女儿逃出火坑,其他的罪,她可以用这一生和以后的生生世世来赎:“回禀公主,奴婢家住——”
“我相信你。”楚言突然说道。
韦芝华又惊又喜,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啜泣。
惠芬讶道:“公主?”一块儿呆了这些日子,她怎会不知道?这位主子虽然好相处,可只是面上随和爽快,心思是极重的。取信于她,并不容易。
“我相信你。”楚言微笑着又重复了一次:“我知道你有很多伤心事,不愿意提,就不必说。我不喜欢说话时得盯着别人的头顶,你先站起。告诉我,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出了什么事儿?要我帮什么忙?”
“她上个月满八周岁。她出生时,主人在喝酒,顺口起了图雅这么个名字。我悄悄给她起了一个汉人的名字,叫做猗兰。”
从她开口说话,楚言就觉得这个韦芝华态度从容,谈吐不俗,暗暗存了好感,猜想她有些来历,也能体谅她不愿连累家人名声的心情。听见她给女儿起的名字,不由问道:“兰之猗猗,扬扬其香。可是这‘猗兰’二字?”
“正是。这孩子从会走路就帮着干活,做饭浆洗缝补带孩子都做得来,性子也安静谨慎。若能让公主看得顺眼,留在公主身边做个小丫头,就是她的造化了。”
楚言更加怜惜,几乎已经打定主意要帮这个忙,却想到一个问题:“你女儿的生父,是什么人?是蒙古人么?”万一这女儿是她和现在这个主人生的,这事儿可棘手。
“是汉人。奴婢被卖到大漠时就已经怀着她。”
楚言很想问个究竟,到底克制住了好奇心,沉吟片刻:“你把她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看看,再做道理。”
这就等于是答应了。韦芝华心中一块大石落地,欢喜得又落下泪来,忙忙地磕头谢恩。
楚言也不拦她,却问:“你,不想同你女儿一起走么?”无非是要想个说法打动阿格策望日朗出面,带一个走和带两个走没区别。看她们母女相依为命多年,倒是不想把她们分开。
韦芝华红着眼摇摇头:“我还有一个儿子,刚两岁,是和现在这位主人生的。主人的大儿子粗笨愚莽,对这个小儿子倒很上心。看在儿子的份上,对我还好。”
楚言点点头:“我明白了。你先去吧,想个法子把你女儿带到我这儿来。”唤来阿依古丽,命她叫个人陪着韦芝华回去。
待到帐内只剩她们两个,惠芬低声埋怨:“公主这事做得鲁莽了一些。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多少双眼睛盯着公主!不知多少人想在公主身边埋颗钉子呢。我看这个韦芝华是个有心计的,又给她那个主人生了儿子,万一——”
楚言安慰说:“她再怎样有心眼,她女儿也不过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咱们这么大的人,还能被一个孩子给吓住了?当真别有用心,日后少不得要落下蛛丝马迹,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不会叫她讨了好去。难得在漠西见到一个同种同族的人,又是这么一个境遇,怎么忍心不帮?买一个女奴也不是什么难事。”
惠芬知她心意已决,心下也为韦芝华的遭遇恻然,便不再多言。
阿依古丽拿了油灯近来点燃,惠芬自去预备晚饭。
楚言和衣靠在榻上,闭目假寐。阿依古丽不敢打扰,悄悄退了出去。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时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当为王者香的猗兰,深陷于泥沼,与众草为伍尚且不能——韦芝华母女的不幸勾起了楚言的感慨。
回想起来,有关《猗兰操》的来历故事,还是四阿哥讲给她听的。说起《猗兰操》琴谱已然流失不可寻,四阿哥似是颇为遗憾。
他本是随意闲谈,可她惦记起文字狱,暗暗讥讽道:“从来的当权者,嫌文人不顺他心意,把人关起来不算,还要把书全找来烧了。点把火烧书容易,也不知多少好东西就是这么给烧没了的,后世的人再怎么惋惜也无处寻。可算央及子孙的第一事。”
说得四阿哥沉下脸,盯了他好一会儿,难得倒是没发脾气,闷了一会儿,还拨弹着琴弦吟了韩愈的《猗兰操》辞。
还有那回,她帮着何七种兰花。胤禩路过看见,笑了笑没说什么,回头画了一张《种兰花图》请她评点。
画上那旗装女子,眉目有几分像她,纤柔娉婷,扶着花锄,姿态闲适。她故意摇着头:“你这画,要是仕女图,我就不说什么了。要说种兰花,这画中人哪有点干力气活的意思?腰不弯,腿不屈,十指不沾泥,监工还差不多。”
他笑着辩解说:“理虽如此,美人种兰花,总不能与圃翁种兰花一样,画得优美雅致一些才好。”
她故作惊讶:“你不知美人与圃翁一样,也要上茅房,也会闹肚子?赶明儿,你画一张《美人闹肚子图》给我看看,美人怎么就优美雅致了?”
他喷笑出声,指着她的鼻子笑骂:“罢了,与你这村姑说不通。”
很多事,不管当初发生的时候,怀的是怎样的心情,数年以后的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亲切。那般压抑的皇宫,人人自危,小心谨慎,她还能这样张扬个性,除了天生迟钝,大概也是那些人宠出来的。
又想到最后一封信里,胤禩提到侍妾有孕。算算日子,顺利的话,那孩子比她的小上一些。希望是个男孩,平安降生,解决他无子的问题。现在,正是他人生的顶峰,春风得意。她只望他这样的日子多一日是一日,厄运的开始晚一天是一天。
想起这两个人,也就不由得想起他们已知的不可改变的未来,自己难以预测的前途。
感觉小家伙动了动,似乎传染了她的不安,楚言低下头轻声安抚:“不怕,有妈妈在。”
阿依古丽走进来报说韦芝华母女来了。
见到那个小姑娘,楚言立刻明白韦芝华担忧的原因。
八岁的女孩,衣服破旧但是干净,额头上有一道旧伤痕,但无损清丽,身体有些瘦弱,却有一股出尘的气质,眼神是不符合年纪的沉静淡然,仿佛八岁的人生已经历经无数看破尘世。下等粗俗的男人不能欣赏这气质的美丽,却很喜欢折辱这份气质。也不知有多少如狼似虎的眼睛盯着她,等着她再长大一点,再长开一点。再晚两三年,她只怕就要被推下无底的深渊。
转而看向韦芝华,她的身上隐隐还有一些与女儿酷似的美丽,想必这些年为了保护女儿,她吃了不少额外的苦楚。随着她的美貌被苦难渐渐磨去,女儿的美丽日渐引人注意,她将再也无法将保护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蹂躏侮辱。
“你会唱歌吗?唱一首童谣吧。”
韦芝华连忙推了推发愣的女儿。小姑娘轻轻唱了起来。
楚言微笑起来:“我有些饿了。阿依古丽,去看看晚饭准备好了没有。告诉王子,我等他共进晚餐。”
阿格策望日朗瞟了一眼帐篷里多出来的小丫头,也不说什么,等着楚言来告诉他。
楚言却忍住了,只同他说些天气行程的话题,直到用完晚饭,喝茶的时候,才对小姑娘笑了笑:“你的歌唱得很好。再唱一首,让王子也听听。”
小丫头在帐篷当中站了一顿饭的功夫,上菜倒茶递水回话的人从她身边来来去去,紧张拘谨是免不了的。她低着头,努力把自己缩得小些,碰到有人端着东西从她身边经过,会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往旁让一让。一肚子的疑问彷徨,却一声不吭地忍耐着,等待着,听到命令,她躬了躬身,打开嗓子。
楚言笑道:“垂着头,把喉咙都憋住了,可怎么唱歌呢?”
小姑娘滞了一下,缓缓抬起头,小心地让视线落在两位贵人身前的桌案上,在阿格策望日朗冷森锐利的注视下有些瑟缩,声音有些发颤,曲调倒还算流畅,身体仍然站得笔直。
阿格策望日朗调回头,望着妻子,等着她的说明。
楚言对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女孩非常满意,喜笑颜开:“怎么样?我是不是捡到宝了?这个女孩我要了。”
他皱了皱眉,他承认这女孩漂亮温顺也很有勇气,再长大一点,会让很多男人动心,可是不明白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怎么会是她的“宝”:“你能让她做什么呢?”
“我准备让她做孩子的侍女,让她专心陪伴照顾我们的孩子。”
“她太小了,什么也不懂。我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她。孩子会有保姆嬷嬷照料。”
“不是把孩子交给她。能找到一个妥帖能干的保姆嬷嬷,当然好。可我是母亲,抚育教养孩子是我的事,惠芬和阿依古丽可以帮助我。即使还有保姆嬷嬷,大人总有大人挂心的事,有个什么事要走开一下。过不了多久,孩子会爬会走了,还要有人陪着玩,保姆嬷嬷恐怕不会有那样的体力和心情。我想给孩子找一两个能够照顾他也能够陪他玩的侍从。我觉得这孩子很合适。”
阿格策望日朗让人打听过韦芝华的来历,明白她的民族情绪。她高兴就好,多买多养一个小奴隶没什么,她事先打招呼,他就该高兴了:“你喜欢,就留着,让人告诉她的主人一声就是了。”
楚言皱着眉:“她的主人很好说话吗?嗯,她母亲还要留在这里呢,我可不希望这丫头心里挂着别的事。”
“买还是要?”他听明白了,妻子有事,丈夫服其劳,还得劳得合她心意。
“当然是买,我又不是强盗!喏,这点金子,最少可以买三个健壮男奴隶。”
交待妥当,阿格策望日朗去找人经办,楚言就把韦芝华叫了进来:“明天一早,你女儿就要跟我走了。今晚,你们母女回去好好说说话,收拾收拾东西。”
韦芝华喜极而泣,拉着女儿磕头谢恩,回道:“按主人吩咐,奴婢夜里也要留下来预备使唤。公主容情,能否让猗兰留下服侍,奴婢回去给她拿身替换衣服?”
听这口气,竟是怕女儿回去过一夜都会发生变故!可巧,她也不喜欢临时变数:“你同王子派去的人一起回去吧。”
小姑娘晕晕乎乎的。今天傍晚,她正背着弟弟,提着比她矮不了多少的大木桶去打水,担心着回去晚了耽误了做饭要挨打,母亲匆匆忙忙地找来,接过水桶,叫她送弟弟到萨仁大娘那里去。等她跑到萨仁大娘的小屋,母亲送完水也来了。把弟弟托给萨仁大娘,母亲急急地拉着她就走,只在路上停下帮她理理衣服,拢了拢头发。她想问怎么回事,母亲已经陪着笑脸,迎着一个武士一样的男人走上去。
憋着一肚子疑问到这里,就唱了两首歌,呆立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让她做。突然,这位王妃就说要带她走。
悄悄地抬起眼,发现王妃正笑眯眯地看着她:“你愿意跟我走吗?”
愿意两个子从心底浮了上来。王妃给她很亲切的感觉,她的容貌她的语言都述说着,她和母亲一样是从“关内”那个美丽的地方来的。她从没见过的故乡,她本该属于的地方。
“我该叫你什么呢?你喜欢叫图雅,还是叫猗兰?”
第一次有人询问她的意见,小姑娘认真地思考着,犯了难。猗兰是母亲给她起的名字,母亲不喜欢图雅这个名字。只有母女俩人的时候,母亲叫她猗兰,轻轻地念些诗句,告诉她兰花是多么美好高贵。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兰花。她喜欢听母亲吟诵,但是听不懂。图雅只是一个女奴,永远不可能高贵,她已经习惯了图雅这个名字,放弃这个名字令她无所适从。
楚言了然一笑:“还是叫你图雅吧。猗兰这个名字对阿依古丽他们恐怕太难了。”
次日早起,所有人又一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