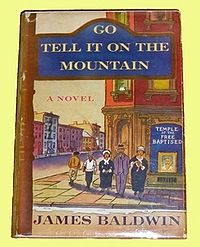冬衡山上的落日-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惯不怪的陈衡霖,却在一旁冷眼的看着鄂飞的举动,还打着哈欠,似乎没睡醒。
面对鄂飞的举动,她说:“喂,你怎么像个神经病似的,语无伦次,手舞足蹈,不就是别样天空吗?”
“你这十三妹呀,别打断我,让我发泄发泄。”
“什么?你叫我十三妹?你啥意思呀你?”
“疯完再找你,你先到一旁睡去。”
“神经病。懒得理你。”
“记住不要走太远哦,你可是要保证我的安全的哦,还要带我下山的哦。”
“神经病,国语都讲不好,还学台湾腔。”
“十三妹,你已经连续说了三句神经病了,你可是导游,我可以投诉你的。”
“切,你疯完到上面的平台找我,我到那边去歇会。”说完走开了。
站在祝融峰之颤,往下望的时候,山哥的话再次在鄂飞的耳边响起,眼前虽然被一片云海阻隔,但鄂飞似乎能望到谷底。
山脚下的小雨,半山腰的大雾迷茫,到山顶的烈日当空,同一座山,却是三种不同气候,在三个不同的位置转换着。
或许这就是山哥要说的:人不能只站在一个位置去看事物,不能在一个物体里把自己固死,往前一步,都是不同的感受与认知;一座山都可以有三种气候,人的一生又可只只摔倒一回?要学会换位思考,往上看看不到,那就站在高处往下看吧。
雨早过去了,雾也过去了,再过一会,太阳也都下山了,人还得继续走着。
没有永远的栖所,也没有打不开的心锁,那就让这些在穿山插雾中放下吧。
第八章 小十三妹
千里迢迢,南来北往,柔情车厢满怀。湘南群山,耐何溥纱层叠。飘零异土,恨长夜、无情细雨。明日何来有晴天,祝融峰观日?日落寄情金花,恐此情无缘,无意而去?两地相遥,南岳山得佳人相伴!千里追忆!无忘寒冬到此游。乐之,只是佳期不常有。
又似是:山路弯弯上九天,林阴绵绵纵万顷。祝融峰上有晴天,会仙桥上会知故。
他们开始向山下进发了,鄂飞已没有初上山时的又吟又跳了,平静的听着陈衡霖讲解着沿山的景点。
看到新奇的事物,还会问,很似陶醉在这场邂逅里。
路旁有农妇挑着担在歇脚,看见鄂飞他们走了过来,也招呼他们:“帅哥靓女,来喝碗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又解渴又能填肚子。”
鄂飞不解的问:“豆腐脑?什么来的?”还是那生硬的国语。
“哦,广东人叫豆腐花,来一碗吧,很新鲜的。”
“你咋知道我是广东来的?”鄂飞这回不是说好好的练习国语了,而日反问回去。
“听你口音就知道啦。”说完,把剩好的豆腐花递到鄂飞的手里。
陈衡霖嘻嘻的笑了一下,小声说:“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中国人,连国语都说不好。”
“吃吧,把你的嘴塞住,这么多废话。”说完把手里的豆腐花递给了她。
吃完付了钱,鄂飞他们又赶着去欣赏美景了。
“喂,你怎么叫我十三妹?”
“我还没问你为什么换了个妆了呢?”
“你?”陈衡霖有点诧异了,吃惊的看着鄂飞。
“怎么,我只不过把眼镜摘了下来,你就不认识我了?”
“哦,是你呀。可我换了妆了呀,而且还戴了眼镜呢,你是怎么认出来的。”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眼熟,本来我还不敢相信是不是你的,可是你那爱靠着陌生人肩膀睡觉的习惯怎么也改不了,在睡着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你的真头发。”
“你还真下流,老爱偷窥女生。”
“你除了下流还会用别的词吗?不要左下流右下流的好不好?我这叫欣赏。”
“你还不是强词夺理?不怀好意就不怀好意了,还摆出一副正人君的模样,什么欣赏。”
“哈哈,果然是十三妹,是不是湘妹子都这么辣的?”
“什么是十三妹?你这死广东佬,乱给人起名字。”
“哎哟,还骂人呢,说你十三妹还是不错的。”
“其实在火车上你的妆容才像个古惑女,所以才叫你十三妹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倒像个淑女了。”鄂飞接着说。
“淑女还差不多,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十三妹了,否则让你滚下衡山去。”
“尊命,十三妹姐姐。”说着还摆出一副敬礼的样子。
“说真的,你长头发挺好看的,为什么非要把头发弄短,然后套个假发上去?”鄂飞停了一回,问道。
“我只负责给你做导游,介绍景点,这此私人问题不在此列,恕不能从命。”陈衡霖一本正经的回答。
“现在不是正走着路吗?咱们聊聊天,解解闷嘛。”
“和你这种流氓没什么可说的。”
“我那里流氓了?我没有流氓到你吧?”
“表面是君子,内心是流氓,简称伪君子。”
“这躺旅游可真的值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没想到这么快就对我了解透切了。”
“承认了吧。”
“我决定,为了你,从此以后把“流氓”这个词彻底埋在心底,决不被它浮出来。”
“切,狗改得了吃屎吗?我看还是算了吧,你就乖乖的做了流氓吧,下山之后记远不要出现在本小姐面前。”
“因为我是人,不吃屎的,所以不存在改不改得了的问题。再说,要我不见你这不难,但是要我忘了你,已经不可能了。”
“你还是省点口水吧,不要在我面前花言巧语了。”
“而且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在你心里,已经把我铬在里面了,你就不要口不对心了。”
陈衡霖听完这句话,看似开玩笑,却又不像,而且是那诡谲的笑容。
迎合着吹过来的风,狠狠的打了个冷颤,任鄂飞可是一针见血的刺向了她,的确,眼前这个喜欢胡扯的男生,已经在她的心里扎根了。
慢慢的侵蚀着她的灵魂,浸遍她的全身,她说他的每一句骂话都成了骗人的幌子。
只不过,陈衡霖想不明白的是,任鄂飞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是怎么看得出来的?
陈衡霖再一次打了颤,心里再一次发出了碰撞:在此人面前,自己穿再多的衣服,包得再严实,也是赤祼祼的。
这个人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深澳,就凭自己的井底之蛙的见识,根本无法去猜测他想做什么?
陈衡霖靠在树前沉思,任鄂飞却举着相机对着山外狂拍,对于陈衡霖举动,他似乎已料到,偶尔偷偷的笑一下,他的一句:在你心里,已经把我铬在里面了。
已经把这个套着假发的女生俘获了,他也正得意着。
这一刻,不光是肖小兰在他心里消失了,连相恋了三年的申影也漂得无影无踪。
似乎他这次出游的目的不是为了洗刷内心的苦水,而是成了追女之路,背叛注定成了他的这次旅途的收获。
或者是经过了衡山之行,把他那夥多情的心给唤醒了,除了把锁了三年的心结打开,也把花花的心给打开了。
困锁了三年,孤僻过三年的心,就这样给一次衡山之旅而悉放。
邻家女申影无法带给了更多的欢乐,让他还徘徊在困惑中。
大方而开放的肖小兰,给他带去了快乐与激情,却还是无法让他走出在徐锋的阴影里。
衡山脚下的小雨,为他淋走了困惑。
半山腰的大雾,把的孤僻给缠走了。
祝融峰上的烈日,蒸发了他的阴影。
而陈衡霖,则是洗刷掉了身上不该有的戾气。
一连串的简单的拼凑,还原了一个真正的任鄂飞。
更是把一个困在牢笼里的老虎给放了出来,将来咬到的人又会是谁呢?也可能受到伤害的就是她——陈衡霖自己本人。
任鄂飞把镜头转回来,对着陈衡霖,笑着对她说:“把脸转过来,笑一个,给你照张靓照。”
卡擦一声,镜头停下,鄂飞冲着陈衡霖大笑着说:“看,沉思的女人才是最美的。”
陈衡霖已经不再去和任鄂飞争执了,微微的笑着冲他说:“是吗?给我看看?”
半山平台处,虽然是冬天,仍然集着很多游客,有些人还趁着有阳光,还在放风筝。
陈衡霖这次倒打一枪任鄂飞了:“广东佬,你说鹅绑了一根绳子还能飞吗?”
“如果是被你绑的,那情愿不飞了。”
“来,过来,那让我把你绑在这衡山上,看会不会把你冻成冰鹅。”
“你舍得不?”
“开玩笑,舍不得?成冰了然后再用冷水浇开你呢。”
“哈哈,我已飞进衡山的林子了,飞不走也不可能成冰的了。”
“我说不过你,说真的,你爸为什么给你起个这么难读的名字?鄂(鹅)飞。”
“我是在湖北出生的,所以叫鄂飞,我爸希望我能飞得更高更远;广东话的鄂和岳是同音的,要是用广东话来念,还蛮好听的。”
“那你得飞多远?飞多高?也会飞出衡山的一大片树林吗?”
“我要带着衡山这片树林一起飞走。”
“你带得了吗?这里树木何止万千?”
“我只带一棵就够了。”
“花言巧语。”听着这翻花言巧语,心里却像吃了蜜饯一样甜。
又说:“走吧,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也要下山了。”
“不急,我就是要等太阳下山,我不能错过这个日落。”
“你要看日落?”
“嗯,衡山上的日落是很美的,我要用来做我的毕业作品。”
陈衡霖无语了,她觉得这只是一个借口,她在想着日落后会发生的事。
可她现在却很从容,似乎无论会发生什么,她都能接受似的。
鄂飞却回过头笑着说:“别担心,我们不会在山上过夜的,我们一定会下山,你别想太多哦。”
说话的语气,还是怪怪的,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会‘想太多’。
这个‘想太多’还真是煽情,为什么偏要带着诡异的微笑呢?陈衡霖在心里骂道:你看得出来就算了,还非要说出来,无耻之徒。
“你是学摄影的吗?千里迢迢的跑来衡山取景?”
“我是学设计的,同学知道我要来玩,所以顺便叫我看这里的日落,这样毕业作品便有着落了。来到了,怎么也要看看是不是真的。”
“刚才在山顶我也看到了这上面的云海,我想,要是太阳落山那一刻,想必会更美,对于学美作的人的思维来推断,日落那一刻的云海伴着晚霞会更美。”鄂飞接着说。
“是吗?我在这里做导游,我还真没留意过。”
“呵,难怪你会说你没上过衡山了。”
“怎么说我没上过衡山呢?”
“如果是真正上过衡山的话,你应该会告诉我这些的,还有这上面的景色,哪里美、哪里比较好玩,可是这一路好像你都是跟着我走,在这方面的触觉你就没我强了。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却胜过你走过了无数次,这就是用身体去走路和用心去感受的区别。”
“你是说我只用双脚去走,却没有用心去感受?”
“嗯,从另一面说明你更本不想留在这里,我想你会告诉我为什么的。”
“你为什么不继续往下猜了?”
“老猜心,不累吗?”
一句‘老猜心,不累吗?’反而又再次让陈衡霖陷入了沉思,她现在却慢慢的开始在猜任鄂飞的心了,正一步一步的陷入去。
第九章 衡山的落日
才17点30分,太阳已进掉进云海里了,衡山朦胧起来了,一片柔柔的寒意笼罩在周围。
游客亦都下山了,随了山上的僧人和道人。
斜阳散在萧萧的树木身上,发出如夜光棒的色素。
成了朦胧的衡山上一幅水彩画。
任鄂飞箭步飞奔而上,直奔观日台而去,后面跟着跑得气喘吁吁的陈衡霖。
陈衡林一边跑,一边大喊:“笨鹅,你能不能飞慢点?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真的见鬼,怎么跟上这样的游客了?早知道不接了,跟着个神经病。”
不管陈衡霖怎么叫怎么喊,任鄂飞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是箭步而飞,生怕太阳就躺进云海里了。
走了一段,任鄂飞回头看看后面跟着的陈衡霖,没看到人跟上来,他也停了下来。
向山下喊了一声:“喂,小霖!”
没听到陈衡霖的回答,随即转过身往回走,转个弯远远的看到陈衡霖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正喘着气,抬着没力气的头转着脸说:“算你还有良心,还知道往回走。”
“疯丫头,吓死我了,还以为你丢了,叫人也不应。还能走不?要不我扶你吧?”
“要不你背我吧。”
“你说真的?”
“我现在的样子像是在说哄你开心吗?”
“还哄我开心,别以为你是在‘献身’,可是要我受罪的。”
“那你背不背?我反正走不上去了,我坐在这你又不放心,除了背我上去,你没别的选择了。”
“现在的九零后,还真的会占便宜,拿你没折。”
叭在任鄂飞后背上的陈衡霖,附在任鄂飞的耳边小声说:“我告诉你,我不是九零后的,那天我说我18岁,并不是虚岁,是周岁,我也是八零后的。”
这话似乎是陈衡霖故意说给任鄂飞听的,给他发个信号:我们都是八零后的,不会有代沟。
鄂飞见她这样说,也只是笑笑,打趣说:“我还以为捡了个九零后的小妹妹了。”
“去,谁让你捡了?不要脸。”
任鄂飞已经四年没有进行大运动了,背着陈衡霖到观日台,似乎很吃力,一直喘着气,有几次都想放下来,可一想到海游的话:反正还有半年,你就好好的恢复你的体力吧。
鄂飞硬是背着陈衡霖走上去。
也可以说是他已经在准备着和海游之战了。
正一步一步的做着恢复训练,体力是第一步。
他也是想赢得这场比赛的。
看着鄂飞的腰慢慢变得弯曲,有好几次要求停下来,可鄂飞就是不放,总是说:“也没几步了,乖乖的呆在上面,不要晃来晃去的。”
这一段路似乎走了很长一时间,终于到了,鄂飞轻轻的把陈衡霖放到观日台的石条上,擦了擦额上的汗,笑了笑,说:“还好你不算重,总算背过来了。”
同样,鄂飞也在感叹着,没想到四年时间把自己的体力都消耗光了,一点都不剩,要是换在以前,背着一个人,还可以健步如飞。
一幌四年,老本都没有了,背一个小女孩,走平坦的山路也走不了多远,以后的路还能走到哪呢?
感觉自己就像这落日一样,慢慢的在云海中消失了。
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