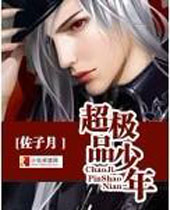笔尖少年-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说,老东西即便觉察了不对头,现在想明查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大学毕业后靳轲几乎全盘接手了撑在靳氏集团背后那些肮脏见不得光的势力,道上吃的很开,大有青出于蓝的势头。有时偶然开车路过自家于中心商务区内赫然高耸的大厦,只觉那阳光下纵横排列的变色玻璃明晃晃直闪得人眼晕。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坦荡磊落,其下暗潮汹涌又能几人有幸得见。
打着正规营生的幌子与黑道暗中勾结,这在集团内部高层中间已经不是秘密。想在世上立足、站稳了脚跟无人敢惹,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抛弃的东西很多,而且不能犹豫。比如说良心。再比如说,人性。
靳徽之幽冷的目光定定投去,手中闪着微光的餐刀将盘中珍馐轻易割裂。“……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他了?……那个不识好歹的杂种。”
闻言,坐在他对面妆容精致的女人几不可察的滞了滞动作,神情复杂。
“瞧您说的。已经被扫地出门的人,和我还有什么关系。何况,我们本就不是同姓。”
男人半信半疑的哼一声,眼神阴鹜。“那种只会给靳氏丢脸的东西,当初没把他的腿也打断就罢了,竟还敢为那命大的毛头小子和我玩失踪。出了这个家门他就别想再回来,是生是死都再和靳氏没半点干系。”
靳轲面上始终笑眯眯貌似恭敬的听着,却见自己父亲对面的女人眼圈已有点红了,仍旧未敢贸然出言。明明五官均与那个沉默清冷的少年如出一辙,眼底卑怯、妥协的悲伤又和那个人的坚毅执拗截然不同。
这刻在骨子里的、讽刺的基因。
下午两点准时抵达机场,靳轲在候机厅内毫不意外的接到了那簿名显示为“兰舒”的来电。
他翘着长腿接起,声音磁性轻快:“你好。”
“小轲……”那边的声音不但轻且带着极力抑制的哽咽,似乎不知该从何说起,酝酿许久才迟迟开口。“你其实已经找到小杉了……是不是?”
果然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女人这种生物啊。
“干嘛一个两个都这么怀疑?”他为难的蹙了蹙眉,笑意不减。“老头疑心病重就罢了,阿姨您可比他明理。这带着血缘的人都耐得住性子每天吃睡不误,我一个外姓人犯得上大动干戈么。”
女人闻言陷入难堪的沉默,过了能有半分钟才低微道:“对不起……”
靳轲仰头望望设计极具艺术感的天棚,神情淡淡。“……这话,您不该对我说。”
他觉得对话到此已经可以结束了。再没什么可讲。
“总之……”然而她又在那边顿了一顿,艰涩开口:“小杉他……就拜托你照顾了。”
“您到底了不了解情况啊。”毫不避讳的笑出声来,他脑海里又浮现冷杉几近毫无情绪、甚至可以说是流露着厌憎的那双黑眸,嘴角上扬。“您儿子根本恨不得亲手杀了我呢。”
女人根本不知道他在兀自愉悦些什么,迷茫的犹豫回应:“怎么会……你也知道小杉他还不懂事……”
“……你没资格说他。”被拂了逆鳞般骤然冷下语气,他下一秒便干脆利落撂了电话,连对方反应的机会都不给。
“真抱歉啊。”事后,他又很快露出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对着手机轻声慢语。“晚上还得陪弟弟过年,现在什么也别想影响我的心情。”
作者有话要说:
☆、番外四 昨日的他和他和他(二)
有多少人的一生,都在以朋友的名义爱着一个人。 ——题记
谢赭终于在火车彻夜的颠簸声中迷迷糊糊捱到了天色微明。
揉揉困倦的眼睛后撑着床沿无声坐起来,时间尚早,同厢的三人都还在安静酣睡。反正这一夜他是辗转难眠,并且因为频频更换睡姿现在浑身都透着酸疼。
凌晨五点三十八分,列车正在驶往海城的路上。今天,已经是除夕了。
前一日收拾行李时谢母还往公寓里打来电话,试图最后说服他换乘飞机回家。他没做考虑就拒绝了。谢赭记得很久以前刷人人时看到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要慢慢体味回归思念之处的过程。
拢着被子枯坐到六点多钟,列车员敲着厢门要换票,尚在沉睡的三个旅伴这才被声响惊醒,茫然蓬着头挣扎起来。
而在列车员离去很久以后,曦光才极不情愿地在沉郁的天际撕开一道口子,于窗外飞驰而掠的雪原上投下鎏金的、碎虹般的薄辉。
进站之前,他最后一次侧过脸试图捕捉到那直映入眼底的温暖。
而后,就是铺天盖地湮人的幽暗。
过年,其实真是一件挺无聊的事儿。这个感慨随着谢赭年龄的不断增长,而被屡次印证得愈发可信。
分居半年的父母见了他分外亲热,他便也陪他们一遍遍看春晚,唠着琐碎家常,去逛阔别已久的繁华商业街,然后穿着光鲜的新衣与他们四处走亲访友。却不知,这样究竟能不能填补他们心中,被自己搁置已久的空缺。
他何尝不愧疚,因那距离实为自己生生划出。若问这一切的始因,那就是个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几乎是老生常谈的旧事了。
他父亲和白宇泽的父亲多年前便是故交,各自成家后得知彼此的爱人都生了男孩,就二话不说地送到同一所幼儿园,再后来又是小学、中学。看着谢赭和白宇泽两小无猜的长大,子辈的友情又愈发加深了两家的联系。
变故突生在白宇泽性向的秘密被发现之后。
那时候,白宇泽和冷杉已经在一起接近两年了。初三的学业比起以往紧张了很多,但由于三人从不需要家中操心的稳定成绩,乐队的排练打着减压的旗号,硬是半分都没耽误,有时还拖到放学后很久。
有一天排练结束后天都黑透了,三人和往常一样结伴回家。谢赭是因为和白宇泽本就顺路,冷杉则明确表示“谁知道趁我不在某人会不会对他做这样那样的事”,坚持护送白宇泽到家。谢赭心说去你妈的,老子要干早出了娘胎就干了!然而心里憋火却无处可发,只得上下学都一脸苦大仇深,死闷着全程一声不吭。这天也和往常一样,白宇泽望着他强压怒火的背影走远满眼疑惑,冷杉就耸耸肩表示别在意那魂淡。
走到白宇泽家楼下的花坛边,两人照例在隐蔽处吻别。然后,这一幕就被临时加班归来的白母撞见了。
等白宇泽回到家里,死水般压抑的气氛让他心里有了不详的预感。三人在书房里彻夜的谈话,无外乎一个主题:立刻和冷杉撇清关系。这个懵懂的年龄,如果是单纯的早恋也就罢了,凭白宇泽知理懂分寸的个性,他们都不至于这么大加干涉。但是,那是个男生。自己儿子喜欢的人,竟然是个男生。
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他们和白宇泽为这件事情,一直僵持到中考。谢赭知道了事情缘由,却也只能干着急。毕竟是别人家的私事,外人就算关系再密切也无权干涉。然而让他们都始料未及的是,对方家长竟然比他们的反应还大,中考甫一结束就采取了过激行动。
而那种人,他们得罪不起。
在白宇泽出事之后,靳氏的人还犹不罢休的公然上门威胁,勒令他们带着重伤未愈的白宇泽尽快搬离海城。为首的那人,就是亲逼白宇泽跳楼的靳轲。作为“补偿”,除了医药费全包之外,精神损失费他们愿意出三百万。
打官司是绝没有可能赢的。靳氏集团的势力,在海城可称是一手遮天,就连谢赭的父母 都拿他们毫无办法。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
等白宇泽腿伤初愈,白父白母就带他连夜离开了海城,对方的钱一分也没拿。去向,只有谢家知道。而得到消息的当天,几乎没有犹豫,谢赭一脸平静的坐到父母面前,向他们坦然出柜了。
他说,对不起,爸,妈。我知道我很任性,也知道这么做很不负责任。可我必须去找小白。如果没有他,我会疯。
说完,他就转身回屋收拾东西。不管父母接受与否,他去意已决。
自始至终,谢父谢母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清晨谢赭出房门倒水喝,才看到主卧的灯光沉默亮了一夜。
谢赭觉得和白宇泽比起来,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对思想相对开明的父母,纵容他过分的任性,满足他离经叛道的执念。同意分隔两地,并非就心里舍得,可也没办法。谁叫他们摊上这么个儿子呢。
临行前夜,谢赭收到了销声匿迹近一个月的冷杉打来的电话。他并没有解释自己失踪的原因,只急切询问小白的近况。谢赭冷笑一声,“……他死了。”他说,听着那边亦蓦地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如果冷杉不出现在白宇泽的生命中,那他就不会受伤。就不会眼里再没有了自己。两人就不会被迫远隔千里的分离。最不可饶恕的是,在白宇泽最脆弱、最无助、被逼上梁山走投无路的时候,冷杉人在哪里?他人在哪里?!!……
“……你骗我。”良久,那边那个人的声音恐慌得简直不像他自己。谢赭猜,他必定是刚从家人那里得到了相同的答案。可他现在体会到的绝望,远不会抵得上白宇泽从楼顶跃下时的十分之一。谢赭肯定。
于是回答便愈发冰冷刺骨,直接下了最后通牒。
“以后别再和我有任何联系。我谢赭他妈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狠命掐断电话,他并不觉得自己哪里残忍,即便面对的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人。即便自己,其实也不过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人。
然而,他之后又是从何处得来的消息,一路追到异地他乡去的呢?……
谢赭站在曾经熟悉的校门口,默默望着前方那个先他一步于此久久驻足的纤细身影。
仿佛感受到他无声的注视,少女在下一秒便敏感回过头来,见到来人先是愣了一愣,随后微笑,脸上现出浅浅酒窝。“……你来了。”
……是了。就是这个人。谢赭尽管内心无力,面上仅无甚表情的微一颔首。
自己当时竟会傻到将白宇泽的去向告知这个女人。谁料她不但不替小白不平,反还和那混蛋站到同一战线上。
“虽然知道你过年肯定会回来,可也没敢贸然和你联系。谁想到竟这么巧。”陈曳齐肩的发已经长了些,乌黑如缎地垂落胸前。她又陪他安静站了一会,随后主动开口。“来都来了,一起进去走走吧。”
大年初二,再怎样也不好说出平时尖锐的言辞。谢赭迟疑片刻,也就默认了。两人绕到学校后身,依次手脚麻利的翻过围墙。
海城由于气候温和湿润,冬天鲜有积雪,今年又是暖冬,塑胶场地清洁干爽。
谢赭先是在篮球场上一动不动盯着篮筐站了一会儿,后又不发一言地向综合楼的方向走去。知道目的地是哪里,陈曳便不问他也不蓄意搭话。
廊内空空荡荡,除了两人自无其他。当初熟到闭眼都能摸到门的音乐教室,门牌上却清清楚楚印着“陶艺”二字。伸进兜里去掏别针的手忽然就停住了。
……为什么要进去。还有什么意义。
坚硬微凉的别针后来终于硌疼了手指,他低低笑了两声,就转身走开。
陈曳尚立在门口,侧脸看他站定在走廊尽头的窗前,逆光的背影透着那么点落寞。
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前,的确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无比的。晴时满树开花,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入夜的电台情歌,沿途的旖旎盛景,可尽化作一字一句,留人年复一年朗读。
可这世界有光就必有影。光明越是耀眼之处,绝望也就愈发浓重。或许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曾经的伤口会慢慢愈合,再激烈的爱恨都已潮退浪平。犹如自己在那日后才得知冷杉之前一直被靳氏软禁,随后又被扫地出门——最终,还是没能将那句气头上的赌咒贯彻到底。
去年暑假,他也曾独自一人回过学校。不过并没有摸到这里,仅仅去看了眼他们所待的最后一间教室。在白宇泽当年那张前排的书桌角落,他看见了一行刻字。
“这世界是你的遗嘱,我是你唯一的遗物。”
没有署名,但他知道出自谁人之手。黯然良久,他不发一言而去。
过去那些群魔乱舞、万愁不知的青葱岁月竟就这么过去了,除了曾镌刻在眼底心间的会心一笑,连予人缅怀的机会都不给。他还记得那时每到周末三人常结伴到教室自习,掐着时间做卷子,等头大的理科撸完了,白宇泽就逼他和冷杉把讲过的必背课文从头到尾过一遍。
“最是人间留不住,下一句。”
两人本就漫不经心,又被郁闷的诗词搞得心浮气躁,答案渐渐越来越离谱。
“天真十载等哥出。”
“节操、肥皂和破处。”
白宇泽脸立即黑的像锅底,炸着毛抄起牛津中阶冲头顶一人一下,哀嚎空谷传响。“是‘朱颜辞镜花辞树’啊魂淡!你们给我适可而止一点!!”
两人便只得态度良好的乖乖认错,然后把诗虔诚的从头背起。
而今物是人非,此时此地或许正上演着同样故事的主角,也已经不是我们了。
凝望着远处黑黝黝的群山上那一嫣霜白,谢赭独自笑过又旋即黯然。
一个时代的退却,不过也就像唱完一首歌。所幸的是,我们还曾嘶吼过。
“……走吧。”轻声带过一句,脚步声起,等陈曳回过神来,谢赭的身影已隐没在楼梯口。她不知道短短几分钟里他都回忆了些什么,正因自己不可能了解,所以一贯选择了安静闭嘴。但这次,她没有忍住。
快走两步屹立在距他半层的高度,她忽的开口:“不声不响陪了小白十多年,你究竟求的是什么?”
他就慢慢站住,回过头来,深棕的瞳底瞬间溢满夹杂在笑意和惆怅之间难名的索然。而在这种时刻,他脑中所想的,竟是件与问话近乎不相干的事情。
当年为了应试再怎么死记硬背,现今能深深刻在他脑子里的诗也只剩了一首。唯一的一首。它并非在大纲所圈的范围内,却只因触动,便是不忘。
我说,爱是包容,是攀击,
是拥抱,是荷尔蒙相撞,
是忍让,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