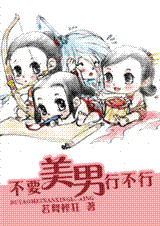不行-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进入首都之后他和那班记者分道扬镳,记者们也是惜命的,只待在治安相对稳定的都市,不肯再犯险去乡下。可是景海鸥要去的湖区乃是军方混战的战区,没人肯去,除了军队。可是军队又不会带着他去。
他耽搁在首都,在旅馆的时候每天听着外面零星的枪炮声,不时从东南西北某个角落升起一阵浓烟,街上的流民不时跑过,有的拿着冷兵器,有的挥舞着热兵器,水电煤气都断了,留下的人不知道怎么生活,连怀揣美金的景海鸥都觉得每天要吃上点什么很不容易,还要时时担心流弹。
他想起在湖区的时候交游的军官,如果能联系上他们,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有希望得多,可问题是这个国家军队编制复杂,景海鸥连哪部分和哪部分打起来都没有十分清楚,在乱世中要找到那几个只一起看过几场脱衣舞一起飚过车的军人谈何容易。
作者有话要说:好吧,不知道这个文如果出定制印刷的话会有多少人买。。。嗯。。。如果很少的话。。。嗯。。。
69
69、那以后的生活18 。。。
几经辗转,景海鸥联系上了当地华人商会,接触之后他才感觉到中国人伟大的生存能力和拓荒精神什么的。作为游客的时候,景海鸥觉得此地只算上山清水秀,然而差不多也到了山穷水尽万古洪荒的地步了,不是个发财的好地方,然而做了一半难民之后和自己同胞接上头才惊觉,这里竟不声不响地窝藏了这么多中国商人,卖啥的都有,看来真正核心的中国制造并不是鞋子衬衫集成电路板那种东西,而是活生生的中国人啊!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从鸦片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的时候起就源源不断地倾销向世界各国反倾销着自己的人口,直到今天……好吧,只要有自己人的地方就好办事,景海鸥总算找到点门道,他努力想找到那几个湖区军官的番号和联系方式。
在国内将派包机来接人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景海鸥也恰巧找到那几个军官的下落。
包机预定两天之后到达,商会副会长一个四十多岁富态的大姐亲自坐在雇来的军方坦克上挨个通知,景海鸥告诉她自己要去趟湖区把朋友一起带回来。
那大姐操劳过度嘶哑的嗓子,担心地说:“湖区那边很乱的,没我们的人,照顾不到,你还是不要去吧。”
景海鸥笑笑说:“两天后我一定会回来的,如果差了个十分八秒的,大姐你就跟机组人员说说稍微等我一会什么的。”他还有时间开玩笑。
大姐见他去意已决,就没多说什么,而是跟他说了几个在湖区的旧识朋友,如果他们还没逃离家园的话也许能帮得上忙。
景海鸥又通过商会的门路,自掏腰包租了军车上一个座位,跟着某部队往湖区去了。
进了湖区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也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原因很简单——这里的信号塔被炸坏了。
进了这一地区才发现情况虽然还不至于是最糟糕的那种,不过也不容乐观,之前发生过一定规模的交火,当地的住宅多是砖木建筑,不少受战火波及,被焚毁原本熙来攘往的集市一个人影都没有,那些印第安土著据说都躲进湖里的芦苇船上去了——几百年前他们就是这样躲过了印加帝国的种族灭绝。街道上只有现在占领这一地区的某部军官的装甲车招摇过市。
景海鸥站在彦清住的那间旅馆前面,彻底傻了眼,这里已经被烧了个底掉,一堆黑乎乎的残砖断瓦,不知道这废墟下面是否有他朋友的尸骨……他蹲下来不停地撸动着头发,这是什么情况,彦清他是死是活?
一辆装甲车在他身后开过,一分钟后又倒了回来,停下。
车门打开,一双军靴迈下车,“mi amigo ”有人向景海鸥大喊。
景海鸥回头,看见一个荷枪实弹的军官,他认得他,不过上次见面他可没这么威风,那时他们在一起喝酒往脱衣舞娘大腿里塞钱来着。
景海鸥的西班牙语非常有限,一些无伤大雅寻欢作乐的场合用倒还够,反正那时候就肢体语言也可以,和外国人日常沟通还是要靠英语的,那军官就问他:“你是回来找你的朋友?”
景海鸥说:“你知道我那个朋友在哪吗?他和我一样是中国人,大概这么高,长得不错……”
军官说:“我的朋友,我当然知道他,来这一区的中国人不多,所以你们很受注目的。”
景海鸥听他这么说突然有了点希望,大声说:“那么你知道他现在在那里?带我去见他好吗?求你!”
军官露齿一笑,“当然可以,上车跟我走吧。”
景海鸥只犹豫了一下就抬腿上了军车,那军官关上门之后对他说:“不过你要有点心理准备,你的朋友稍微有了点麻烦。”
BJ,虽然陈建林十分想搭乘包机一起前往战乱国,不过那样的话去的时候还好,回来的时候就要占用在地华人的座位,因此根本就不被允许。
那边的消息也很模糊,只说当地华人团体在积极奔走营救,可是名单却迟迟不公布。陈建林每天除了焦急等待外别无他法,只能和晋波一起谈心得体会什么的。
俩人一致觉得之前的别扭纠结折腾都太无聊了,活着,好好地活者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那两个回来了,不管以后能不能在一起都要好好对待他们。说到动情处,陈建林往往泪眼朦胧,晋波就安慰他,吉人自有天相,再说还有景海鸥在那边照应,那人最擅长的就是化险为夷。
彦蕴城和李老师也随后赶来,陈建林本来说他们年纪大了没必要过来这边,有什么事他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的。
李老师说:“那哪成,老头子说什么也要亲自来,”她压顶声音说,“反正也是国家给安排吃住,我也过来照顾他。”
陈建林不知道说啥好。
彦蕴城从行李里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卷轴,递给陈建林,“这个是昨天收到的,彦清出事前寄给你的。”
是了,陈建林想起来,彦清是说过要送他一幅画的。
他有点颤抖着一点点摊开那画布,金色的湖泊,璀璨得让人睁不开眼,然后在那背景里,一个人的背影坐在湖畔。”
陈建林看着,突然就泪流满面。
他认出那画上看风景的人是谁了,那个是自己啊。
他曾经说过也想五湖四海地看风景,彦清就把他画进风景,而彦清就看着这样的风景和风景里的自己,这幅画里画的是一个人,可是却是两个人的事。
可是现在的彦清到底在哪里呢?未来他们是否还能在一起看风景?
陈建林哭咧咧地拿着画去找晋波商量,他也不知道要商量什么,这种无助和恐慌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只有同在这里的晋波才更能理解。
晋波在听他絮叨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陈建林最后也注意到这点,“怎么了?”他停下来紧张地问,要知道晋波的消息要比他灵通,他上面有人,外面也有人。
晋波沉默了下,缓缓说,“海鸥在进入湖区后手机也联络不上了。”
“不是据说整个湖区的通信系统都暂时瘫痪了,不是人都遭遇不测。”
“那边商会的副会长说海鸥曾经用有线电话和她联系过,说已经找到彦清,不过……”
“找到了?!……不过怎样?!!”
“好像受了点伤。”
“受伤?伤到哪里?严重么?”
“这个还不清楚,我已经和那边负责组织营救的商会副会长联系上,请她多加照顾。不过事情到底怎样还要看运气了。”
“那……那他们能跟明天的飞机回来吗?”
“不知道。”
陈建林霍然站起来,“我看我还是要去把他接回来。”
晋波说:“你就算再着急也上不了飞机的。”
那边等待无比煎熬,这边营救争分夺秒。政府派的包机终于在已经差不多封闭的机场降落了,中国公民凭护照等身份证件就可以登机。
商会则早一步有组织有纪律地雇佣当地某军队把用军车把人护送至机场,一路上大家大气都不敢出,耳边还时常听到外面的枪弹声,就是寂静的时候也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战争像一只怪兽,不论贫富美丑国籍地吞吃人的性命。
离景海鸥当初说的四十八小时期限已经不远了,副会长派人守在电话旁,始终没有得到他的进一步联络。她一方面固然是受了关系方的拜托,然而心里也很佩服那个很讲义气的人,她焦急地看着表,最后一班发往机场的车在十分钟之后就要离开,否则的话就赶不上飞机。她衷心希望奇迹可以在这短短的十分钟内发生,景海鸥会突然带着他的朋友从飞驰而至的车上下来,大声宣称:我回来了!
十分钟后,望着扬起滚滚灰尘而去的装甲车,副会长的心沉了下去。
景海鸥和他的朋友生死未卜。
在被困人员家属被集中在一起听第一批被解救人员名单的时候,晋波和陈建林因为上面有人早已经拿到手那份名单,所以他们比谁都清楚地知道——那两个人并不在飞机上。
陈建林暴走了,泪奔了,指天指地要不顾一切去那里亲自寻找。
晋波也觉得头皮发凉,然而他还是比较能沉得住气的,安抚陈建林说:“你不要冲动,我去想想办法。”
于是在第二家包机起飞前,晋波动用了各方面的力量,终于在最后关头弄到了两张临时机票,且是以医疗队的名义。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据说第二批被解救的人员并不是很多,这架飞机在归航的时候不会满员。即使满员的话……他们只要有站票就好了。
掩人耳目地穿着白大褂的晋波和陈建林在一个角落里互相安慰着——主要还是晋波安慰陈建林。
陈建林说:“他受了什么伤,严不严重也不知道,即使小伤,在那里自然是没有药的……”越想越悲愤。
晋波安慰他:“既然人已经找到了就好,海鸥会想办法的。”
陈建林继续悲愤:“发炎了怎么办!”
晋波说:“也不定就没有药。”
陈建林哽咽地说:“并发症怎么办?”
晋波说:“要往好的方向想,不会那么糟的。”
陈建林男儿有泪说:“我真后悔以前没有好好珍惜他。”
晋波说:“以后再好好珍惜他也不迟。”
陈建林抹了把眼泪,“现在想想,我竟然没有跟他说过一句——我爱他。”
晋波说:“呃……没说过么?”
陈建林捶打舱壁,恨道:“我是个混蛋!”然后他泪崩了。
晋波有点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好背过身去,给朋友挡着点人。
70
70、那以后的生活19 。。。
景海鸥觉得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了,他被困在湖区警备军部的一间屋子里,两天前他在一个临时战地医院里找到了腿部中了流弹的彦清,然后被那个带他来此地的军官又带回此处。
景海鸥才知道那个军官叫保罗,是此地一个少校,他没有概念少校在这里到底有多大权力,不过既然他能有自由使用这样一间屋子的权力,看来还是很实惠的。
不过麻烦就出现在这个保罗身上,他把景海鸥他们带到这个屋子,然后就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既不让他们走,也不进一步害他们,就这么关着他们。
景海鸥当然想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何况他知道那家救命的飞机是不等人的,可是他向保罗提出此事,对方就以战事繁忙,抽不出人力护送他们安全离境为由拒绝,景海鸥就说不需要他派人护送他自己会想办法,保罗又说不放心他们的安全。
“我真遗憾你来的不是时候,外面在打仗,其实和平的时候这里不是这样的。”
“这里很美,我知道,可是你看保罗我要带我的朋友回去,他受了伤,这里没有药,只有阿司匹林是不够的!”
保罗耸耸肩,“我为你的朋友感到遗憾。”
“那就让我们离开!”景海鸥忍不住有点激动。
“嗨,我的朋友,你这是在干什么?我对你没有恶意,我只是希望你能多呆一阵,等这场事态平息,我们再一起出去喝一杯怎么样?”保罗拍拍他的肩。
景海鸥对于他不合时宜的好客和浪漫简直有点抓狂了,“如果你只是想和我睡觉的话,那么就直说吧。我的时间有限!”
保罗脸色大变,推开他,用西班牙语很激动地说着什么,最后用英语总结:“你伤害了我的骄傲!”然后气愤难平地走开了,锁上门。门外有两个士兵把守。
景海鸥就用汉语大声骂了一阵,垂头丧气地回到屋子里,那里彦清躺在床上,脸色苍白。
他现在的情况不太好,右大腿上有一块血肉模糊,只接受了简单的包扎处理。
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只差一点就要离开此地了,可是突然战事就展开了,他甚至来不及跑回旅馆,旅馆就着了火,他也中弹负伤,跟随慌乱避难的人跑到一处掩体,然后才发现自己身上什么都没带,行李都留在旅馆,手机也没了信号。
此地的原住民在惊魂稍定之后就有组织有计划地以家族为单位陆续撤到湖里生活,而彦清和少数几个外地人没有去处,徘徊在小镇的街头,此时他身无分文,连证明身份的证件都没有,生存还是毁灭才是当前的大问题。
不久之后他因为失血和饥饿昏倒在街头,被保罗发现带到军营临时医院,算是救回他一条命。
景海鸥颓丧地坐在床边,对彦清挤出一个微笑,无可奈何地说:“那个保罗脑袋有病吧,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白养着我们难道能打赢仗吗?”
彦清现在在发烧,腿伤引起的炎症正在侵蚀他的生命,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也努力弄出一个微笑来给朋友,“保罗救我的时候说,他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是为了你救的我。他还是喜欢你的。”
“问题就是这个喜欢是哪种喜欢啊?我就只和那孩子一起看过脱衣舞的交情!”
“我想,他可能就是因为不清楚是哪种喜欢,所以只想暂时把你留在身边想想吧。”
“好吧,他长得不赖,如果是我不忙的时候不介意给他开开荤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