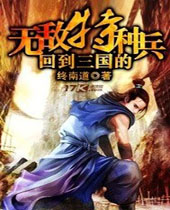回到起点-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杜月生不但没有感受到快感,相反,在这种持续不断仿佛没有止境的冲击中,他又难受得想吐……然而,受伤的胸腹还有那个可怜的胃被压在下面,他竟连呕吐的能力也失去了。
羞耻的泪水终于像开闸的龙头哗啦啦地流出来,杜月生发出闷闷的呜咽声,他希望能有人来救他。
在极端的痛苦中,他恍然想起了戴立——那个温柔体贴风趣幽默的爱人——可是他不在身边,台风阻挡了他的脚步,而在这本该欢庆的日子里,他却只能任由别人欺辱。
就在杜月生几乎失去神志,想要用昏迷来摆脱这份痛苦时,那扇木质的房门——又开了。
“月生,你睡了?感觉好点了吗?”
门口处,杜老爷子拄着手拐放轻了脚步声走进来。楼下的客人还在互相敬酒互攀交情,杜老爷子因不放心儿子,特地上来察看一番。
可当他适应了房间的黑暗,看清楚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后,杜老爷子像头发怒的狮子高举着拐杖冲过去。
“混帐!畜生!你放开他!”
黄景龙抱着杜月生往地上一滚,躲开这致命的一击。
紫红的孽根从温热的甬道里滑了出来,黄景龙抬头盯着老爷子轻蔑一笑,挟持着杜月生移动到床比较干净的那一边,旋即用力一顶,又冲入杜月生的体内,甚至当着老爷子的面不急不徐地律动起来。
杜月生在父亲冲进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呆傻了。他是如此的不堪,又是这样的无能,而这些丑态全被父亲看到——他身为男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
刚刚还在低低惨呼哀哀呜咽的杜月生,此刻已是心如死灰一般双目呆滞,无声无息。坐在黄景龙的怀里的他,好像变成一具失了灵魂的大号人形娃娃,随着对方的动作一上一下地晃动着。
“老爷子,我忘了件事——刚才还有件厚礼没有送出。”
黄景龙突然开腔,神态却好似在谈论天气般悠然。“杜家在上海、深圳、南京、重庆、北平、天津的几位合伙人,和晚生约定要给老爷子你一个惊喜——明日,他们会将资本加到黄某经营的公司里去,而杜家的资产,他们也不再留恋。”
“你说……什么?!”
杜老爷子冲过来的脚步一个趔趄,他赶紧撑住手拐,对黄景龙的话半信半疑。
“黄毛小子也敢说大话!你把月生给我放了!”
黄景龙凑到杜月生的颈项边细细啄吻,嗤笑道:“月生最爱我如此对他,老爷子何苦棒打鸳鸯。至于晚生是否胡说……楼下的那些个宾客,有多少是真心来祝寿,又有多少是等着看好戏呢?”
“你……你想干什么!?”
黄景龙似真似假地问:“如果让他们看到这种情形,杜家是不是真的会名誉扫地呢?”
杜老爷子愤怒到额头青筋尽暴,太阳穴剧烈地跳动着。他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强自缓和下口吻。
“你既喜欢月生,又怎忍他当众受辱。你……你不会那样做。”
“我也不想,只要老爷子别逼人太甚。”
好一个本末倒置!杜老爷子却只能深深咽下这口气,连声道:“好、好!我不逼你……你先把人放开!”
黄景龙狠狠向上抽动数下,然后半眯着眼无奈道:“可惜还不行。”
随着他的这句话,只见杜月生无精打采的分身下面的部位、那里的皮肤忽然一鼓一鼓地蠕动起来,片刻后杜月生原本平坦的小腹也微微鼓胀起来——黄景龙竟当着杜老爷子的面,把精液射到杜月生的体内,一滴不剩。
在这不长也不短的过程中,杜月生仰了头,发出比临刑前的犯人们更可怖的惨呼——那是一种仿佛从地狱爬上来的厉鬼的声音,嘶哑难听,令人胆寒。
黄景龙这才放开人,抓过床上的被子盖住杜月生的身体,然后才站起来整顿自己的衣裳。而失了支柱的杜月生像个破败的娃娃倒在床里,被单只盖住了他的上半身,下身处光洁修长的双腿大张,原本肉色的穴口在经过一番蹂躏后,红肿微张,一些媚肉被拖出来,被泊泊流出的浊液洗刷过后,显得更加淫靡。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此刻黄景龙早已是一滩烂泥。
可惜他不但完好无损,还能谈笑风生。“老爷子,请期待明日的惊喜。”
杜老爷子纵横江湖数十年,头一次感到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潇洒来去。
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迟缓地走到床边,看着床上失神的小儿子,不禁流下两行老泪。
丢开拐杖,杜老爷子坐在床边,把杜月生的头抱进自己怀里。杜月生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眼中既失了昔日的光彩,也没有半点聚焦。
“月生,没事了……没事了。有爸爸在,没人敢再欺负你。”
苍老的声音,与在寿筵上时判若两人。
英雄迟暮,鬓染霜。
一夜之间,杜老爷子那头花白的发全部转白。
第二十八章
杜老爷子下楼去送走所有的宾客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杜月生已被转移到那里,原来的房间不能再待——在杜月生身边守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噩耗传来。黄景龙并未夸大其词,几乎涉及到杜家所有合作项目的各地区分公司的合伙人,全部撤资出去,纷纷投入到黄景龙名下的各个分公司中——黄景龙许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丰厚利润——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
于是,杜家的流转及储备资金几乎一下子被淘空殆尽,空余下庞大的残躯。
杜老爷子病倒了。
杜其琛怎么也想不到,当他满怀欣喜赶回来时,迎接他的会是这样一种局面——父亲病重垂危,被送进医院;弟弟精神异常,在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除此以外,杜家的生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杜其琛是个冷静的人,并未因此也跟着一块儿垮掉。他打起精神,一方面先请同行的戴立——在这几个月中,戴立凭借他的交际手腕,成功获得杜其琛的信任——清点杜家所有财物的情况明细,然后再谋对策和出路。另一方面,他每天在医院照料父亲,陪伴弟弟。
杜老爷子这次是突发脑血病,躺在床上整日昏昏沉沉地睡着,对外界的感应很是迟钝。于是杜其琛大多时间都是陪伴着杜月生。
杜月生的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他在当时突然受到强烈的刺激,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下意识地关闭了所有的感知,抽空自己的灵魂。
这本来就是暂时性的,只要细心照顾,不多时便可恢复。可是杜家的佣人们在杜老爷子也病倒后,因为怕麻烦,所以一并把这爷俩都送进了医院。
这几天经过杜其琛的呵护照料下,在九月初的某个夜晚,杜其琛惊喜地发现,原来那个灵动的弟弟回来了。
“月生,你没事了……这就好!这就好!”
兄弟俩抱头痛哭——杜其琛是喜极而泣,杜月生是劫后余生——两人都没体会过这种苦楚。
杜月生在得知父亲的病情后,黯然自责不已。
“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爸爸!”
“不,这全是黄景龙干的好事!”杜其琛并不知晓那晚发生的事情,他认为是那场灾难性的变故害得父亲病倒。
所以,杜其琛的眼中燃烧着浓浓的恨意,以及战斗的欲望。
“我们不能这样被击垮,月生。等爸醒来,我们再一起对付那个白眼狼!”
上天似乎听到了杜其琛的祈祷,在杜月生恢复神智的一个多月后,昏迷多时的杜老爷子竟也慢慢睁开了眼,还能口齿清晰地和俩兄弟说话。
杜家兄弟守在父亲的病床边,不约而同地泪光闪闪。
谁想老爷子的第一句话却是……
“这道坎,我怕是撑不过去了。”
“不会的!爸,你一定会好起来!”
杜老爷子缓慢地摇了摇头:“活这些岁数我也够了。接下来的杜家要靠你们……‘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你们一定要撑下去!”
杜老爷子闭了闭眼,歇息一下后继续说道:“书房里有本手札,是我毕生经商的阅历总括。”
杜家兄弟越听越不对劲,老爷子这是在说遗言哪!然而即便如此,两兄弟也不敢违逆父亲的话,含泪点头。
杜老爷子又停了会儿,看了眼杜其琛,又转向最让他放不下心的小儿子。
“和戴立间的合作只能是短期的。还有,他不是能天长地久的人。”
杜其琛听懂了前半句,对后半句却茫然不解。杜月生却听明白父亲话里的意思,他心里一酸,眼泪扑哧扑哧掉了下来。
杜老爷子见了,也只是暗自嗟呀。
原来杜月生出世没多久,杜老夫人就撒手人寰,留下嗷嗷待哺的幼子。当时杜老爷子忙于生意,没空去管。杜其琛那年也不过是个不满九岁的小孩,即使尽心尽力了,杜月生仍是有一口没一口的维持个半饱不饿。
直到他能呀呀说话满地乱爬时,杜老爷子才恍然醒悟地找了个老妈子带他。可是,那个时候的杜其琛被送到英国读书去了,杜月生只能在孤孤单单、没有亲人的陪伴下逐渐长大——唯一的玩伴只有比他大不了多少,又非常臭屁的阿黄(小杜语)。
这使得杜月生一生都在渴求爱的关怀。他会喜欢上戴立,也是因为对方的温柔体贴,让他感受到亲人之外的温情。
杜老爷子看穿了这一点,除却把杜月生留在自己身边,别无他法。他只能尽量劝说,能让杜月生回心转意最好。若果真不行,那也是儿孙自己的命。
戴着大口罩的值班医生过来例行检查,确认过数据后离开病房,似乎对杜老爷子的清醒并不如何在意。
这时杜老爷子说道:“我累了,想睡会儿。”
杜其琛轻声道:“爸,你睡吧。我和月生守在旁边,有事叫我们。”
杜老爷子疲惫地闭上眼,睡了过去。
这一睡,再也没能醒来。
第二十九章
杜家两兄弟在内外交困下,熬过了老爷子的头七。那时已是十月份的中下旬,天气逐渐变冷。
另一边,戴立花了两天左右的时间,把杜家的账目算得一清二楚。杜其琛为了老爷子的事,心力交瘁,尚无心思打理,便暂时交由戴立代为管理。
而杜月生因了这场巨大的变故,对有些事情能够看开了。以前的他对爱情执著顽固,对生活憧憬抱有幻想,然而现实的残酷打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人情世故,悲欢苦乐,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过于天真无知,让敌人有机可乘,间接害死最亲的人。而他,正是赤裸裸的帮凶!杜月生所受的煎熬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杜其琛更甚,且无从宣泄。
他虽然仍喜欢着戴立,却再也不复以往的那种热烈——更像激情退去后残留的淡淡余温,不烫,尚能暖人心。
但是,黄景龙俨然成了横在他俩之间很难逾越的一道深沟。
那个晚上,黄景龙留给杜月生的,不仅是肉体上的侵犯,更多的是刻在心房上的烙印,时刻折磨得杜月生不能入睡——也导致他至今无法坦率面对戴立。
因此他对戴立采取能躲则躲,能不见面就不见面的消极的处理方式。
所幸这些日子,老爷子的丧事占去他们太多的精力,而戴立也要忙前忙后,根本无暇顾及杜月生多变的心情。
杜其琛给远在英国的娇妻寄去消息。两个星期后收到一张薄薄的明信片,上面表达了对公公的哀思和遗憾,最后是不能赶来参加葬礼的原由:爱子体弱,经不起长途奔波,对老爷子的逝世深表哀悼。
杜其琛看完后,一言不发地把明信片撕成碎片,扔进火炉中。杜月生在一旁静静看着,等到碎片在火炉中快要燃烧殆尽时,他走到杜其琛身边,跪坐在沙发前很是依恋的把脸埋入他哥的双腿间。
“哥,杜家只剩下我们了。”
带了点冰凉的修长手指抚上杜月生的脸庞,杜其琛弯下腰和弟弟脸贴着脸,闭了眼不吭声。
兄弟俩保持着这个仿若雏鸟互相取暖的姿势,直到初冬的暮色降临,四周变得一片漆黑。
出殡下葬的时间定在冬至那天。
前来参加葬礼的人格外少,这虽在杜家兄弟的意料之中,但仍不免感叹世情的凉薄,人心不古。
在他们的感慨中,黄景龙来了。只是还未来得及上柱香,就被杜家兄弟联手赶了出去。
打跑了黄景龙,之后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其中有不少是背叛杜家的合伙人,杜家兄弟有心如法炮制,但一来对方人多势众,闹起来恐怕场面会很难看;二来这些人的诚意祭奠,总归是把场面撑了起来,不至于让杜老爷子走得冷冷清清。
葬礼结束后,杜家兄弟疲惫地回到家中,准备着手整理杜老爷子的遗物,同时杜其琛拿来戴立整理完的账目进行比对确认,这一看,生生把杜其琛惊出一身冷汗。
“这是怎么回事!?”
杜其琛抓着账本,怒气冲冲地对着戴立大吼大叫。
戴立自从杜家遭逢变故后,便住了进来,而杜家兄弟也默认了这一点——少了一个人的杜家,显得格外的清冷,这让他们心照不宣地接受戴立搬进来住的做法。
杜其琛信任戴立,所以当他发现戴立背着他们,把杜家名下所剩无几的份额收购到他自己名下时,那种愤怒是深刻的,不可名状。
戴立自有他的一番说辞:“杜家已经沦落为人人可欺的羔羊,被人收购是迟早的事。肥水不流外人田,戴某为杜老爷子的事可算是仁至义尽,收取这些小利对你我都是好事,大少爷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
“你不该擅自转移杜家的资产,你没有这个权力!”
“吃下去的肉,吐不出来的。我不是圣人,既然付出就一定要有相应的回报。当初杜老爷子许我在上海滩上的资助,戴某只不过兑现罢了。”
“你、你给我滚出去!不准再踏进杜家大门一步!”
杜其琛不想再和他多言。他没有记住杜老爷子的话,错信对方。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只能和对方打官司,争取早日把杜家的资产要回来。
杜月生在外奔波,托生意圈内的几个熟人帮忙,但是一无所获。回来后又听说了这件事,他几乎要生出心灰意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