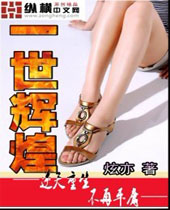一世牵by夜笼纱-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些不屑的,厌恶的,憎恨的,甚至是□的嘴脸,尖酸刻薄的话语,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来回转动。
云修儒用被子,将自己蒙起来,人渐渐缩作一团,被子微微颤动,里面隐约传来,若断若续的哭泣声。那样的压抑,那样的凄凉无助。
不知哭了多久,想是累了,昏昏沉沉的睡去。
柳春来牵了云娃,李放,药童紧跟其后。四个人做贼似的,蹑手蹑脚的推门进来。
当掀开被子,见云修儒一动不动的趴在那儿。柳春来以为是睡着了,上前连叫数声不应。李放一把推开他,伸手将云修儒翻过来一看,见他双眼微肿。泪痕犹在,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连嘴唇都成了灰白色。
云娃尚小,不明白父亲怎么了。柳春来毕竟要大几岁,见他这般观景,忍不住抱了他的腿,大放悲声。云娃见他哭得这般,也跟着哭起来。
李放喝道:“你们是想他死吗?快去倒杯水来。”说罢,将云修儒扶起,靠在自己怀里坐好,又命药童将他的双腿盘起。一个揉搓前胸,一个捶打后背,又在人中上掐了好一会儿。只听云修儒微弱的哼了一声,这口气总算是缓过来了。
高智远奉了骆缇之命,前来探望。在外头听得动静不对,三步并作两步的闯进来。
李放原不认得他,此时也顾不上问他。一面与云修儒喂水,一面轻声唤道:“公公可好些了?”云修儒微睁开双眼,眼珠儿动了动,半天方认出是谁。不由皱眉道:“不是叫你别去叫吗,你……”李放扶他缓缓躺下道?“公公可别错怪他,是骆掌印传我来的。”
云修儒一眼看见高智远,正要问他,云娃便一头扑过来哭道:“爹爹,我怕了。”云修儒摸着她的发道:“青天白日的,怕的什么呀?”又对柳春来嗔道:“你这孩子,见来了客,怎的不把我叫醒了?”众人一听,都面面相觑。
李放小心的道:“公公方才闭住了气,昏死过去了。若非我来得快,怕是要出大事了。公公竟不知吗?”云修儒呆了呆道:“我委实不知。难怪觉得胸口,憋闷的难受。”高智远瞪了柳春来一眼道:“小柳儿,你是怎么当差的。亏得骆爷还夸你,赏你了。”云修儒道:“是我让他带云娃出去玩儿的,高公公莫要错怪了他。”高智远赔笑道:“是,知道云爷疼他。”又拍了柳春来的肩道:“以后要小心当差,别让爷白疼了你。”柳春来抽抽噎噎的答应着。
药童放好引枕,将那雪白的手放上去。李放伸指一搭,凝神静气的诊起脉来。
约一盏茶的功夫,药童收了引枕,李放提笔斟酌再三,拟好了方子递与他道:“你先回去,抓好了药,让他们务必赶着送过来。”药童领命而去。
李放对云修儒道:“公公这病本无甚大碍。若不知保养,只怕会酿出大祸。”又对柳春来道:“柳哥儿,日后若见你家公公不舒服,便立时来回我。他知你为他好,必不会真骂你的。我隔三差五的,定会不请自来的。”柳春来用衣袖擦了把眼泪,竟象得了圣旨的一般,趾气高扬的对云修儒道:“爷可是听见了,这可是李太医说的。”高智远在后面敲了他的头道:“可是蹬鼻子上脸了!都是云爷自己惯的。”
李放交代了些日常饮食之事,便告辞出去。高智远借口相送,也跟了出去。
到得外面,高智远拦住李放道:“李太医且慢走。”李放回身拱手道:“高公公有何指教?”高智远笑道:“不敢不敢。只是我们骆爷想问问,云掌印这病,终究是个什么症后?”
李太医看了他两眼,见四周无人,低声道:“若论这病,原也不值一提。吃几剂药,好生调养数日便好了。可偏偏是云掌印得这病,这便难了。”高智远不解道:“却是何故?”李放道:“他少年之时,受过内伤,又不曾治好。身子原比人弱些。加上前些时……”说着,朝四周望了望,再压低声音道:“那‘醉妖娆’虽只是助兴的春药,实乃虎狼之药。虽不曾久服,但剂量太重。云掌印肠胃本就弱些,这药一下去,无疑是火上浇油,他如何受得了?”
歇一歇道:“云掌印心结颇多,又无处排解。我前些时还对陛下言道,云掌印人年轻,还扛得住。现在看来,他以快支持不住了。他心中若不是念着孩子。怕是早就……请高公公回去,将我这一番话,禀明骆掌印。他是陛下跟前儿的红人儿,原比你我能说上话。天已不早,我告辞了。”高智远与他拱手而别。
回到房中,见云修儒斜靠在软榻之上,头发松松的绾着,上面插了支柳叶簪。脸色依旧苍白,衬着微微红肿的双眼,好不凄婉动人。
高智远忽然觉得,他美的太不真实。仿佛是晶莹剔透的雪花儿,随时便可化去。又像山间的轻雾,待你看清时,他却已经散得无影无踪了。
柳春来上前,拉了拉他的衣袖。高智远自知失礼,尴尬的笑了笑道:“云爷若无事吩咐,那小的就告辞了。”
云修儒示意他坐下,缓缓开口道:“你告诉我,灼阳宫怎么走?”高智远奇道:“云爷到那里做什么?”云修儒便将弄脏廉松风衣服之事,说与他听。
高智远笑道:“廉首领可不是这等小气之人。我劝云爷还是不去了吧?”云修儒摇头道:“今日他从小路而出,必是有要紧之事。我把他的衣服弄脏了,他回去换时,岂不耽搁了正事?上面若怪罪下来,他定要受罚,岂不是我连累了他?我是一定要去的。”
高智远暗道:“我若不说,他必到处询问,这样反而不美。”想到此,便将去灼阳宫的路径细细相告。
云修儒又问道:“我听说,廉首领在宫中大大的有名啦,不知高公公,可知详情吗?”高智远道:“小的跟他不熟。听宫里人讲,当年三国会战狮虎岭,廉首领还不到二十岁。罗丹第一勇士只一招,便被他砍与马下。大小战役近百场,哪一场不是廉首领冲锋在前。就连宝麟亲王,也对他另眼相待了。”
廉松风,云修儒见过两次,据都是近在咫尺。高智远虽然只两三句,言语未免有些夸大。分明已看见一员小将,手握善胜刀,顶盔罩甲,骑着高大的战马,英姿飒爽的领着众士卒,以破竹之势,杀向敌军。耳畔战鼓声催,喊声震天。
高智远见云修儒,不言不语的靠在哪儿,像是定住了。连叫数声不应,只得打着胆子,上前拍了他一下。云修儒一惊,醒悟过来。神情有些不自然的道:“我有些乏了。”高智远道:“云爷多多保重,小的告退了。”说罢,起身退出去。柳春来直送到大门外方回转。
高智远回到司礼监,骆缇的住所。约等了有一柱香的工夫儿,才见骆缇回转。
高智远上前请了安,接了小内侍送来的茶,双手奉与他。骆缇满腹心事的坐在那儿,一言不发。高智远不敢打搅,静静的立在一旁。
好一会子,骆缇才对他道:“云掌印怎么样了?”高智远便将今日之事,以及李放的话细细回明。骆缇听后,摇头叹道:“我很知道,他是病由心生。陛下在他面前,有些喜怒无常的。如今,连我也琢磨不透,陛下对他,终究是个什么意思?偏偏,这二位的脾气都够倔的。哎,真是冤孽呀。”
又压低声气道:“今日,陛下同宝麟亲王,在御书房大打出手,你可知所为何来?”高智远吃惊非小,颤声道:“小的……不,不知。”骆缇便将早朝之事一说。接着道:“王爷对云掌印起了怜惜之心,要陛下将他送与自己。”
高智远皱眉道:“爷,这可不是好兆头啊。皇家最忌手足相残,这……”骆缇道:“我难道不知吗?看来,是得去向王爷请安了。”见高智远一脸的担忧,拍了他的肩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二人正在说话,忽听有叩门之声。高智远喝了声“进来”。门一开,二人看时,却是常在骆缇身边儿伺候,唤作金生的小内侍。
骆缇呷了口茶道:“何事?”金生关好门,低声道:“回爷的话。方才小的出去送东西,听那些人讲……”说到此,微微的有些脸红。骆缇斜了他一眼,自顾吃茶不理他。高智远道:“你进来便是要说此事的,又何必吞吐吐?”金生道:“他们说,有人看见云掌印,在给女儿喂……”骆缇放下茶碗,两眼紧盯着他,拖长了声音道:“喂什么呀?”高智远也在一旁催道:“小兔崽子,还不快说!”金生道:“在喂奶。”
骆缇惊的猛地一起身,衣袖带倒了桌上的茶碗。他一把抓住金生的胳膊,沉声道:“你方才说,云掌印在给女儿喂奶?”金生瞪着骆缇近在咫尺的脸,又是怕又是疼,战战兢兢的道:“回,爷的话,是。云掌印,在,在给女儿喂奶。”骆,高二人相视一眼。
高智远道:“你在哪里听见的?”金生道:“在流萤宫附近,还有,还有尚膳监。”高智远又道:“你可认得他们?”金生摇摇头。骆缇松开手,摸摸他的头道:“好孩子,这话不许跟他们,到外头去乱传。你细细与我打听清楚了,究竟是谁造谣生事?”金生惊魂未定的点着头,倒退着出去了。
高智远道:“此人不是孙树,便是记娘娘的人。”骆缇在房中踱步道:“也不是空穴来风吧。”高智远“啊”了一声道:“此话怎讲?”骆缇便将云娃的那个“怪异举动”说与他听。
二人在房中思付半响,均摇了摇头。
骆缇道:“他若是阴阳之身,在净身之时便已知晓。再有,瞒谁,也瞒不了陛下吧。”高智远敲了敲额头道:“这便奇了。”
骆缇坐下道:“犯不着怎么费劲的瞎猜。不多时,便会传到陛下耳中,谜底自然会揭晓。”说罢,低头看了一眼打翻的茶碗。高智远忙叫了人收拾下去,重新奉上新茶。
骆缇吃了一口道:“我听宫中老人讲,这阴阳人,乃是长了男女两副东西。□只得七八岁幼童般大小,再不发育。下面却是妇人的物件儿。他们每半年行一次经。干净之后,便可同房。运气好的,一招便中。运气不好的,只得等下半年了。”高智远听的瞠目结舌,喃喃道:“世间果有此等样人吗?”骆缇笑一笑道:“我如何知道,只听说罢了。”
高智远道:“这等说来,他们也如妇人一般,能哺乳喽?”骆缇似乎在回想,那个老内侍的话。过了会儿才道:“此等人皆容貌秀美,颇有女子之态。双乳只馒首大小,产子之后,据能哺乳。听说,他们每胎可生两个。一生之中,只生产一次。民间若有此等人,必会献于天子。还传说,与他们生的孩子,阳气最足,将来必是人中龙风。”
高智远迟疑的道:“爷,云掌印果真是阴阳同体吗?”骆缇怔了一下道:“他若真是,便是死期到了。”
20
20、第 20 章 。。。
云修儒在家里养了三四日,方渐渐好转。期间,中兴帝虽未过来探望,却命人将赏赐的金银,衣服,茶叶,吃食,笔墨,器皿,名贵药材等物,一一送过去。他知道无法推却,只得谢恩收下。心中冷笑道:“这便是我的卖身钱吗?不曾想,我云修儒还能卖出,这等的好价钱。”
柳春来见他不喜反悲,多少明白他的心事。一面向云娃使着眼色,叫她悄悄儿的,一面手脚麻利的,将东西收拾下去。
波利使团不知何故,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于今日未时一刻,抵达京城。中兴帝定于晚间,在月华殿设国宴款待。
一清早,云修儒连哄带骗的,将女的小嘴儿,打自己的胸口上挪开。起身梳洗,用过早饭,嘱咐两个小孩儿几句,便往灼阳宫去了。
今日天气格外的晴朗,树枝上结的冰棱,在阳光下发出七彩之光。
云修儒缓缓而行,约走了近半个时辰,方看见灼阳宫的大门。
上前举手正要叩门,不想,门却自己开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圆脸少年,打里面走快步走出来。两人均为提防,正好撞了个满怀。若不是少年眼疾手快的,将云修儒一把抓住。他定会摔倒。
望着这个比自己稍矮些的少年,云修儒唇边绽出一抹微笑。犹如冬日暖阳,让人流连不已。
汲庆祥就怎么抓着他的手,痴痴的立在那儿,仿佛已经沉溺其中。直到耳边响起温婉柔和之声,方才醒悟过来。
云修儒见他满面羞愧,期期艾艾的不能言语,笑道:“上次匆忙,不曾问得小哥儿名讳,敢问如何称呼?”汲庆祥躬身道:“实不敢当,小的贱名叫做汲庆祥。”云修儒点头笑道:“真乃好名好姓也。”
汲庆祥渐渐缓和过来,拱手问道:“不知云掌印到此有何公干?”云修儒道:“哪里有什么公干,今日是特来拜谢廉首领的。不知在否?”汲庆祥面有难色的道:“实在不巧,我们爷出去了,临走之时,不曾说几时回来。”
云修儒一听,好不沮丧,只得道:“烦你与廉首领说一声,我来过了,他既然公务繁忙,我改日再来拜会吧。”汲庆祥道:“是为了那日之事吧?那事原不值一提的,云掌印也太多礼了,这般辛苦跑来,我们爷如何当得起?”云修儒道:“那日可有耽搁廉首领的正事?”汲庆祥笑着摇摇头。云修儒道了声“告辞”,转身离去了。
没走多久,忽听得身后一人叫道:“汲哥儿,汲哥儿。哎呀,昨晚吃醉了,廉爷等着骂我了吧?哎,你掐我做什么?”
云修儒身子一僵,慢慢转过来,望见汲庆祥同一个内侍在一起。见自己回头,神色尴尬至极。又狠剜了那内侍几眼,到把他弄得莫名其妙起来。
以为他要走过来,高声喝骂自己,然后拉自己到爷跟前去评理。以为他会满面怒容,拂袖而去。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