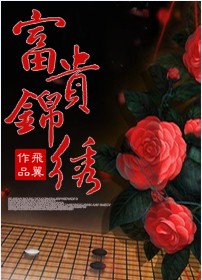一流富贵门户作者:木三观-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牧菁道:“这蓝仪也甘心。”
“他如何不甘心?”凤艳凰说道,“他一心振兴门阀。只是这样的时世,要振兴家声,难道就是安闲度日得了的?或是参军,或是从政,并无别的路可走。这从军一路,已被我们这些成名的武夫们堵死了,唯有趁这新君登基、老乐正要用人之际去从政了。”
牧菁道:“哼,乐海可不比将军。蓝仪这么心气高的,却跟了他,血都不够他吐的。”
凤艳凰笑道:“难道蓝仪竟不知道?他也是求仁得仁。”
正说着,却听见有人敲门。牧菁扬声问道:“谁呢?”
“牧菁姐姐,是我……景重。”
牧菁笑道:“进来吧。”
景重推门而入,手握一张纸,便道:“这是乱皇打来的电报。”
凤艳凰忙拿了来,展开一看,一跌足,便道:“坏了!”
景重忙问:“怎么了?”
牧菁将纸条拿过来一看,便道:“乱皇怕将军为难,自己动身去了京师,又说明并不会当京官,只要有一条命都会回来长乐的。这……这也没什么的呀。”
凤艳凰却咬牙道:“你还不知道老乐?老乐会杀了他的!”
牧菁也愣了。景重倒很清楚,便道:“那我马上打电话问问,看他已去了哪儿。”凤艳凰点头便道:“更让人去打电话通知金玉隐。我们在京城附近也有人,设法拦着他,不准他进京。”
景重急忙去了,半天回来,又道:“已查问过了,他只去了半日,还没到京师呢。金将军也已马上行动了,说已安排了一位名叫牛二的去拦了。”
那牛二本是附近的一个官吏,与金玉隐相厚,闻言便在附近设了关卡,见乱皇的车来了,连忙命人将乱皇及其随行者一并带进了府衙。乱皇不知其意,便道:“这位官爷,我们奉旨进京的……张三!”张三便递了文件来给牛二看。牛二便笑将原委与乱皇说明了一遍,乱皇闻言甚为讶异,半晌也无主意,便且留宿一晚。竟不防,那张三原已被买通,牛二的手下也有被买通了的。牛二和乱皇双双被毒杀。牛二便带了二人的人头去见乐海。
蓝仪还是头一回见着死人,却见乱皇和牛二的人头七窍流血,面容乌青,竟散发着浓烈的腥味和恶臭,蓝仪再稳重,亦敢恶心,不觉以袖掩面。乐海瞅了蓝仪一眼,又看向张三,只说:“这就是乱皇?”
张三忙道:“是的,大将军,这就是乱皇,如假包换。”
乐海沉默了半晌,揉了揉鼻子,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啊呀,我的乱皇啊!你这样的豪杰,怎么就被小人所杀了!”正哭着,吓了张三一跳。蓝仪会意,忙整了整衣冠,站了起身,厉声说道:“大胆张三!竟敢谋害忠良、刺杀朝廷命官?来人,快将这没王法的畜生拿下!”
张三吓得魂不附体,正要大呼冤枉,就被几个侍卫打了几拳,拖了下去了。
乐海又继续哭道:“太没王法了!重罚!必须得重罚!中书令大人,您说是吧?”
蓝仪强忍着恶心,只道:“是的,将军说得很是。”
堂下一众臣子也伏地称是。乐海哭道:“唉,我太伤心了,今儿个就聊到这儿吧。你们都退下……呃,中书令大人可否留步?”
乐海又走到堂下,提起了乱皇的人头,走到了蓝仪跟前。蓝仪脸色煞白,却亦不敢动弹,只垂头站着,然而,即使他不去看,那恶臭还是直窜进鼻子,恶心到肚子里了。乐海抹了抹眼泪,说:“你看,这可是当世豪杰啊!”蓝仪点头道:“是的。是一个死了的当世豪杰。”
乐海笑了,便抛开了那个人头,说:“是的,死了的。蓝卿,你何必嫌弃?如果你死了,也不比他好看多少!”
蓝仪怨恨自己永远不能习惯乐海的恫吓,而乐海亦仿佛以恫吓他为乐。蓝仪强忍恶心答道:“是的,将军说得很对。在下会尽力活着的。”
乐海笑道:“是的,你死了的话,就很可惜了。”见蓝仪不语,乐海又说:“乱皇不是巴望着回去吗?我怎能不如他的愿望?来,快叫人把乱皇的人头装回去,赶紧的送回长乐,给老凤。”
蓝仪只能说,乐海这次肯定能狠狠地恶心着凤艳凰了。
这件事对于凤艳凰来说,与其是“恶心”,更多的是“痛心”、“伤心”。他从未将乱皇当做山贼、乱党看待,他亲自地去见他,不畏惧危险。他尊重乱皇,乱皇也尊重他。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引为知己——酒逢知己千杯少,他那天和乱皇吃了十坛的女儿红。今天,凤艳凰独饮了三坛便醉,眼圈都红了。是酒,他想,是酒烫红了他的眼眶。
景重也没有睡,也没有回家,只在内书房写公文。牧菁推门出来,轻轻的“啊”了一声,道:“怎么没回去?”景重笑道:“我原有几分公文未写,便留着了……是了,将军可睡下了?”牧菁又是笑又是叹的,只说:“你什么公文要写这么久?只等着看将军什么时候睡下罢!”
景重有些不好意思,只垂头道:“那将军可睡下了?”
牧菁便道:“睡是睡了,不过是醉了睡的。刚伺候过他躺下,好费力气。”
景重心里忐忑,半晌才说:“我能看他么?”
牧菁笑道:“没什么不能的。只是他有什么稀罕值得你去看。”
景重放下了笔,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掀起了帘子,便是一阵暖香。原是苏工和田玉雕的小香炉里烧着甜梦香。景重慢慢想起了在乱山郊外的那一天……他一直想起那一天,那一天,他一直喜爱的大哥哥比以往更温柔。凤艳凰对他的好总是细致得出不了一点错。那样的好,叫景重十分窝心。因此,景重也想知道,怎样能让凤艳凰也感到那样的“窝心”?
景重掀起了纱帐,以铜钩勾住,便见凤艳凰闭目躺着,双颊酡红,剑眉略蹙,仿佛梦中亦难脱烦忧。景重惯见了指点江山、雄姿英发的凤艳凰,没想到会见到他那样的愁容。而景重并不因他的愁容而失望,反倒高兴能见着更完整的他。
却见凤艳凰的被子没盖严,露出了半截足。凤艳凰是个长相精致的人。脸是很容易骗人的,但这双脚倒是能告诉人,他是一个武夫。他的脚并不算是好看的,但男人不必要那么好看的脚。厚茧也好让他走远路——不过磨损了的脚趾甲可不是好的。景重心弦轻颤,垂头了半晌,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个银柄黄铜的指甲锉,又在床边坐下,将凤艳凰的双足搁到自己的大腿上,细心地为他打磨起脚甲来。
景重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只是教他悄悄欢喜。
76、
凤艳凰吃了酒睡了,半夜却醒了过来,正抬了抬脚,却似碰着了什么,便想是牧菁把衣服被子随便堆了,抬眼又见灯仍亮着,帐帘没放下,正是吃了酒的,心情又不畅,便道:“想必是牧菁那个丫头趁我醉了便躲懒,不好好收拾。明天起来看见,倒赖我发酒疯胡闹了。原是我越发纵了她!”凤艳凰本憋了一肚子气无从发泄,这下有了由头,便堆起怒容来,从床上坐起,正要喊人,却瞥见床边脚畔原是躺了个人。凤艳凰借着灯光细看,原是景重缩成一团,和衣睡在了他脚边。凤艳凰胸中的闷意顿时作流云散,怒容顿敛,双眸也散发出柔光来。
凤艳凰也不知景重怎么躺了在这儿,却道:“还好没喊人,不然倒把小公子吵醒了。”
这床倒是十足的宽敞,即使是成人也是横睡竖睡侧睡均可。凤艳凰抬头一看,床边果叠着新收的枕头被子,牧菁确实没好好收拾,适才也不算冤枉她。只是现在凤艳凰也并不在意,只扯了个长条的绣花洋枕来,一手轻轻抬起景重的头颅,便将枕头垫在他的头下,自己也靠在那枕头上,伸手去解景重的衣服。景重却醒了过来,睁眼便是凤艳凰的脸,不禁吓了一跳。才突然想起自己昨晚迷迷糊糊地歪在将军的床上睡着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就和将军睡了同一个枕头、盖了同一张被子。景重急忙坐起来,挺慌张地说:“将军!”
凤艳凰道:“怎么不喊‘大哥哥’了?”
景重愣了愣,便小声说:“嗯,大哥哥。”
凤艳凰笑道:“这样才好,平日在书房便罢,私底下也不必拘礼。”
景重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怕将军……大哥哥不高兴。”
凤艳凰也笑道:“很是、很是。来,先把外衣脱了,穿成这样睡觉也不热?”
景重忙道:“我……我怎么好睡在这儿,我还是回家吧。”
凤艳凰道:“现在什么时辰了,回什么家呢?才刚说不必拘礼,你现在倒更拘谨了。”
“这……”景重想了想,说,“那也不该睡这儿。”
凤艳凰却道:“现在却叫牧菁起来收拾客房,她可不依。且你我何须拘礼?”
“可是……”
凤艳凰故意板起脸来,道:“你再辞,我就恼了。”
景重无法,只得道:“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本该如是。”凤艳凰又伸手往景重外衣上摸去。
景重却躲着说:“我自己可以。”
凤艳凰一笑,说:“我倒偏要来。”说着,凤艳凰一把将景重推在床上。景重正吓了一跳,双手往前拒他,却被凤艳凰一下把住了他的双手,紧按在床上,又一手去摸景重的衣扣。景重脸红得番茄似的,睁着眼睛看凤艳凰,却道:“大哥哥……”凤艳凰细细地摸着他立领的扣子,又问:“这盘扣倒别致,是谁给你打的?”景重嚅嚅道:“是……是娘。”
“原来是景夫人啊,那我可得慢慢儿解了,免得弄坏了它。”凤艳凰便也慢慢儿的解开了第一个扣子,露出了一截粉白的脖子来。那原是青色的外褂,一颗颗纽子解开来,便见里头却穿着银红的夹纱衣,倒也好看。那扣子一直从脖子开到了腰间,凤艳凰解了他最后一个扣子后,便捏了一把他的腰侧。景重一缩,说道:“痒!”
凤艳凰细看了他一阵,便放开了他。景重如蒙大赦,忙坐起来,将那褂子脱了,又脱了那银红的夹纱衣,最里头是一件象牙白的小衣。凤艳凰仰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景重见他似有愁容,便歪在枕头上说:“乱皇的事,也不必再细想了……”
凤艳凰扭过头来,睁开眼睛,那目光明亮跟灯似的,半晌一笑,说:“我再不去想了。我只想眼前的。”
77、
景重便伏在枕上,好奇问道:“眼前?什么眼前的?”
凤艳凰歪着脖子看景重,又笑了,帮景重掖了掖被子,道:“眼前天冷,盖严了被子好睡觉。”
且说牧菁是个惯常侍夜的,浅眠警敏,里面有了人声动静,便醒了过来,披了外衣、穿了鞋子,从绣帘过,见里头形迹,又笑道:“是被子不够、还是枕头不够?这么大的一张床,竟挤成这样!”
景重明明无心,听了这话也脸红了。
凤艳凰坐起来,笑道:“好你个懒鬼,好好儿不收拾,倒得闲来取笑!什么时候也叫你学习学习规矩!”
牧菁笑道:“是、是、是!现都有了最贤德的景舍人了,哪用得着我这个别无是处的大丫头?我出去便是,你们慢慢儿盖着大红棉被、睡那绣花枕头——都成这个样儿了,我倒还懒得取笑呢!”说着,牧菁扭身便走。
只是被牧菁这么一说,景重自己也心虚起来,倒觉得这样确实是当得起“形迹可疑”四字了。凤艳凰倒是没理论,道:“先把灯熄了再走。”
牧菁便到床头来将灯熄了,才拿着一盏小灯出了去。这样房里都暗了下来,因天冷门窗紧锁,也漏不进明月星光,只是一味的黑暗。景重睁着眼看不着什么,便闭起眼来,然而闭了眼,神智还是清明的,一呼一吸都是凤艳凰身上暖暖的香气。这跟那天郊外,景重在凤艳凰身上闻到的香气是相似的,却又是不似的。那一天,还有鲜血的腥气,也还有树林的泥土、青草芳香,糅杂了凤艳凰的香气,倒不显得过暖过浓了。如今一室都是脉脉馨香的,凤艳凰身上这份味道,倒显得浓艳至极到了扰人心神、拂人意志的程度了。景重忙转过背去,望能离这气味远一点、是一点。
就是这样昏昏沉沉的,便也睡了。只是这么睡着,究竟不踏实。也不知是夜里什么时辰,景重又默默转醒过来,窗户仍是紧闭的,灯却亮了起来,亮堂堂的烧着,照得那张大红的棉被十分扎眼,上面绣着明丽的鸳鸯戏水,教景重没的脸红。
暖暖的气息吐在景重的耳边,凤艳凰问他:“小公子,我们做鸳鸯好不好?”
景重的脸登时红得跟这床被子一般,正是要说话,那暖暖的气息却已吐到了他的唇上,与他的气息交缠在了一块儿。景重无法抗拒这样的缠绵,身体深陷在这一床柔软舒适的被褥之中。那气息越来越烫,那缠绵越来越紧,他的心越跳越快,就似焚烧的火苗,一窜一窜的炽热,蓦然间,便爆破了,耳边震得巨响,景重挣扎着扑腾,眼睛蓦地睁开,看着洒金银红的帐顶,半天回不过神来。
景重抹了抹额上的薄汗,扭过头看,却见床边的位置空空如也,窗户也透出晨曦的微亮来。
只听见外面有人的脚步,又听见凤艳凰的声音说:“轻点儿声,小公子还睡着。”
“什么时辰了,我看他也该醒了。”牧菁便答。
景重才似被一巴掌打醒了,忽而发觉那红灯高照不过是一场春‘梦。他伸手摸向被褥,果然凉凉的湿了一片,惊得快面无人色,半晌那没颜色的脸上又羞耻得充得红彤彤的了。
此时牧菁却打了帘子进来,笑道:“我说是吧,景舍人是醒了。”
景重窝在被中,见牧菁来要伺候他起床,他忙拉紧了被子,满面通红地说:“姐姐别忙!我……我自己、自己能起来的。”
牧菁笑道:“行,我也懒怠伺候你。”
说完,牧菁就去打了洗脸水放到床头,又说:“这是将军的绢子,你照用就是了。”说完就走了。景重正是难过,又懊悔自己不该那么放松的,怎么就和将军同枕了呢?还把人家的床铺玷污了……更……更在梦中……景重越想,脸上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