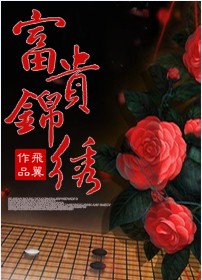一流富贵门户作者:木三观-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魏貂忙缩了头,说:“我错了。”
谢姑奶奶便笑道:“原来这也不曾要紧。确实是有几年你亲娘叫‘钟灵’,我叫‘毓秀’,本是躲难时起的诨名。当时他正是护送我们的少将军,时常叫我们‘钟灵毓秀’的,道现在也还时常喊我作谢毓秀的。还有蓝仪,那个时候也和我们一起的。”
魏貂问道:“那蓝仪那时候叫什么?”
谢姑奶奶笑道:“他们这些‘贵族’那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
魏貂更问道:“那时候说将军挨了子弹,是真的么?”
谢姑奶奶仔细想了想,便道:“这我真不知道。那个时候,将军确实是受伤躺了两天,但也没说是挨了子弹,只说是刀伤了皮肉还是怎么了的。并不说得很严重,两天就下床了,依旧骑着马。后来都说他其实是中了子弹,我听了都不敢相信。如果他真的是挨了子弹还那样子,让我竟看不到一丝破绽,也是难为的了。”
魏貂离去后,谢姑奶奶吃了茶便走了去楼外,见她的义子也来拜了。她便笑道:“来得倒是好,卫玲君、中书令都还伺候好了?”义子便道:“都好。”
谢妃往外头看了看,恰好见蓝仪从轿子下来,身边还前呼后拥的,比以前当侯爷时还气派些。谢妃看了看,笑道:“跟着他身边那是谁?”
义子便答:“母亲指的是哪一个?”
谢姑奶奶指了指,说:“就那个……长得跟景家少爷有几分相似的。”
义子说:“原是个在北洲唱戏的,叫‘双官’。”
谢姑奶奶道:“原来蓝中书这么爱听戏,随身都要带个戏子,真是好文艺。”
义子听了,也笑起来。
蓝仪特意却上了楼来见谢姑奶奶,谢姑奶奶忙敛起了戏谑的脸色,换上恭顺的笑颜,请蓝仪进屋坐着,仔细打量,却看不见那双官跟着。蓝仪坐下之后,又吃了茶,便道:“我记得在离乱之时,谢姑奶奶还是个少女,现在都当家了,确实是白驹过隙。”
谢姑奶奶便道:“大人在上,妾身哪敢当‘姑奶奶’三字?妾身倒记得蓝公当时就已经是一表人才,绝非池中物,现在一看,果不其然,已是社稷栋梁了。”
蓝仪却道:“当官的是社稷栋梁,难道商人竟然不是了?当今圣上绝非迂腐之辈,竟不讲‘重农抑商’那一套。现在京中百废待兴,正想着要提拔皇商。我看谢家就很好。要是来了,也是‘有功之臣’,圣恩也必然眷顾,门楣也当得光耀。”
谢姑奶奶当年因与父母离散,与庶出的妹妹随队避祸,怕人见财起意,因此只说自己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换名为“毓秀”,倒见识过蓝仪的孤傲。不想入了官场后,蓝仪这些官腔调调竟是一套套的,对以往最不屑的商人女眷,竟也那么客气起来。
谢姑奶奶又想,那么多的老门户都坏了,蓝家是为数不多还撑着的。家主却那么年轻,现在又荣升中书令,可见他以前虽然低调,但不代表他不厉害。这么厉害的人,又当了朝廷要员,怎么也不能得罪。因此谢姑奶奶便笑道:“其实也是,这儿本就有景洪两家同气连枝,又已老树盘根了,我也不好做。若是别的地方更广阔,我又何尝不想去呢?”
蓝仪听了,便笑道:“谢姑奶奶这么说,可见是明理的。”
谢姑奶奶便站起来,福身说:“那么谢妃就在此谢过大人指点了。”
蓝仪也站起来,说道:“谢姑奶奶何须多礼?”
二人寒暄一番,谢姑奶奶便送了他出去。那义子见蓝仪走了,便问道:“母亲真的要去京城?”谢姑奶奶扭过头,笑说:“再看看吧。”
景重正在家里躺着,却见小保姆进来,手里拿了封信,说是给景重的。景重接过了信件,见上面没有邮戳,便问道:“送信的人呢?”
小保姆便答道:“也不吃杯茶就走了。”
景重说道:“这也奇了,可说是什么人?”
小保姆摇摇头,说:“没有,只说是十分要紧的,须得是少爷自己看。”
景重便拆开了信封,拿出信来看,半晌抬起头来,对小保姆说:“将我的披风拿来,我要出门。”
82、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景重站在岸边,看着这个情景,不禁就想起这么两句诗。景是好景,不觉落了冷寂。两个穿得花红柳绿的女子提着灯笼,向景重打了个万福,引他往船上去。他离岸略远,只堪堪看见孤灯渔火和江上微微星浪,越走越近,才知道那不是十分寂寥的渔船,而是一艘精巧的画舟。
更让他意外的是,船上的人是蓝仪。
景重说道:“是你?”
蓝仪笑问:“你以为是谁?”
景重道:“不拘是谁,只是不曾想是你。”
婢女便扶景重登舟,又上来添茶,只是小船虽然精巧,到底是小,微微颠了一下,那婢女失手便将茶碗打翻到景重身上。那婢女忙吓得央告求饶,满面泪痕,景重也是一惊——惊的是婢女这般惊弓之鸟。蓝仪甚知景重,便道:“她原是伺候乐大将军的,因此比一般婢子都谨慎胆怯。”
景重愕然。
蓝仪又一笑,道:“陪我来此的仆从,全都是乐大将军的旧人。想来大将军对我真是‘宠遇优渥’。”
景重无言可对,便对那侍女说:“姑娘不必慌神,我这身衣裳也不贵重。”
婢女才止了哭啼。
蓝仪便道:“还不快伺候景公子去更衣?”
婢女便引了景重进舱内。那婢女又道:“这儿只有小厮的衣服,万望公子不要见怪。”景重笑道:“无妨。”景重将外套脱下,换上了灰色棉麻的袍子。景重好奇地问道:“是什么事?”婢女便道:“公子不必挂心,再有什么事,也烧不到这儿来。”
外头原是一群官兵,为首的便是朱长史和昭文昌。二人见蓝仪在船上,勉强行了礼,便道:“原来是中书令大人,半夜在这儿,正是好雅兴。”
蓝仪笑道:“两位半夜带着士兵搜寻,也真是辛苦了。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
朱长史便道:“启禀大人,我们发现了一个小贼,一路追捕他,却在这附近不见了,不知可否请大人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一看?”
掌船的仆从闻言便怒,说道:“大胆!中书令的船也是你们可以搜的?”
昭文昌道:“下官也只是公事公办,请大人不要为难!”
蓝仪笑了笑,说:“要惊动两位的,也想必不是‘小贼’而已。可见还是要紧的公务。只是尊卑有序,而且这船里又多女眷,要搜还是不方便的。既如此,我让管事去看一看,你们且说说,那个‘小贼’大约是什么身量、什么年岁、什么打扮的?”
朱长史便道:“那人瘦瘦的,身高与我相若,细皮白肉的,十六七左右年纪,穿的一身灰色的棉麻袍子。”
蓝仪便道:“好的,管事,你听到了,进去看看吧。”
那仆从便进去了。
其余官兵站在岸边。朱长史拉着昭文昌走远了些,又低声说道:“怎么来到这儿就不见了呢?想必是在船里。而且那个细作竟敢来偷文件,很可能就是蓝仪的人。”昭文昌道:“我何尝不是这么想?可是蓝仪毕竟是‘中书令’,咱们也不能硬搜。”朱长史沉吟半晌,说:“其实……其实我刚刚看到,那小贼长得跟景重可是十分相似啊……”昭文昌便沉默了。朱长史又说:“大人您也看得的?”昭文昌默然半晌,才说:“天色昏暗,也看不真切。况且人有相似,现在说这些也不好。”
过了半晌,那仆从便出来,说道:“没有看到可疑的人。”
昭文昌和朱长史也只好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景重才从船里出来,只对蓝仪说道:“刚刚是什么事?为何这么吵杂?”蓝仪便道:“也没什么。”
正说着,却见一队人从附近狭路突然跑出来。那昭文昌和朱长史往前走来,提灯照看,果见景重打扮与那贼人无异。昭文昌也一时错愕了。朱长史便道:“果然是你!”
景重却是云里雾里的,只道:“两位大人,这是什么缘故?”
朱长史便道:“你还狡辩!来人,还不拿下!”
蓝仪往前一站,喝道:“放肆!”
朱长史说道:“景重,你可是贵公子?怎么会穿这么不起眼的衣服?”
蓝仪便道:“刚刚侍女失手,把茶泼到了景公子身上,才换了衣服的。他来时穿的却不是这件。大人不信,我船上各仆从侍女都可作证。且景公子一直在和本官吃茶,从未离开,更谈不上什么做贼了。再说,景公子是什么人,竟要做贼?”
只是蓝仪越为景重辩护,旁人却越觉得景重身份可疑。连昭文昌也不觉起了疑心。
景重听着什么“衣服”“做贼”的,心里暗暗计算了一下,便悄将手伸向了袍子的口袋里,果然摸到了几张来历不明的纸笺,心中自然惊惶,心神既定,便抬头冷冷地看向蓝仪。蓝仪也扭过头来看他,温和的笑道:“重儿莫忧,有我在,他们不敢碰你!”
昭文昌也不觉摇头叹气,只说:“既然蓝公执意如此,我们也没办法了。”
蓝仪便道:“辛苦两位了,明天我自会带景少爷去凤将军跟前说明。”
昭文昌和朱长史也只好带队归去。
景重看着人马归去,深知自己这样呆在船上,不得不引人怀疑。但是他即使想自证清白,跟他们回去,也是不敢的,因为他口袋里就藏着“赃物”,若被发现了,纵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
蓝仪见人远去,便笑道:“重儿且坐。”
景重不禁生怒气,只道:“我何必坐?你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蓝仪问道:“何出此言?”
景重便道:“你今晚写信说什么想知道停职的因由便来这儿,不过是想引我来到,好栽赃嫁祸。”
“我可没骗你,你既然这么聪明,现在已经知道停职的因由了吧?”蓝仪一笑,说,“那‘栽赃嫁祸’我可不敢当。你被抓了吗?你的‘人’被获了?你的‘赃’被获了?”
“‘人赃并获’还不成,太理所当然了,别人反而说我哪有这么笨的,大概被冤枉了,正是这样子似是而非、暧昧不明的,才叫人疑心生暗鬼,一时都不敢信我了。蓝公的手段果然不凡!”
蓝仪沉吟半晌,便道:“手段……自然是的,我跟随乐大将军以来,总算明白为什么我之前事事都不称心,事事都不如意。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又何必在乎手段呢?手段是虚的,到手了的才是真的。”
景重听了这话,不觉跌足,惶惶半日,才抬眸道:“原是如此。所谓近朱者赤……”
蓝仪便道:“无论在哪个州哪个府,细作都是必死无疑的,而且会死得无声无息。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景重凄然笑道:“你何必转弯抹角?不过是想说,不想死就要跟随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蓝仪又柔声劝道:“这儿又有什么好呢?当个小小的舍人,哪里能施展你的才华?你跟我上京,好处是少不了的。你的家人也能沐浴圣恩,岂不更好?”
“是沐浴圣恩,还是乞求你和乐海的垂怜?”景重不觉动了怒,横眉睁目地道,“你这样步步算计于我,还指望我跟你效力?”
蓝仪也一叹,说道:“你要是不这样,你的父母也会遭到牵连的。我也是为你好。”
景重一听这话,心里闪过无数惊雷,呆了半晌,便又说:“你……没错,你心思缜密,自然还有后招,必不如此便罢……可是你算计我便罢了,为什么连我父母也不放过?你……你真的是蓝仪么?”
蓝仪便道:“到时事情闹大了,凤艳凰也保你不住……或许,他根本不会保你。”
景重冷笑道:“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他明知我是冤枉的,也不会保我?”
蓝仪道:“他是成大事者。”
这话听着尤其讽刺。景重呆了很久,才发现船已驶远了,不知去往何方。景重的心便如脚下的这片孤舟,在大江之上浮浮沉沉,不知道该去哪儿,荡来荡去,都只是颠簸罢了。
“你跟我走,带上你的家人。”
蓝仪这么说着,语气温柔,笑容美丽,像江上这溶溶的月色。
============
好意外,原来大家喜欢看小景虐cry吗?
呃呃呃,我尽力吧
83、
月很美,却也是冷的。蓝仪骨子里就有心狠和霸道,只是要被礼教所藏。自从得了乐海的教诲,他便越发恣意起来——乐海这样都称王称霸了,他那样又如何?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做得比乐海漂亮得多。现在回想,北洲的事根本就不算事!众人道他“七伤”,不过是因为他为人太好,对待妓子犹如情人,使那些小官产生了错觉。即使蓝仪远离了他们,他们仍不死心地前来长乐寻他。当时的蓝仪十分惧怕声名被污,因此见也不肯见这些“贱籍”之民,只给点钱,像处理蓝仙那位“胡郎”一样处理这些个“情郎”。
现在,蓝仪自然觉得当初确实有点小题大做了。狎妓又如何?“妓”不就是用来“狎”的么?且男风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也是风雅事。双官也来得是时候,蓝仪再不畏惧“污名”,又想这双官容貌甚好、人也乖巧,便留在了身边。
双官以前是大户人家家里养的戏子。那户人景重也听说过,原是苍萍府的邵家。与景家、洪家一样,是当地的豪门。然而,夏将军不够钱花了,且这邵家又在生意上得罪了夏将军妻子的家人,因此被抄家,那么富贵的门户就此一夜倾颓。再多的金子银子,都抵不过枪炮。这就是乱世的真实。谢家也是有了唇寒齿亡之感,才悄悄将家业迁往了长乐。景家今夜也不由得想起了这户经商致富的人家。凤艳凰虽然不是夏浮萍,但是到了必要的时候,灭掉景家也不过是一句说话的功夫。凤艳凰也许并不乐意这么做,但是当利害攸关之际,也不容人有那么多选择的余地。凤艳凰戎马多年得到了长乐,肯定是视如珍宝吧。
景重一边细想着,一边发现船已到了渡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