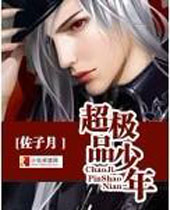十一年-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易谦平日写字都喜行书,夙涯看过一些,那些字笔锋顿挫、意蕴流畅,他就觉得很好看,不想少年皇子的楷字也工整俊逸,不若行书有流云之势,却也别有味道。
因为靠得太近了,易谦的呼吸总能触上夙涯的侧脸,像是初夏时夹杂着微热的风,不多时就教那孩子觉得有些发热,手里也开始出汗,快要握不住笔一样。
感觉到夙涯的异样,易谦停下动作,问道:“怎么了?”
夙涯摇头,扎松了的发带教几缕发丝落了下来,发尾扫了扫易谦的脸,撩得他不住打了个喷嚏,没留心手下,就按着夙涯的手下往下,结果将写了一半的字给涂出了一个墨点。
夙涯惊得想要即刻甩了笔就跑开,但身后那人偏生就是按着他不让动,看着已经写坏了的字,他只不以为意地笑了笑,道:“干脆教你画画吧,不能浪费了咱俩一块写了这么些时候的功夫。”
然后易谦照旧握住夙涯的手,三下两下地就开始在纸上添加笔画,时拖时扫,比之前带着夙涯练字的时候动作轻快飘逸许多,都教怀里那孩子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最后夙涯索性不看了,全由着易谦引着自己摆弄,他就一会儿抬眼看看半开的窗户,可以瞧见外头园子里正开着的花朵,要不就是去听听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叫得欢畅的鸟叫声,或者偷偷看上易谦两眼,看易谦专心致志的样子,心无旁骛得仿佛连他都是不存在的。
“还不错。”易谦即兴收笔,抬起手时忘了跟前还有夙涯,动作做得太快,就教那孩子顺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手中的笔飞了出去,然后啪嗒一声落在地上。
还有那个忽然被拽起来的孩子,脚下没站稳重心就朝着一边倒去,最后直接扑在了易谦怀里,将紫衣少年抱了个满怀。
易谦整个人倒在地上,一条手臂将夙涯环住,只将那小小的身子往上托,另一只手却按着夙涯的头往自己怀里靠,胸口被稍稍撞了一下,却是在瞧见夙涯满是自责的目光后将这些小疼小痛都尽数抛去了脑后。
“是我一时大意了,跟你没关系。”易谦干脆就仰躺在地上,教夙涯那样靠着,他则望着房梁,饶有兴趣道,“阿夙你看上头,梁上的花纹好不好看?”
夙涯抬眼望去,横着的房梁上果然绘着彩绘,颜色不太艳丽,但就这么看着也能看出画师精巧纯熟的画工——易谦的宅子里就有这样一些教人一旦看见就不由惊喜的东西。
“我要说那是我画的,阿夙你信不信?”易谦问道。
小脸贴着易谦胸口,这会儿还在盯着那些画出神,听见易谦的问话,他又开始迷迷糊糊的,像才睡醒一样,动了动脖子,说点头不像点头,说摇头又像在点头。
房梁上画的是初春时房间外头花园的一角,那时候夙涯也在的,但他怎么就不知道易谦将这画偷偷画去了房梁上?
就好像他自己不知道九岁那年,易谦分府第一年的冬天,少年皇子在雪地里写了什么。
易谦没有与夙涯说过那时他在雪地里写过什么,孩子只是记得因为自己一个憧憬又期待的眼神,于是易谦就带他在风雪中玩了起来。
“等一等。”易谦将兴冲冲想要出门的夙涯拦住,将孩子头上的帽子、脖子上的围脖、身上的披风都尽数检查过了,才与他一同出门。
朔风吹来,寒意扑面,夙涯还没踏出房门就吸了好大一口凉气,身体内部快要被冻结了一样,冻得他连眼睛都闭上了。
“要不还是在屋里烤炉子吧。”易谦道,口中呵出的白气即刻就被北风吹散了。
夙涯看着帝都上空飞扬的雪花,白茫茫的一片,比江南冬季交加的绵柔雨雪恣意张狂,铺天盖地的教人看着都觉得想要纵情放肆一回。
于是夙涯提了衣摆就跨步踏出门外,小跑着入了飞雪中。
“阿夙。”易谦跟上去,将已经在雪地里跑开的孩子捉住,两人的脚印在雪地里留下长长的一串痕迹,只是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新落下的雪覆盖了过去。
夙涯笑着在雪里跑来跑去,像只小麻雀似的,一会儿在原地不停地跺脚,将积雪踩得实实的,一会儿张着双臂鼓动着身上的披风,正像在飞一样,或者捧起地上的白雪朝天上撒。
其实他吃了好些雪,冰凉的雪花落入口中,就跟才从房里出来时喝了满口的寒风一样,冻得他直想打哆嗦,但这会儿太高兴了,也就顾不得了,而且要是让易谦知道的话,说不准他就要被“强行”带回屋里去对着炉子看雪了。
后背忽然被什么东西砸中,夙涯回过头才看见易谦正蹲在雪地里捏着雪球——刚才就是这个人偷袭自己呀。
“阿夙你再不动手,今天就等着被我砸成雪人吧。”
易谦的声音被吹散在风里,零零碎碎地飘入夙涯耳里。然后那孩子也矮下身在雪地里抓了一把雪,团了几下,扬手就要朝对面砸去。
但是……才要把雪球丢出去的时候,夙涯却是犹豫了,同时……鼻子上好像被什么冰冰凉凉的东西打个正着,整张脸都连带着遭了殃。
“阿夙!”易谦赶忙跑去夙涯身边,伸手拍去孩子脸上的残雪,亟亟道,“你怎么停下来了?”
怎么都不该忘记了如今是易谦养着他,再开心都不能逾越了那层规矩,他刚才要是把雪球丢出去了,万一砸中了易谦,让那人生气了怎么办?
易谦将夙涯脸上的雪擦干净了才发现孩子那张圆嘟嘟的脸这会儿已经被冻得有些发红了,他捧着看了一会儿,道:“冷不冷?”
夙涯摇头。
“我倒是觉得有些冷了,这就进屋去了,你再玩一会儿就进来,别给冻出病来。”易谦拍了拍夙涯的脑袋,这就提步离开,也没有进屋。
夙涯暗暗舒了口气,看着手里的雪球,他索性就又挖了一堆出来,开始自己堆雪人。
后来来了一些府里跟夙涯年纪相仿的侍者,孩子遇见孩子总是更要亲近一些,夙涯也觉得一个人玩着没太大的意思,于是几个人就一块儿玩。最后那个好不容易堆起来的雪人,在激烈的对战中被砸得面目全非,夙涯也酣畅淋漓地赢得了胜利。
那时的他没想到那些忽然出现的侍者是易谦叫来的,他就那样接受了那人的好意,在帝都那一年的大雪里放开了玩,笑声被不曾停歇的风吹得几乎回荡在整个园子里,就像再小些时候那样,那一年有亲人在侧,父母在堂,他玩得累了可以扑进双亲怀里,然后酣酣地睡上一觉,醒来时,能够看见母亲慈爱的眉眼。
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二)
那些侍者不过刚好也在别处玩雪,被易谦瞧见了,便叫来与夙涯一块玩耍了。
雪地里那孩子扑着身上的披风,已经被风吹红的脸上却绽放着比以往都要开怀的笑容,就好似平地亮起了光一样,看得易谦也不由会心微笑。
易谦小的时候也有这样一回,跟皇帝在皇宫的一处小院子里玩雪,不过没像夙涯这会儿如此放得开。
视线里白色弥漫,但那个跑来跑去的小小身影却依旧清晰,深色披风将他罩着,像个墨团一样,在白雪里窜来窜去。
易谦站在一旁回廊下望着跑在纷扬落雪里的夙涯,信步就踏入了雪中,顺手折了身旁树上的一节枯枝拿在手里,这就默默在雪地里写着什么。
孩子的欢笑声回荡在耳际,视线余光里依旧是那个小小身影不停蹦跶的样子,易谦右手握着枯枝,也不知这会儿是要写什么,就是凭着心意这样比划着。
那一头笑声停止的时候,易谦还沉湎在某种思绪里,全然不觉,这样写写画画一直到结束,抬头时,才见夙涯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自己跟前。
孩子立得像根木棍一样,笔直笔直的,衣上落了好些雪,脸上眉间也都是白色的雪花,但他不去拂,愣愣地站在易谦跟前,低头看着雪地里并不清晰的痕迹。
“傻站着做什么?”易谦将枯枝丢开朝夙涯伸出手——他特意换了左手,方才右手露在外头都快冻僵了,左手藏在披风下面还暖着。
夙涯如今两只手都被冻得通红,他就不好意思拿出来,在披风下面搓啊搓,犹豫着咬起了嘴唇。
易谦俯下身将夙涯抱起,吓得孩子惊呼了一声,忙伸出手环住易谦的脖子。
易谦笑着将夙涯抱进屋里,才跨进门槛,里头一阵热气迎面而来。夙涯伸手将脸上的水珠擦去,又见易谦眉宇间也沾着才化开的水珠子,便想要伸手帮易谦也擦了去。
然而怀里的孩子将动不动,一脸踌躇,视线没个落脚的地方,易谦看着忍俊不禁,稍稍将脸凑了过去。
眼见着易谦已经有所表现,夙涯便大着胆子捏了袖角往易谦脸颊上移去,然后一下一下,小心翼翼地擦着。
易谦很是享受的样子,抱着夙涯继续往屋里走,待夙涯把水珠都擦完了,他将孩子放在铺了软枕的榻上,两人挨着坐好,又开始说话。
易谦顶喜欢跟夙涯说在外头的见闻,但其实有好些夙涯都是听过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上,他见过的、听过的,比易谦还要多一些,毕竟是从小在民间长大的孩子,遇见的人、听见的事,都比只是生活在皇宫里的易谦要多上许多。
但夙涯从来不会打断易谦说话,每每就是这样安静地听着,听易谦的声音,有些低沉的声音里带着柔和,就好像小时候年轻的父亲给自己说故事那样,只是易谦说话的时候嘴角噙着的笑容不若父亲那般看来宽厚,却别有情义。
原本是易谦给夙涯抹药膏的,结果这样揉啊揉,他就将夙涯揉进了自己怀里,双臂环着夙涯,道:“阿夙,再给我点时间。”
夙涯并不明白易谦的意思,其实连易谦自己都在矛盾着,一方面希望可以早日跟夙涯一起离开帝都,彻底远离兄长们之间的争斗,一方面他又希望皇帝的身体可以好起来,不至于这样缠绵病榻,难说好坏。
手背上忽然覆来一阵温暖,易谦低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居然是夙涯的手搭去了自己手背上,但是此时夙涯已经睡着了,正歪着头靠着自己的手臂。
也不知夙涯什么时候养成的睡午觉的习惯,大概是在飞音寺里的日子比在原先宅子里还要安逸,是以夙涯如今睡的时间比过去都要多。
才将夙涯安置好了躺去床上,就有寺里的小僧过来叩门说太子易琨过来了。
易谦原本还隐约含笑的眉宇顿时收敛起所有轻松惬意,与小僧说了一声“知道了”遂回头又看了一眼还未醒来的夙涯,这就提步出去。
太子易琨这会儿就坐在当初易谦跟易筠说话的园子里,还是那方石桌,依旧是那张石凳子,只是上头坐着的人换了一个,也换了一种姿态。
“九弟。”易琨与易谦说不上亲近,自然也就不若易筠见到易谦时笑意那么明显,不过保持在适当的礼度之内就可。
“大哥。”易谦朝易琨行礼之后便坐在易琨对面,问道,“大哥怎么今日来了飞音寺?”
“陪你大嫂过来祈福的。”易琨微微哂笑着摇头,道,“妇道人家就是事情多,不过闲着也是闲着,我就一起跟来了,顺道也来看看九弟,回去好跟父皇回话。”
易谦这才记起易琨虽然早几年就成了亲但一直没有子嗣,去年年底的时候说是太子妃终于怀上了身孕,到如今也该是要临盆的时候了,无怪乎易琨要亲自陪着过来,说到底心里也是焦急又重视着的。
“大哥跟大嫂伉俪情深。”易谦这样说着恭维的话,又将话题转回到皇帝身上,问道,“父皇近来的身体可好?”
“还是老样子,说好也不好,说不好,父皇样样也都能做,就是精力接不上,隔一会儿就要歇歇。”易琨道。
“如此就要辛苦大哥了。”
“我听父皇说,你想离开帝都?”易琨将视线停落在易谦身上,审视一般将紫衣皇子从头打量了一遍,唇角笑意深深,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
“是。”易谦道,“想多出去走动走动,把以前没看的都看了,也就不枉此生了。”
“我倒没看出来兄弟几个里,你的性子居然是最野的,往常老七老八他们一个劲儿地闹,也没见说要往帝都外头跑,就你最积极。”易琨一身气度已然沉着,比易谦自然老练纯熟许多,这会儿说话的样子真有长兄如父的意思,却是连皇帝都没有这样说过易谦的。
“易谦不济,也就这点嗜好,只是如今父皇龙体未愈,我才一直留在帝都,没想自己也不中用地生了病,要来飞音寺休养斋戒,如今还劳烦大哥过来看望。”易谦一面说着一面拱手,算是感谢。
“自家兄弟不用这样客气,其实我今日过来也是有事要与九弟说的。”易琨笑色不减,只是目光渐渐锐利起来,沉沉地隐在笑意里,更有几分锋芒乍现。
“大哥但说无妨。”
“其实九弟真要离开也就是一句话的事,纵然父皇不放,九弟要走,也是没人拦得住的。只是,九弟既然出去了,万里行路,下笔有神,父皇过去教九弟做的出行手札,用意,九弟也是知道的。”
易谦已然明白易琨之意,就是要他做在民间的笔录官,有些官面上不好出手的事就教他做了。
易琨的心思比易筠更胜一筹,至少如今这样明面看着,易琨还会尊重易谦的意思,不过多加了些附带条件,不将人抓得太紧,所谓欲擒故纵。
“大哥是太看得起我了。”过去的笔录大多是庄淮做的,如今庄淮身在朝中,他也不好拖好友下水,便权当是自谦说了这句话,也不在易琨跟前提起庄淮。
“九弟就是太谦虚了,谦虚得都恨不得不出这飞音寺的大门了。”易琨笑出了声来,“不过这飞音寺确实景致甚好,无怪乎九弟养病都要过来这里,教人心旷神怡,我也巴不得要住上一段时间呢。”
“要不是兄长们在父皇身边尽心尽力,哪里有我这偷得浮生闲暇,还要感谢诸位兄长才是。”
兄弟两人这样客套来客套去,不多时,就有太子妃身边的侍女过来传话说一切都已收拾妥当,请易琨过去。
易琨这就离开,也不教易谦一起,说是琐事太多太麻烦,要易谦好好休养,早日回宫里去见见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