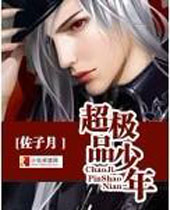十一年-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九弟。”
易谦才踏出皇帝寝宫,身后就传来易筠的声音,他便转身,正见易筠快步朝自己追来。
“五哥。”易谦拱手道。
“怎么这样生分了?”易筠忙抬手道,“九弟这是要出宫?”
“正是。”易谦回道。
“正好一起,一个人走着也无趣。”易筠不由分说就拉着易谦朝宫门走去。
“五哥是有事?”易谦虽与易筠并肩而行,却总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没事就不能寻九弟说话了?”易筠含笑,负手走在如今微热的阳光下,一身锦衣,环佩玲珑,与易谦衣着简单对比倒有些分明。
“臣弟不是这个意思。”易谦赔笑道。
“出去一趟怎么回来之后就拘谨成这样了?”易筠看来随性之至,笑道,“莫不是九弟听了旁人说了什么?”
“旁人能与臣弟说什么?无非就是听听太医们回报父皇的病情,其余的多是听不见的。”易谦微微颔首道。
“就知道九弟一片孝心,不枉父皇一向最是疼爱你。”易筠一声叹息不知意欲何为。两人就这样沉默着又走了一段,易筠忽然问道:“九弟这大半年去了哪里逍遥?”
“五哥说笑了,不过四处游走,看看各地风俗,也就是臣弟的志向了。”易谦总是显得谦逊非常。
“九弟智达高远,果真与众不同,却也是教兄弟们欣羡的。”易筠继续朝前,问道,“那九弟都看了些什么?与为兄说上一二,也好教为兄听得些帝都外的风致,就当过把瘾了。”
“五哥这是在考臣弟的功课了。”易谦垂首道。
“能考九弟的除了当年学院里的师傅,怕就只有父皇了,九弟这话说得,是成心不教我多问,要自己一个人独乐了。”易筠眼底划过一丝阴霾,却终是隐在那看来与人为善的笑意里。
“外头山川秀美瑰丽,也不是臣弟一人之言能够诉尽。”易谦回道。
易筠不过是想问他这段时日究竟去了哪里,如何遍寻不见,再由此去推算些什么,偏偏这向来中立的易谦回答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却多少也有些将自己的立场显山露水——必定是不愿与他易筠为伍了,还记恨着当年他用夙涯作要挟的事。
“对了,九弟这次是一个人回帝都的?”易筠问道。
“五哥怎么这么问?”易谦心底那根弦已然绷紧。
“之前九弟身边总是带着个孩子,这次怎么没有带回来?”易筠倒是问得开门见山。
“暂时寄养在友人家中,将来臣弟再去接。”
易筠笑而不语,望着已经能够瞧见的前方宫门,道:“当初九弟带着那小娃,是怎么都不肯分开的,如今九弟只身回来帝都,想必很是想念吧。”
易谦颔首,只当默认。
易谦几次三番被试探,听着那些各异的说辞,却是清楚这都是因为那个人人心知肚明的答案——皇帝此时病重,他自然不会就这样离开;易琨以夙涯作为要挟拖着不教他走;易筠各种揣测都往他身上安——无论他如何解释,都有个居心叵测的罪名落在他头上,谁教他这个时候回来帝都呢。
庄淮啊庄淮,如果不是当时在忘川看见的是庄淮,他大概不会这么干脆地就回来帝都。认识了这么些年的人,说到交情,究竟还剩下多少?
心里是知道庄淮不会真对夙涯下狠手的,但他不能保证易琨不做出些出人意料的事来。
“易谦?”皇帝叫着正在出神的易谦。
“什么事?”易谦回过神,忙将皇帝手中的药碗接下放去一边的木几上,又替皇帝扶了后头的软枕。
“该是朕问你怎么了。”皇帝靠上软枕,喟叹之下,再看易谦的眼神竟染了些自责,道,“易谦……”
“儿臣明白的。”易谦打断皇帝的话,微笑道,“父皇对儿臣的照拂,二十年来都是众人看在眼里的,比起诸位兄长,儿臣显然已经幸运很多。父皇有父皇的决定,儿臣不能左右,虽然儿臣也不能完全理解,但父皇的决定总不会是错的。’
“年纪大了,有些事情确实看不清了……”感叹里终究带着无可奈何——人说帝王无情,但那毕竟是亲生骨血,手心手背,都是肉。
“父皇心里不忍心,只是五哥到现在似乎都没有明白。”易谦道。
“他再不明白,朕也没多少时间给他了。”皇帝苦笑道。
“父皇?”
皇帝与立侍在侧的大太监周维道:“传宁相进宫。”
“父皇是要……”
还带着病容的皇帝此时却神色宽和,看着惊诧的易谦道:“朕知道的,远比他们以为的多。”
易谦默然。
“易谦,扶朕起来。”皇帝一面说着,一面就要从床上下来
易谦忙上前搀扶,关心道:“父皇小心。”
“朕……总算还有你这样一个儿子。”皇帝笑看着身边始终谦和的易谦,眼底笑意蓦地就欣然宽慰起来。
这些事心里明白就好(三)
宁谨铭进入御书房的时候,易谦正陪在皇帝身边。
当朝天子,病容斑斑,枯瘦着身子坐在那把宽阔的龙椅上,瞧见这丞相进来的时候,他便不由微笑,道:“宁相来迟了,让朕好等。”
宁谨铭垂首道:“微臣知罪。”
“与宁相开个玩笑,不用如此当真。”旋即皇帝将宁谨铭招来圣驾之前。
宁谨铭走近了方才发现,那张御案上铺着一纸黄绢。
“皇上……这是要……”当朝丞相即刻明白了九五之尊的意思,不由惊讶道。
“该是早些时候就写的东西了。”皇帝清咳了两声方才继续道,“宁相在朝素以刚直清正立名,今日这诏书就由宁相为朕代笔,易谦,你且听着,做个见证。”
易谦对皇帝的行为总是抱有困惑的,忽然就要立诏,御书房内还只有他们三人。
“人不用多,足够可信便好。”皇帝将东西推去宁谨铭面前,道,“有劳宁相了。”
“臣惶恐……”宁谨拱手道。他确实是被皇帝这突然一击弄得还有些失措,然而毕竟在朝日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辅相还是很快收拾了内心迷茫,提笔记录皇帝所言。
苍老的声音缓缓而来,一字一句却分外清晰,如宁谨铭落笔的肯定,丝毫没有含糊。
易谦将诏书内容一一听在耳里,眼前却仿佛时光回转,幼年时光轮回,自己还小的时候,身边这个已然龙袍在身的帝王不若这般苍老,也不是这样的病态。他的世界里还单纯得只有父皇、那时还未过世的母妃,以及待自己都还亲厚的兄长,甚至还有庄淮。
“易谦,这就是你的侍读了。”六岁的时候,易谦头一回遇见庄淮。
那时候的庄淮就跟个小老头一样,总沉着一张脸,跟所有人都欠他银子似的。
但易谦不在乎,因为只要自己高兴就好,何况,庄淮虽然闷闷的,却是个不错的同伴,什么事交给庄淮办,一定不用他操心的。
师傅布置的课业他不想做了,就拉庄淮做。
“庄淮,你帮我把东西写了吧。”小皇子笑着讨好道。
庄淮还是板着那张脸,还满是稚色的眉宇间却透着一股誓死不从的味道来。
易谦见讨好不成,便将腰间的玉佩解下来,拿在手里晃来晃去,道:“庄淮你看,这玉佩好看吗?”
庄淮虽然年纪小,却也是爱玉之人,对易谦身上这块佩可说是“觊觎”已久,如今见了易谦这架势便不由凑了上去。
但见庄淮上钩,易谦便将玉佩交到庄淮手中,看着那眉头总是跟打了结一样的小侍读捧着那块玉佩别样欣喜的神色,他便趁机道:“你要给我把东西写了,我就将这玉佩送你了。”
庄淮惊讶地看着一脸嬉笑的易谦,指尖还触着手中那块玉佩……然后,他莫名其妙地点头就答应了,并且……干净利索地把东西写完了交给易谦。
那时头一回做坏事没经验,易谦直接将庄淮写的东西交给了师傅,结果被抓了包,庄淮被他父亲痛打了一顿,十来天没进宫,那些日子可是把易谦逼疯了——皇帝罚他看书做笔录呢。
但是那样的一个人,究竟也跟着时间走远了,如今还留在身边的……这个时候,连夙涯都不在。
踏出御书房的时候,易谦暗暗叹了一声,又听见身后传来的脚步声,听见有人叫他,九殿下。
“宁相。”易谦对宁谨铭是敬佩的,同样在这场纠葛里两不相帮,他受人掣肘,但宁谨铭却安然无恙,依旧是那个周正公直的丞相,连皇帝写下传位诏书也要有宁谨铭代笔。
“九殿下一颗心,可以放下了。”宁谨铭与易谦并行在宫道上,中年丞相气韵沉沉,说话稳稳当当的,却有深不可测的意味。
“我不明白宁相的意思。”易谦疑惑道。
“九殿下以为,老臣如何能做这丞相的位置?”
易谦寻思片刻,惊觉道:“原来宁相……”
“九殿下毕竟年轻,看世不穿,对皇上的用心也没有理解得十分透彻。”
“还请宁相明示。”
“九殿下不如好好想想皇上今日为何要殿下在旁做这个见证,兴许也就明白了。”言毕,宁谨铭拱手行礼,就此退下。
诏书的内容几乎就是所有人都以为的那样,储君即位,无可厚非,但正如宁谨铭所说,为何做见证的要是他这个在朝中无权无势的九皇子?
那道诏书也没有即刻就颁布,只是当日宁谨铭与易谦同时陪在御书房的消息传了出去,又惹了些人揣测而已。
太子易琨照旧监国,朝中之事大多不必来扰了皇帝养病的清闲。还有宁谨铭,近来入宫的时间长了,与皇帝见面却多是闲聊下棋,两人不似一国帝相,倒更像是颐养天年之人。
宁谨铭在的时候,易谦多不逗留,那两人说话总是透着另一番味道,听着不甚舒服,他也不想多理,心底的疑窦也在这一日日看似平静的生活里慢慢被磨平——但是夙涯,依旧不知去向。
再见庄淮,已是八月底,快入秋的时节,园子里的花谢了好些,倒是几株菊花竞相绽开,尤有风韵。
紫衫沉静,比才回来帝都的时候看着稳持了不少,此时就坐在园子里,卧在榻上,身上覆着薄毯子,像是睡着。
听见脚步声靠近,易谦睁开眼,瞧见庄淮就站在自己跟前,还和过去一样的动作。
“以前,还有阿夙在的。”易谦从榻上坐起身,伸手比了一个高度,笑道,“大概也就这么高,小家伙还怯生生的,想给咱们做和事老。”
“结果被九殿下给诓了。”庄淮接口道。
易谦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抬首去看庄淮,问道:“说吧,今日劳烦庄大人过来,所为何事?”
“一物换一物。”庄淮回道。
易谦霍然从榻上站起,那一记动作太快,先前庄淮又走得近,这会儿没留神,硬是被惊得连连退了两步才站稳了身形。
“阿夙在哪里?”易谦质问道。
“那日在御书房,皇上找宁相做什么?”庄淮并不避开易谦此时略带薄怒的目光,即使那眼神比过去锋锐许多,他却心如铁石一般毫无所惧。
易谦转过身道:“不如直接去问宁相。”
“那九殿下就只好自己去问阿夙的下落了。”庄淮冷冷转身。
“庄淮!”那一指急怒攻心,然而当看着旧年知交顿住身形,心里头那些诘责忽然一个字都说不出口。他终究是没有那样决绝的勇气,即使庄淮如今这样对他,那些情谊他却是不能就这样抛开的。
“殿下改主意了?”庄淮对方才易谦的斥声仿若未觉,转身再面对易谦时还是来时沉郁的靛色衣衫。
“你随我进来。”易谦拂袖去了书房。
庄淮就跟在易谦身后,看那紫衣前行,全然没有当年的轻松惬意,那背影肩头似扛着什么,脚步也沉重了。
书房还是过去的样子,庄淮踏入的时候就忽然有种时光扑面而来的感受,有些过去陈旧的气息萦绕在周围,将那一年彼此还谈笑风生的画面拉了回来,就是那些,都已泛黄。
易谦速速写了张字条交与庄淮,道:“回去交给大哥,他自然就明白了。”
庄淮将字条收起,道:“不日就将阿夙的消息传达,九殿下放心。”
若是过去,他自然放一百二十个心,但面对如今眼前这个庄淮,他如何放得下心。
见易谦仍有顾虑,庄淮从袖中取出一件用帕子裹着的东西交给易谦。
本能里仿佛已经知晓庄淮手里的是什么东西,易谦伸手时还有些犹豫,然而看着故友掌心的帕子,他还是夺了过来,思量之后打开,果真就看见那块残了角的玉佩。
“这……”易谦怒目相向,质问道,“阿夙究竟在哪里!”
夙涯不会轻易就让这块玉佩离身的,如今这佩居然出现在庄淮手中,夙涯那里究竟是要发生怎样的状况。
“大哥究竟是要怎样!”易谦终于克制不住箭步上前揪起庄淮衣襟,怒意烧在眼底,再不顾往日情分,低吼道,“阿夙根本就是无辜的,当年大哥自己做的事,连父皇如今都不去追究,他何须苦苦相逼!”
“太子当年做过什么我不知道,只是事情一日没有最终定论,一日就不能彻底放心。”庄淮看得见易谦眉间仿佛可以烧尽一切的怒火,教这平日看来温善亲和的九皇子顿时变得面容狰狞。
“父皇诏书都写了,始终也没人能与他争抢什么……”
“还有五殿下……”
“五哥根本做不了什么。”
“如果我告诉九殿下,如今五殿下正在查当年的事呢?”庄淮眉峰一蹙,眼中冷光随之盛极。
“我说过,连父皇都不予追究,否则也不会写下这纸诏书……”
“太子要的,是绝对安全。”庄淮冷峻依旧。
易谦握着庄淮衣襟的手又收紧了几分,却忽然松开,直将那人推开几步,问道:“既然他要的是绝对,我如何能保证在此之后阿夙是安全的?”
抚去襟前褶皱,庄淮淡淡道:“事实上,九殿下没得选。”
平静却异常尖锐的一句说辞,再次挑起了易谦内心的愤恨,并不因易琨的行径有多不留余地,仅仅是庄淮,在这样的时候无异于趁火打劫、雪上加霜。
“怎么说都是手足兄弟……”
“五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