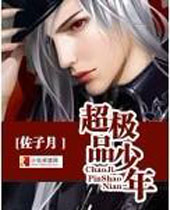十一年-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莫名其妙就死了,如果对齐贤有愧,那自己家那只腮鼠死了,他是真悔到心底去了——那是易谦送他的呀,两个人在街边挑了好久。
“其实这样也没有不好的。”易谦轻抚着夙涯的肩,已然低下目光去看正靠在自己怀中的少年。
“九哥哥?”不明白易谦的意思,夙涯只想抬头问个清楚,然而此时此刻,他方才发现,原来被自己抱在怀里的那只木箱子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而自己就这样被易谦抱住,自己的额头已然触了那人的下巴……
“嗯?”易谦就跟喝醉了似的应了一声,没有要松开夙涯的意思,就是那样轻柔地用下巴蹭着夙涯的额,两只手越抱越紧,越紧了就越抱。
“九哥哥……”夙涯发现自己基本已经动弹不得了,便索性乖乖这样靠着易谦,问道,“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
“自从把那只腮鼠带回来之后,你的眼里就只有那个小家伙了。”易谦叹道。
这话莫名就像是丢了颗小石子到夙涯的心池里,噗通一声,激起了涟漪,一圈一圈的,弯起的弧度就像笑脸一样,从心里一直爬上夙涯的嘴角。
“小家伙笑什么?”易谦将头埋得更低,这会儿鼻尖就抵着夙涯的鼻尖,挨近了其实根本看不清那少年此时的神色模样,但这些早都在心里了,不重要了。
“我不小了。”夙涯必须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他确实不小了,看连阿碧都嫁了人,他已经到了可以娶媳妇的年纪了。
易谦咯咯地笑出了声,忽然就凑近过去轻咬住了夙涯的唇,恶意咬着不放,也不教那人躲开,等觉得够了才松开,又将夙涯搂在怀里,道:“你啊,就是当初我在迎城遇见的那个小娃娃,凭你这会儿几岁了,也始终都是我的小阿夙,改不掉的。”
“叫阿夙不是挺好的吗,做什么非要加个小字?”夙涯不满道。
易谦看着夙涯,道:“你不喜欢啊?不喜欢今晚咱不灭灯了。”
“灭!”夙涯忙道,瞧见那人一脸奸计得逞的坏笑,他便知道自己又着了易谦的道,不知怎么七拐八弯的就给带了进来,还自己一个劲儿地往坑里跳——谁今晚要……咳咳……的……
“我可是听见了。”易谦在摸了摸夙涯的头便站起身,心满意足地离开,一面走一面问道,“阿碧说,今晚要咱们过去吃饭。”
夙涯回头看着那只被放在地上的木头箱子,只得摇头,想起自己方才一时口快被易谦给忽悠了,就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小腮鼠窝在木屑堆里不出来了——咦,为什么是“小”腮鼠?
易谦,你给人洗脑不带这么彻底的!
景如当年我亦如当年(尾声)
在迎城住了一整个冬季,开春的时候,易谦与夙涯说:“不如出去踏青如何?”
旁人踏青都是寻个青山绿水之处赏玩风光,但这紫衣客却拉着夙涯去了迎城最热闹的街市,走啊走,走到了一座桥下。
“阿夙,你可还记得这桥?”易谦望着那桥上来来往往的路人,嘴角带笑,三分追忆,道。
身旁那少年只望着春光里那座石桥,静默无语。
“阿夙,你今年多大了?”桥头站着道紫色身影,在和煦春风中负手而立,言辞间带着感叹,仿佛在说“时光如梭,竟就过了这些年”。
“十八。”身后少年白衣清秀,一双褐瞳泛着柔光却隐有坚韧之色。
“阿夙,你就不能多说两个字吗?”易谦提步,淡笑着走下青石桥。
身旁有经过的百姓,忙忙碌碌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并不曾多留意如今缓步而行的两人,一紫一白,一个看来优容淡然,一个则是悉心仔细地跟着,笑意款款,正像这春季江南沿河的绿柳多情温柔。
“十一年了呀。”易谦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冲着身后正低头跟来的少年发出这样一声带着些欢喜的感慨。
夙涯不想易谦会就这样驻足,所以一头就撞了上去,正撞上那人宽厚的胸膛。正要抽开身的时候,臂上却握来一只手,同时传来易谦爽朗的笑声。阿夙有些张皇地抬起头,恰是望见身前人睇来的一道柔和目光,黑亮的眼眸里有跟自己方才一样的柔色,一时间就教他看得痴怔了。
“阿夙?”叫起少年的名字,易谦不由伸出手,跟过去一样轻轻揉起了阿夙的头发。发丝触在指间,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这些年两人共处的时光那样,安宁和顺,就想这样长长久久地继续下去。
“九哥哥?”夙涯还有些呆呆的,全然不觉自己已经被易谦拉进了怀里。
“阿夙啊,这都过了十一年了呢,咱们又回来这里了。”易谦搂着阿夙,少年其实与他差不多高,但他喜欢就好像过去那样揽着阿夙的肩,说一些话给这个人听,也说给自己听。
“还记不记得十一年前你的样子?”易谦笑问道。
“小乞丐跟少年皇子的故事吗?”终于回过神来的阿夙挑了挑眉,眉宇间有对易谦如今这般行为的抗议,不过也是习惯了一样由他抱着,好比小时候他病了,易谦就哄着他喝药的模样一样。
喝药,这会儿都在喝的呢,各处寻的大夫,开的方子,就巴望着那药别突然出个什么状况,就想着这么跟夙涯一块儿游山玩水,执子之手,相携到老。
“小乞丐这不是已经长大了吗?”易谦忍俊不禁,故意又去揉阿夙的头发,胡乱地揉乱了,才松开手,有些得意地看着不太高兴的少年,道:“这才有点当年的味道。”
当年……这光景一如当年,我亦如当年,只愿这岁月静好,相安无事,等下一个十一年,我们再来这初遇的桥头,拾一次轮回可好,阿夙?
十一年来的旁观者(庄淮番外)
从江南将那个叫夙涯的小娃娃带回帝都之后,庄府里就多了这么一个包子脸的客人,怯生生的不太说话,总是窝在别院里,偶尔出来也是跟在庄淮身后,小小的个子,低着头,总跟犯了错似的。
庄家的下人不知这脸圆嘟嘟跟白瓷一样的孩子究竟是从哪来的,就瞧见庄淮进进出出十回有八九回都带着出门,要不就是从宫里回来了去别院待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不见得跟这娃儿有多亲近。
其实夙涯自己心里知道,是因为如今易谦还没分府,自己进不得宫,所以才暂住在庄淮府上的。
要天天面对着那个总是板着脸跟人欠了他几百两银子一样的庄淮,夙涯心里其实顶不乐意,然而这局面也是无可奈何,谁让易谦在宫外头没个落脚的地方呢。
正在书房里盯着认识不了几行字的书本发呆,门就被人推开了。夙涯即刻从椅子上跳下来,提着衣摆就朝门口跑去,几步路的功夫,但他其实顶不想过去的——不用想都知道是庄淮过来了。
庄淮看着将头埋得低低的夙涯,从衣袖里掏出封书信递到孩子面前,道:“九殿下给你的。”
一听是易谦的书信,小孩子高兴得即刻就伸手将书信接了过去,迫不及待地打开,只是看了没几行,那两条小眉毛就全攒在一块儿了——易谦的字是好看,但是好看得他看不明白呀。
拿着书信犹豫半晌,夙涯那欲说还休的表情全落在了庄淮眼里,一张小脸涨得通红,咬着嘴唇,真跟庄淮欺负了他似的。
“拿来。”庄淮伸出手。
夙涯还有些舍不得,将书信攥在手里,生怕书信里有什么不能给庄淮看见的东西。
那人终究是没有多少耐心的,见夙涯犹豫着不动便要转身,然而身形才动,就听见身后那孩子叫住了自己:“庄……侍读……”
小家伙将书信交到庄淮手里,听那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将内容读出来,那些易谦写来有趣幽默的话在庄淮口中都变成冷冰冰的了。
“我能……写回信给九殿下吗?”听完了内容,夙涯接过信纸惴惴不安地问道。
“明日进宫前给我就是。”庄淮说完转身离去。
第二日庄淮正要进宫,就听见夙涯的声音传来,从来在他面前大气不敢出的那个孩子今日居然一路喊着跑了过来,停在他面前的时候还不停地喘气,一面还不忘将手里的信封交到他手中。
这只信封有些……厚……
后来易谦瞧见庄淮拿出那只信封的时候,不由就朗声笑了出来,跟得了宝贝似的不给庄淮看里头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其实易谦不说,庄淮从夙涯那里也能知道,那一张张纸上画的画,从最开始几乎少得可怜的字,到后来逐渐断句成文,信封也越来越薄……在那些相见机会不多的时间里,易谦就跟夙涯用这种方式交流着,直到易谦在宫外分府了,亲自过来将夙涯接过去。
时间这样过着,易谦还是那个易谦,整日看着游手好闲,不若其他皇子那样为了前程奔波,似乎这天下大事本就与他无关,谁好谁坏,也落不入他眼里,唯有那个叫夙涯的孩子,才是视线里最中心的那个点,是万事行止的基本。
但是易谦跟他不同路,庄淮需得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往昔真诚相待的那个人总不是自己需要去相辅的那一个,道不同也就不相为谋了。
偏偏易琨找上了他,当朝太子对他礼贤,并且透露出希望通过他拉拢易谦的意思。
只是如易谦那样一个人,宁愿跟夙涯一起躲去飞音寺,也不愿搅进这时局里,不管是易琨还是易筠,谁拉拢他都只当耳旁风,除非事情关系到夙涯身上,否则他大概也不大会再跨进庄府的大门了。
两个人第一次为了玉器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争执,但庄淮依旧愿意为了易谦与易琨周旋——放那人一个去处,也将夙涯那样一个无辜的孩子放了。
只是易筠逼得易琨太紧,一定要追查当年易谦生母枉死的真相,而夙涯的身份早就不是秘密。
易筠以此为要挟要易谦相助,并以此保护保护夙涯周全;而易琨则暗中下令绝杀夙涯,表面上依旧与易谦和和气气。
易谦那个心思,已是剔透了的,若不是当时易祯卧病在床,他大概早就带着夙涯离开帝都了。
然而易谦终究晚了,没料到庄淮会忽然将夙涯送走。
渡口上,那袭靛色衣衫的男子说,若他夙涯再不走,就会危及易谦的性命。说是谎话却也不是,易谦再不抽身,怕是易琨也不会再多做顾念。庄淮也会对知交视若珍宝的夙涯痛下杀手,便只有将他驱逐开易谦身边,至于生死,便听天由命吧——有时,他亦自顾不暇——至于易谦一直以为的那种情形,他且一笑置之吧,总该教那人对自己存些感谢的。
庄淮仍记得得知夙涯不见的消息之后易谦焦急得快跟发疯似的的样子,然而易祯一句话,便教他安定了下来——待我有力气走去大殿上,便给你个自由,如今,你且在朕身边待着,做些你身为易家子孙该做的事。
然后易谦就那么留下了,等易祯暂定乾坤之后,他便即刻离开帝都去寻夙涯。
那人走得那么急,带着阿碧就匆忙上路了,并未顾得上与他这个多年好友道别——那个跟在易谦身边的红裙少女,一早就被易琨盯上了,做了易琨的眼线,时刻将那紫衣皇子与夙涯的情况报告给易琨呢。
他该说什么呢?一旦面对跟夙涯有关的事就完全失去了往日分寸的易谦,确实不适合在帝都生存,但大局一日未定,易谦在忘川的自在就随时可能被收回。
庄淮可以理解易筠对当年柳太医之事念念不忘的执着,但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着实教他也不由生出好些厌烦来,因为只要易筠一有动作,易琨就会将视线重新转移到夙涯身上,对易琨而言,活着的夙涯就是一个威胁。
然而易祯保着易谦,也就同时保住了夙涯,皇位迟早是易琨的,没人抢得去。易琨不过是要易筠知难而退,等将来易琨登基了,好教易筠安安乐乐做他的王爷,也别再有旁的心思。
只是易谦终究还是又回来了帝都,因为易祯的病情,也同时被易琨逼着用夙涯的事作为联手打压易筠的筹码。
那一日见到被这种已经畸形的兄弟关系激怒的易谦,庄淮只在心里惨笑,也有着易谦去误会他的用心,反正本来他就是以此作为向易琨表忠的手段——前程与旧友,他要了前者,好教易琨放低了戒心,将来若是想暗中为易谦做些事,也方便些吧。
易琨终于如愿登基,易谦便又离开了帝都,这一回竟是连易祯都跟着走了——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易祯总要回来帝都的,那时候他定会与易谦再见的。
对有些人来说,重逢意味着新一次的离别,当后来收到易谦从忘川送来的书信之后,他便请命亲自前往,易琨与他说,教易谦带着夙涯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对旁人狠了,自家兄弟还是留些情面,但别教某些人遇见了,否则照旧不顾情谊的。
君心难测大概就是说的易琨吧,但只要这一国之君发话了,他又能做什么违抗之举呢?
这样的结果未尝不好,看着易谦跟夙涯走了,客船远行,大概这一场说乱不乱的“闹剧”也就最终收场了吧。
易谦,待你再回帝都,不知我是否还在,不过这些年的情谊,我庄淮铭记在心,不为旁的,只因你是易谦,我庄淮真心相待的第一个朋友,更是知己。
腮鼠记(易谦、阿夙小剧场)
小屋后头有个少年抱着一只木头小箱子在出神,他坐在一旁的凳子上,低头看着箱子里铺着的厚厚的一层木屑,很久都没有说话。
“阿夙?”易谦一路寻了过来,终于找着了夙涯,见少年坐着出神,他便放轻了脚步靠近过去,俯身在还没有回神的少年身旁,低低叹了一声,道,“阿夙……”
“是我一时大意了。”夙涯仍旧看着那只木箱子,咬了咬嘴唇,转过视线去看易谦的时候,满眼愧疚,道,“我忘了腮鼠好斗,不应该把齐贤家的腮鼠跟咱们的放一块儿的。”
有时候夙涯心太软,易谦看着虽然心疼但也无可奈何。他想起前两天齐贤将他的那只腮鼠托给夙涯照顾几天,结果夙涯没留心,将齐贤的那一只跟自己养着的那一只放在了一个木箱子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发现齐贤的那一只被他养的那只给活生生咬死了,尸体就躺在木箱子里,半掩在木屑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