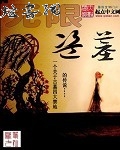[伪盗墓]蛇蜕-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好不容易倒匀了呼吸,眼角还挂着挤出来的泪水,一脸看了好大一场热闹似的表情看着我
“韩宇,你老自诩热血现充大好青年,还真信妖魔鬼怪轮回往生这些劳什子的东西?你就是你,你爹妈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风华正茂22岁。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
作者有话要说:
窝发现窝现在想不起来蛇蜕当时想写什么了。。_(:з」∠)_
☆、(四十一)结束
我被他这抽风的反应闹得愣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问道:“等等,你是说你刚才那些话都是编故事逗我玩的?”
李潇摆了摆手,“我说的没一句话是我编的,不过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奇闻异事,到底能有几毛钱是真货?反正我是一个字都不信。”
“那白景皓到底是谁?”
“还能是谁?”李潇好像觉得这个问题相当可笑,“不就是个15岁有点能耐的臭屁小鬼。”
刚刚那样一番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的描述之后,忽然又说这一切都是扯淡,未免让人太难接受。我紧皱着眉头,说道:“可你刚说的事情前后都没什么漏洞啊,不像是假的……”
“《西游记》逼真不逼真?唐僧跟孙猴一步一个坎儿,一路上各种妖魔鬼怪,各种苦难艰辛,写得都跟真事一样。你难道相信往西走十万八千里就真能见到如来佛祖?这事根据一位学者考证,孙悟空的原型可能是《三藏法师传》上记载的唐僧在西行路上遇到的年轻胡人石槃陀。神话传说这种东西,不过是古人对一些事情添油加醋的想象罢了。”
跟之前所说的白景皓的事比起来,反而是这番解释更苍白,好像是某种掩饰。我想了一会,犹豫着问:“所以呢,当年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
“这种事情谁知道?你当我是大罗神仙么?”李潇瞪了我一眼,随即又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据我猜测,金代建国之前的女真部落可能真有一个人叫蒲阳温,而且在部落里地位还不算低。他到底做了什么正史上没提过一句,不过有件事可以确定,他留下了一颗珠子,被野把式叫做鹰眼。”
他这话倒提醒了我,“所以反而这一千年中野把式前赴后继去偷鹰眼的事是真的?”
“千真万确。”李潇点头。
我眉头皱得更紧了点,“为什么?这鹰眼到底有什么神通?”
“我这么跟你说吧,蜧这玩意虽然自古就有,不过人们对它们的印象一直只是某种能纵蛇的怪物而已。包括古代神话传说中,‘蜧’的形象是掌管降雨的灵蛇,这都跟所谓的‘空间闭合’没半点关系。空间闭合是鹰眼的功能,这两个东西会联系起来,是因为当年蒲阳温建鹰王冢保存鹰眼的时候,塞了两只蜧王进去守墓。久而久之,蜧就吸收了一部分鹰眼的力量。”
“可这力量对人有什么用呢?”我对所谓的“空间闭合”唯一的印象就是白家楼下那个有进没出的地下室。别说让我拼了命要弄个能做出死循环的东西来,我真恨不得离这玩意越远越好。
之前小鬼提过一句,说鹰眼可以控制这些蛇妖,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倒是真的,至少蛇妖会被鹰眼所吸引。
“你好像以为空间闭合就是进得去出不来的死循环吧?其实对也不对。”李潇露出一个挺神秘的微笑,“白小鬼肯定跟你说过我哥的尸体六年不腐是那些蜧在作祟,其实那也是空间闭合的一种应用方法啊。”
“贮存尸体?不……如果还能贮存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好像确实很有用。”
“Bingo!不愧是大好青年,这么快就开窍了!”李潇打了个响指,夸张的语气反而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贮存东西是一方面。不过一直以来人们所想的,更多的是另一件事。你说,如果这种功能用在活人身上怎么样?”
长生不老!
我虽然没把这句话说出来,但李潇看我的表情,显然知道我已经想出了答案。
“也未必就真能长生不老,毕竟谁也没真研究过鹰眼到底能做到什么。之前去闯鹰王冢侥幸回来的人当中,确实有一些驻颜几十年的例子。”
“这样说来,倒不怪这么多人拼了命也要得到它……”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李潇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会,才又问我:“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大好青年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我想了想,说道:“我问个不该问的事……杀了李伟的人真的是张淑芳?她就这么逍遥法外,你不恨她吗?”
他好像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好一会才苦涩地笑了一下。
“我跟我哥,关系比较复杂……他比我大八岁,我才一丁点大的时候,天天追着他屁股后面到处跑。等我懂事了,他已经能跟着我爹出去打猎,总是给我带各种有趣的小玩意。那时候我觉得他特威风,比我爹还厉害无数倍。”
他低下头,沉默了半晌。
“……不过,野把式这活计也要看点天分。没有那点天分的话,再努力都没用。我12岁的时候就能打到他一直没办法搞定的东西,家里因为这样,也对我更加倚重。后来他就渐渐把生活重心放到做学问上了。不过他也憋着一股气吧,这么多年他自己无论什么事都绝不会跟我商量,坚决不让我插手。要不是我死皮赖脸隔几个月就往他家跑,估计真要老死不相往来。”
听李潇这么说,我心里一时间像打翻了五味瓶,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原本以为他是个一贯不着调的人,却没想到他也有这样的一面。
兄弟之间的感情,我可能真的永远无法理解。
他又叹了口气,勉强笑了笑,“原本干这一行过的就是目无王法的日子。行里虽然有行规,但是我爹已经去世,按我哥的想法,肯定不会希望由我给他出头。我之前警告过那女人别再搞鬼,看她这六年确实还挺低调,所以也就这样算了。”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用力握了一下。“抱歉……”他点了一支烟,站起身来走到一个大窗户前面仰着头望向窗外,很慢很慢地吸着。
后来的时间我俩都没再说话。
冰灯里的蜡烛在太阳西斜的时候烧完,烛火晃了几下才熄灭。外面的冰雕化得只剩下骨架,上面的浮雕已经看不出了。
没过多久小鬼从外面推门进来,还背着那个巨大的登山包,全身整整齐齐的,好像没受什么伤,只是眼神看起来非常疲惫。
他抬手扔给李潇一个挺大的玻璃瓶子,里面好像是些枯树叶一样的东西,沉声说道:“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李潇早恢复了之前玩世不恭的态度,把那罐子很宝贝地接住,连声对小鬼道谢:“我哪还敢再麻烦小爷您啊,再借我个胆子我都不敢。”估计那一罐东西就是李潇所说的某种野物身上的宝贝,不过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心情去好奇那到底是什么了。
小鬼没理他,只是把登山包往他跟前一放,径直到那冰灯前拿了鹰眼,又回过身来递到我面前。
“收好。”他淡淡地说。我愣了一下才接过来,李潇在一边意义不明地笑了几声。
小鬼好像确实累了,只朝我点了一下头就往外走去。我只能在后面默默跟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潇说开车送我跟小鬼回家,我当然是乐得搭便车的,小鬼之前一直没给他什么好脸色,竟也难得没有反对。等他从楼转角后面的停车位把车开过来,我才看到:好家伙,奥迪Q7!
……这货到底做小本生意赚了多少钱啊喂?还能给我等小老百姓一条活路不?
我忽然觉得有点欲哭无泪了。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说土豪我们做朋友么?
我跟小鬼一起坐在后面。一上车我就忍不住盯着他的眼睛往死里看,他的眼睛还是一贯有些恹恹的,看不出什么感情的波动,瞳孔在傍晚阳光的映衬下显出一种明亮的茶色,很美。
他发现了我在看他,转过头来问道:“怎么了?”
“……你的眼睛,没事吧?”我想了一下,这样问道。
李潇虽然后来说白景皓的事情只不过是无稽之谈,我心里却始终难以释怀,总觉得那些话至少不会都是假的。但要让我都相信,我却并没有勇气。
“没事。”他转回头去,过了一会又说:“放心。”
“……那就好。”他似乎以为我是在问他今天有没有受伤,我一时想不出该怎样解释,只能也转回头来望着窗外。
从那个工厂到我家开车大概只要半个小时,周末路上车不多,很快就到了。李潇在我租的公寓楼下停下的时候,小鬼正头抵在车窗上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拍了两下他的肩膀他才猛地醒过来。
他跟李潇又说了几句话。说完之后李潇转过身来,把手机递给我。
“韩宇,很高兴今天见到你。虽然我觉得你应该没什么需要用到我的地方,以防万一咱俩还是相互留个电话吧,总之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我会不会帮你不一定。”
“我非常诚恳地希望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你了。”我狠狠白了他一眼,还是在他的手机上输了我的电话号码。
作者有话要说:
☆、(四十二)崩坏
我一直看着李潇的车拐了个弯不见了,回头把钥匙递给小鬼:“你累了先上楼休息吧,我去买点吃的。”
从我家再往前走过两条马路就有一家很大的湘菜馆子,口碑很不错。我到他家点了几个招牌菜打包,又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菜才上来。回家的时候小鬼换了我之前给他准备的家居服,他因为手臂的伤没办法洗澡,但显然已经洗过头发,略有些长的黑发沾了水结成一缕一缕,被他用毛巾揉得乱糟糟的。
我把饭菜摆到餐桌上,再叫小鬼过来吃饭,这才发现他已经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他面朝沙发靠背,枕着左手臂,头向下倾斜着,湿润的碎发挡住了大半边的脸。
我走到他跟前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鬼,吃饭么?”
我没忍心大声问,他也像完全没听到似的,没有一点反应。我又对着他的后脑勺怔怔地看了一会,然后起身到卧室拿了枕头和毛毯,把枕头塞到他脑袋下面,再为他摆正手臂的位置,毛毯则放在脚下,等夜里凉了再盖。
他好像真的累了,我做这些的时候,一直都没有醒。
小鬼不起的话我也没了吃饭的兴致,随便吃了一点把其余的都直接塞进了冰箱了事。再回到客厅的时候小鬼的脸转过来一点,他皮肤非常白,跟漆黑的头发配在一起显得尤其干净,眉头却好像一直微微蹙起。
客厅只有一把双人的沙发,小鬼躺上去就占满了,我便靠着沙发在地板上坐下来,打开电视调到静音模式,找了个电影默默地看着。房间里极安静,就只有电视机微弱的电流声和我身后小鬼轻轻淡淡的呼吸声。
后来我也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在梦里,终于见到了“白景皓”。
不是我身边十五岁的小鬼,而是那个金代初年的女真勇士,鹰王冢的壁画上所画的人。
至此为止,“白景皓”这个人对我来说始终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他生于金朝建国之前的女真部落,神秘,强大,被人们所传颂。这一切听起来,与其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倒更像是某种盲目的崇拜的臆造。人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被捧上神坛的偶像,一个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有血有肉,名叫白景皓的这个人。
梦中的白景皓与那幅壁画所描绘的意气风发的样子全然不同。那时他颓然跪倒在地上,深深地弓着腰,头埋在双臂之间一动不动。我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瑟缩的脊背,心里蓦地一阵发冷。
那个样子只能让我想到一个词:悲痛欲绝。
我这一辈子说短不短22年,一直都过得极为平庸,从没经历过任何大起大落。对于一个处在这样的悲恸中的人,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李潇对我所说的白景皓和蒲阳温的那个不清不楚的故事中,似乎从头到尾,白景皓都在单方面地受到伤害和背叛。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时正常的感情是什么呢?愤怒?仇恨?或者原谅和宽恕?甚至我也想过,也许白景皓才是卑鄙险恶之人,因为对蒲阳温不忿,才编造了这些故事诋毁他的名誉。
然而我全部的想象,都没有包含这样的场景。那时的他看起来就像是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而失去了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东西,无比悲伤、懊悔、而又自责。
我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梦到超出我实际认识的事了。其中的每一次,都和白景皓有关。
我走过去绕到他的面前,想试着安慰他几句,结果话都卡在嗓子眼,怎么也发不出声音。这种体验我在做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般都是把自己急个半死之后才会醒过来,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做梦。
但我很快就发现,这一次有微妙的不同。
我在梦中有很清醒的意识,身体却不受大脑的控制。就像在看一场第一视角的电影,我虽然置身于故事的场景中,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局外人。
如果我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了这段记忆,看到了白景皓,那我所借用的这具躯体就是——
此刻我对自己的好奇甚至大过了对面前的白景皓。我想低头研究一下自己的装束和身材的时候,这个身体竟不受我的控制自己动了起来。
那种明知道动的人并不是我却又确实是“我”的感觉特别违和。我能感觉到“我”极为缓慢地蹲下身体,望着白景皓被长发遮住的脸颊停顿了一会,像是轻轻叹了口气。
然后“我”俯身抽出了他挂在腰间的剑。
我对古代民俗完全没有研究。以我从一些武侠小说或电视剧中得到的粗略印象而言,似乎佩剑是中原汉人的风俗,北方少数民族则更多以刀作为武器。而白景皓通俗地说就是女真族的猎人,跟剑这种东西更是不搭得很。
单刃为刀,双刃为剑。那确实是一把剑。
那把剑造型很奇特,剑格只有一半,剑柄的形状也很不完整,虽然材质是某种金属,外形却像是古树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