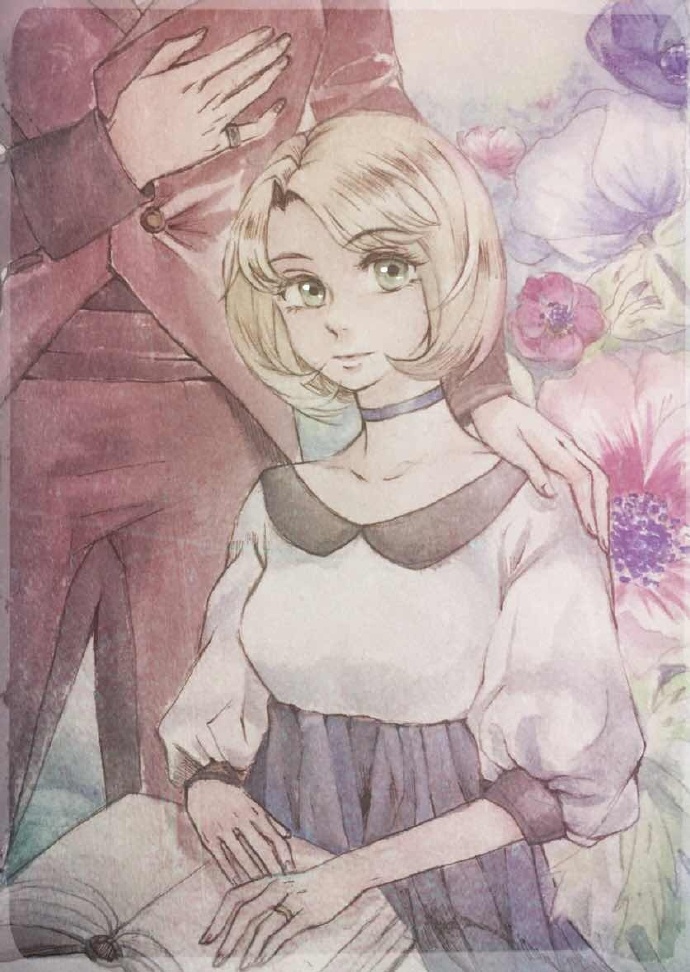(aph苏露苏)炽血之心-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话,也期待您上司考虑的结果。告辞了。”说罢起身打算离开。
阿尔弗雷德在他身后握紧了放在膝盖上的拳头。
“为什么会这样?”他站起来,垂头看着地面,眼神被眉骨投下的阴影挡住看不清晰,“俄罗斯……你什么时候起真把自己当成他的加盟共和国了?你明明是个帝国,明明实行了上百年和我们一样的制度,怎么可能几十年就……!”
伊万有些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现在的客观事实是我是苏维埃的联盟主体,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阿尔弗雷德重重地一拳打在桌面上。“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他的政权基地,他的原料库,他的工厂,他领土的主要部分——我只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一条心了?明明你和他该是意见相左的!明明是他夺取了你的地位,你该是想杀了他的!可是现在竟然轮到你为了扞卫他的利益、给他圆场而来跟我谈判……果然只是因为国家利益相同吗……”说话的时候阿尔弗雷德想起伊万曾经拒绝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国家利益不同,因此这话的末尾不自觉染上了浓浓的挫败情绪,让人没法无视。
“……您为什么要如此在意这种事呢。”伊万的话里含着隐约的叹息。
世界的HERO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因为你对我来说……很重要啊。”
※
飞机在莫斯科落地的时候,伊万没想到保尔还会来接他。两个人的关系因为这件事已经彻底闹僵了,甚至连像以往那样表面上修复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当初伊万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就想,大概以后保尔再也听不进去他的任何劝告了,那自己就尽己所能帮他这最后一次吧。可是如今保尔出现在了机场,让伊万心里升起一丝微弱的希望,觉得或许事情还没有那么糟。
很遗憾他想错了。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一路保尔都没有对他露出过笑容,甚至没怎么正眼看他,只是问:“会谈取得了什么结果?”
这是伊万意料之中的情境,然而真到了眼前,他还是感到有些难过。不过他掩盖得很好:“达成了我的预期。您撤回导弹和发射系统——这是没得说的——阿尔弗雷德解除海上封锁,并且撤出土耳其,只不过是秘密的。”
保尔皱了皱眉头。“为什么我是公开撤出,他就是秘密的?”
伊万说:“他说是为了顾及他那些欧洲盟友的感受。无论如何,就最终的事实而言,您并没吃太大的亏。古巴本来就不是您的势力范围。”
保尔没说话,只是伊万能看得出来,他咬紧了牙。
隔了半晌,保尔的话音才在他耳边冷漠地响起:“您知道吗?您这一次次多管闲事的‘帮助’,特别像一个担心自己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的母亲。”
多管闲事——伊万听到这个评价时,不由觉得受到了沉重的一击。他自己最清楚,从1929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为了身边这个人。对方非但一点都不感激,反倒指责他管得太多。因为年轻的他不能理解一个活过千百年岁月的帝国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也不能理解国家意志在绝对的冷酷的理性下所做出的看似残忍的选择。他不仅不能理解,甚至忍受不了。就像喜好阳光的向日葵无法在冰天雪地生长,理想主义者无法接受现实对他信仰的一点玷污。
理想主义。他身上最珍贵、最强大而又最脆弱、最无谓的东西。
理想主义。这能够成就他,也能够毁灭他的东西。
“我只是不希望您毁掉自己。”伊万说出这话时,就确定保尔一定会再次因此而皱眉。
果然应验了。“我不会的。”年轻人倔强地说。
伊万苍白地笑了一下。我也希望您不要迎来那样的结果,因为您,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啊。
作者有话要说: 又到周末了,来更新w
同志们看文愉快w
☆、乍暖还寒
后来的捷克共和国有个人类名字,叫卡特琳娜…诺瓦克。她曾经也叫过一段时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它很长的名字,但在1993年,她和斯洛伐克和平分裂,国名改成了简短的“捷克共和国”。
1993年上任的卡特琳娜的哲学家上司曾经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卡特琳娜在21世纪的钟声敲响时,也能悠然自得地坐在百塔之城的街边长椅上,面对着曾经外国坦克最多的这条街道,对世界另一端来的客人说:布拉格相信,外力总要离开,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1'
那个时候,弥漫在欧洲上空的红雾已然消散殆尽,曾经被生生割裂的大家在温暖的阳光下重新团聚。遮天蔽日的红旗彻底成为过去,卡特琳娜也慢慢地在岁月中沉淀下了如此淡然的话音。
然而,在外国坦克冲上街道的当时,她远没有如此超脱的认识。她感受到的只有撕裂般的痛苦,和无穷无尽的恐惧。
这是一个在她还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时发生的故事。
“一潭静水总会腐坏,要想在新时代更好地活下去,我们必须要变革。”1968年初,卡特琳娜这么对上司说。国内的高层们很赞同这一论调,很快,她家里开始了全面的社会改革。
到了这个时候,菲利克斯、伊丽莎白和卡特琳娜他们纷纷认清,保尔推行的那一套过于陈旧,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他们。他们需要更个性化、更与时俱进的制度。所以卡特琳娜这次喊出的口号就是“摒弃苏联模式”和“走由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简而言之,她也想从保尔身边独立。尽管菲利克斯和伊丽莎白头破血流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仍然阻挡不了卡特琳娜一试的渴望。
势力范围内什么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保尔的眼睛,何况是卡特琳娜此番这么大的动作。他很快下了决定,任何人的反对都被他当成了耳旁风——既然她想向伊丽莎白靠拢,那就按照对付伊丽莎白的方法对付她吧。
8月20日深夜,布拉格一个机场收到苏联民航客机的紧急信号,声称机械故障,要求迫降。因为是民航,又有正当理由,虽然家里正闹着轰轰烈烈的独立,但机场也没有理由阻止对方降落。谁知降落后,走下舷梯的不是惊魂未定的旅客,而是荷枪实弹的苏军特种部队!他们乘着夜色快速占领了机场,随后一飞机一飞机的坦克、大炮、军队纷至沓来。仅仅一小时后,在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领下,军队进入了布拉格市区。
第二天清晨,苏军已然攻占了城内各重要据点,逮捕了卡特琳娜的上司。同时,50多万华约军队大军压境,将卡特琳娜所有的部队全部缴械。在保尔的压倒性优势下卡特琳娜的下场比伊丽莎白更加凄惨,她惊惶地四下环顾,却只看到围绕着自己的一张张冷漠的脸庞。
伊丽莎白,菲利克斯,基尔伯特——这些平时和她一样口口声声独立的人们,现在都哪儿去了?!
百塔之城正蓬勃着的春天,就这么被冰冷的坦克履带压碎了!
卡特琳娜被暴力镇压的消息传到王耀耳朵里时,他整个人都觉得四周寒意逼人。菲利克斯那次他可以替保尔圆场说每个党都会犯错误,伊丽莎白出事后他严肃地对保尔提出了意见警告他不要再这样做,但这次保尔分明就是明知故犯!武装干涉从一开始就不是犯错误,而是保尔认为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王耀感觉从头凉到脚。
他能三番五次地干涉东欧,难道他就不能干涉他王耀吗?伊丽莎白、卡特琳娜,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就是自己——于是,这件事之后,早已与保尔离心离德的王耀一边义愤填膺地给保尔扣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一边改变了自己的对外战略,加强边防工事,时刻准备迎战。
1969年3月初,保尔在西方各处奔走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有些措手不及的消息。当时他在伊丽莎白家,是伊万打电报到大使馆通知他的。
“边境军队和王耀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我们被击退了。”
伊万是3月14日到达远东边境的。在他来到这里之前,对这里发生了什么甚至说不上很清楚。原因很简单,自从6年前古巴事件结束以后,保尔和他的关系基本上算是决裂了。如他所料,他的任何意见再也入不了苏维埃的耳,苏维埃的一切决定也不再与他谈论,之前对卡特琳娜的镇压,就完全是保尔自己的主意。更绝的是,苏维埃这一次索性直接架空了他的权力,伊万什么都做不了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在霸权主义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无法阻拦,整个人都被阴郁的情绪笼罩了起来。
冬季的乌苏里江气温达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裸露在外的面部皮肤很快就失去了知觉。风像刀子一样吹过封冻的江面,冻住的枯枝在寒风中瑟瑟摇摆,在冰面下若隐若现的部分好像溺水人留下的枯骨。即使现在,他仍然认为这场冲突本不应该发生并且绝对不能发生,然而这都没有意义了。列昂尼德给他的命令是夺取珍宝岛,他必须无条件执行。在河的对岸,曾经好奇与欣喜的目光,如今全都在恐惧和畏缩之中掩藏。伊万不由得想起了40年代的冬季,只是当年的冰天雪地似乎都没有如今这里的冷,透过寒风,浸入骨髓,一直冷到一草一木的根上、冷到人的心里去。
第二天凌晨,苏军于珍宝岛北端发起了入侵,傍晚时苏军尚未攻下阵地,不过明天或者后天肯定能结束战斗。然后就可以离开了。伊万灌下一大口烈酒,无动于衷地感受着要将肠胃洞穿的烧灼感,毫无感情地想。
然而第三天早上,随着“砰”的一声巨响,伊万那边彻底陷入了一片混乱。任谁也没想到,在这里横行霸道了好长时间的坦克居然还会触雷,而且一炸就把最好的履带炸断了。伊万调集了一队又一队的人出发去把那辆坦克之王抢回来,然而王耀显然也看得死紧,一副母鸡护雏的架势愣是逼退了苏军的好几次进攻。伊万的心情越发恶劣,阴暗的情绪仿佛火山下搅动的岩浆,撕开大地冒着狰狞的热气,随时准备爆发。不过给保尔的电报上,还是一如既往冷静而克制的语气。
那辆T…62最后被王耀炸沉了。那天夜里,双方对峙的岛上一片死一样的寂静。伊万站在岸边,听着冰冻的风划过冰面呜咽一样的声音,眼中的远东夜色无星无月浓黑一片,看不见代表人类存在的温暖的灯火,也看不见横亘在国界之间的冰冷的刀光。他盯着一团黑暗看了一会儿,静静地阖上双眼。
可以离开了。
等他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保尔也已经回来了。他告诉对方,王耀大概已经决心离开他。保尔知道以后毫不惊讶,表现的冷漠与他初识王耀时判若两人。伊万见他没太大反应,便把自己想说的接着说了下去:“苏维埃,我打算离开莫斯科了。”
保尔听到这话时表现出的惊讶甚至比刚才还要多一些。“去哪里?为什么?”
伊万看着他微微睁大的眼睛,不由觉得这家伙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以前的影子,这多少算个慰藉。不过也不能改变什么了。“去列宁格勒,我好歹在那里待过几百年,应该能算得上我的半个故乡。至于原因……”他摇了摇头,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权力被架空的无力,无法作为的烦躁,与保尔糟糕的关系带来的郁卒,以及最主要的、他想忽视却无法忽视的——“我对您很失望。”
他非常失望地看到,曾经令他赞叹和想要保护的理想主义,被异化和扭曲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如今的这个苏维埃,和他记忆里1929年星光下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是两个样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放弃,因为一点点阻碍就撒手不干不是他的作风,他仍然希望保尔能循着正道完成他的理想,并且如果有任何的机会,他会倾尽全力帮助他。只是这也并不代表,他不会因为得不到一点回报而感到疲惫。
“我依然会关注您并且给予任何您认为我能给予的支持;”保尔眼中的吃惊和无措让一直以来浓云一样裹在他心头的阴郁心情得到了稍微的纾解,“这点将永远不变。”
在他转身离开时,保尔声音干涩地在他身后叫了一声“露西亚”,然而伊万就像没有听见一样,径直走出了他的视线。
※
伊万离开后,保尔的情绪低落了好一阵。他慢慢觉得自己做不出之前那种武断的行为了,因为他逐渐看清,那些行为留下的唯一后果就是如今的满地狼藉——和他新结下梁子的兄弟姐妹至少已经有四个,基尔伯特一直对他充满敌意,托里斯一刻不停地想着要如何离开他——他们都以为自己很秘密,其实苏维埃心知肚明。
只是从前他不觉得这是问题。他觉得无论怎么样,只要伊万支持、或者说不反对自己,他就能做任何事情。他就像一个大胆地走钢丝演员,敢于在高空做出许多危险动作却不担心生命,原因在于他知道下面有人一定会接住他。但现在这个人走了;而且——“我对您很失望”,他说。
就是这一句话让苏维埃的心情糟透了。它的杀伤力比起所有人的冷眼相待加在一起都更有效。
“……怎么办,伊琳娜,我觉得我好像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保尔的下巴搁在桌上,整个人从姿势到声音都充满了沮丧的意味。
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让伊琳娜觉得十分可怜又有些好笑,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保尔的头,后者居然奇迹般地没有表示不满;苏维埃的头发光滑柔软,更让她产生了一种安抚小动物的错觉。“没有的事,”她安慰地说,“万尼亚一直都很支持您。”
“得了吧,他肯定恨死我了。我总是跟他唱反调……不对,是他总跟我唱反调!”保尔的语气有一瞬间的愤愤不平,但接着又低落下来,“要是他能单纯地只是支持我就好了啊。”
您以为我愿意跟您针锋相对吗?保尔在心里对着假想的伊万说。我明明一点也不愿意,明明最希望获得您的支持啊!因为
![[abo]我是一个alpha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6/169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