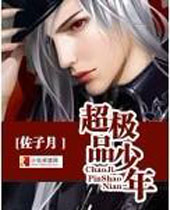莫欺少年穷 by: 廑渊-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祁薄阳对他这近乎苛责的话并不在意:“气度这种东西自然不必,但师兄业已驾鹤而去,我这个太虚道新主当要与他们打个招呼。来或是不来,只看他们,我们只管送帖便好。”
他语气极淡,穿着同当年叶抱玄一样的黑白双色衣袍,身姿如竹,玉冠束发,容色几可入画,乍一眼看去,竟与故人有五分相似。
池风歇略微有些出神,想起十年前那个少年的青涩面容,万难与眼前这个已成了太虚道新任道主的男子重叠起来。
一年前师父故去,祁薄阳接管太虚道,上下之事,有条有理,无有紊乱。
他想,果然如师父与沈岛主所料,这少年的确是最好人选,也不枉师父这些年来的尽心教导。
祁薄阳坐在椅上,骨节分明的二指有节奏地扣着身前的书案:“继任大事,自当由一宗之主亲自前来。楼沧海、笛吹云与白日迟这三人,自然会来。露清饮身子骨不佳,恐怕有些难,凝括苍会来,醒挽真与宣识色尚在两可之间。而沉醉……”
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停顿了一下,神色恍惚,似是想起了什么:“他……”
池风歇虽见了他的异色,但知他当年与沉醉相处过一段时日,有些别样情绪也是正常,并未多想,反道:“沈岛主与我太虚道的关系一向不错,继任大事,他应该不会不来。”
“不……我想他不会来。”祁薄阳垂眸。
池风歇对这结论十分惊讶:“为何?”
“五年之前,他去过一趟祚山。”祁薄阳道。
这个消息并非什么秘密,蓬莱一系虽偏向太虚道,但也算是中立,从不搅和进他们的争斗,与祚山的关系也不会太僵。
“这……与他来或是不来并无关系吧?”池风歇不解。
“呵,”祁薄阳竟然笑了一声,“他走的时候从醒挽真送来他一盆花,他现在恐怕在蓬莱岛守着那花,一眼都不愿离开吧。”
他话里听不出喜怒,池风歇想了会儿,问:“花?”
祁薄阳支颔看他,这动作似乎有些不雅,但在他身上却再自然不过:“传说三千年方开的婆罗花,世上最清净之物。”
蓬莱岛的事情,池风歇也知道一些,听了那婆罗花之事,便知道若是在婆罗花与来此之间作选,那位岛主怕是会毫不犹豫选后者。
故而他也不再多说,捧着帖子退了出去。
不过十年,竟已如隔世。
祁薄阳自嘲一笑,眼瞥见手边笔墨,不觉伸手握了笔,还未回神,便已于白纸上写下“沉醉”二字。
那两字色泽匀润,笔画转折间浑然一体,干净漂亮,墨痕犹新。
祁薄阳食指点其上,眼中似有万千情绪,最终却仍不过一声叹息。
“沉醉……”
孤灯映着他半边脸,他扯了扯嘴角:“可惜……”
蓬莱世外之地,孤悬东海,远离大荒纷扰。
偌大岛上,却只几间木屋零星,空旷辽远。
沉醉弯腰看着那盆他精心看护的婆罗花,眉头皱得死紧。
婆罗花本就是传说之物,也不知醒挽真是从哪里得来的。待得花开之日,以其为引,配以诸色灵药,当能炼得一副逆天之药,到时脱胎换骨,皆再非妄想。
只是……这花丝毫看不出要开的模样,也不知醒挽真那个“花期便在这几年”的结论是怎么来的。
蓬莱岛中典籍有记载,这花的确是真品,只是纵然是真品,这花期不定依旧是个问题。
外间海鸟掠过,发出一声清鸣。
沉醉循声望去,那只海鸟浑然不觉地梳理着羽毛,脚步轻盈地踩着沙子跳跃,昂首挺胸倒有几分意思。
蓬莱岛上只他一人,平日里也唯有这些生灵相伴,寂寞非常。
当年傅忘机说他寂寞得很,他只觉得师父未免太过做作,等自己也有了这种感觉,才明白当年师父的苦处。
心魔血誓纵然再厉害,也无法压了所有情绪。
长生的愿望愈强,其下的那颗心便越是寂寞,一日日加深,心上几乎空了一块,想尽办法也填不满。
只是师父撑不下去,不代表他也撑不下去。
沉醉盯着那盆婆罗花,原本紧蹙的眉心渐渐舒展开来。
第十八章:因缘睹蓬莱
心魔血誓……
当年他拜傅忘机为师,同他一起去太虚道探了叶抱玄,其后便回了东海。
东海的宗门并不仅有蓬莱,比邻便有一个凤凰城。
蓬莱一脉,若是究其历史,已逾千年,凤凰城与扶摇天,原本亦属蓬莱一脉。
蓬莱最初求的便是长生之道,不论因果、手段,只问长生。可惜百年来无人求得,空有余恨不去。时日久了,见得不到结果,这人心便开始浮动。
凤凰城割离的一支,多为女子,那时的城主却也是现在的城主——露清饮。她另辟蹊径,认为所谓长生,只要记忆还在,便算不死,由此创了一套转生之法。
只是万事难有两全,她寿尽之时,渡魂与新的身体,却不想那普通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她强大的精神,虽记忆不损,但自此荏弱非常,若非大事,绝不出凤凰城一步。
这转生之法所用次数越多,她身体便越是脆弱,终有一天连起身的气力也无。可这法子一旦用了,若是不想死,便不能停下。幸好凤凰城本身不弱,又和其余两宗同气连枝,还可支撑下来。
扶摇天则与普通宗门无异,取“扶摇而上九万里,欲上青天览明月”之意,最是自在逍遥,心之所向即乐事,无有及者。门中之人大多性情潇洒,行事不羁,风采斐然,信奉及时行乐,方不枉此生。
作为真正渊源的蓬莱岛,却在千年中一脉单传。而凤凰城与扶摇天虽已割离出去,但仍听命于蓬莱。只是蓬莱中人向来不管事,倒也没什么大影响。
扶摇天与凤凰城各有应对,蓬莱岛自然不可能没有什么手段,心魔血誓应运而生。
那任岛主天纵奇才,琴棋书画、医卜星相,无不精通,却穷尽一生,翻遍古籍,一无所获,心力交瘁之下,大病不起。缠绵病榻时,某日见窗外桃花压枝,色彩妍丽,心中爱极,一时只觉身有余力,竟离榻举步至窗前一观。
正因这事,他忽有所悟。
这世上最难懂的为人心,而最有潜力的也为人心。若一人可以时刻保持着最巅峰的状态,那么这世上可还有能难倒他的事。
他在一生最后的十日间,福至心灵,创了心魔血誓,交由弟子。
心魔血誓的确是一门逆天之术,以心头血为引,持立誓时最强心念,誓言不达,便一直维持着最巅峰状态。只是,创造这门秘法的人根本未想到,心魔血誓利弊相当。
当一种感情尤为强烈的时候,其它感情就显得不明显。而人心本是脆弱之物,常年维持一种状态,任谁也受不了。两者合二为一,便使得立血誓之人,于长生热衷欲狂,却对其他感情不屑一顾。
若真是如此倒也罢了,人本非无情之物,七情六欲皆是常理,哪有一情炽盛之理?需知无情与至情只一线之隔,情之一事孰人能料,哪日里情如洪流奔泻,就再难挽回。
历任岛主时日久了,也能发现这一问题,可誓言不达,血誓不解,别无他法,只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在大限之前,总有些感觉,通常趁还有余力之时收一个合心意的弟子,以作传承,如此方保得蓬莱一脉不断。
沉醉的师父傅忘机亦是如此。
他二人相遇之时,傅忘机面容不过是三十模样,青丝成雪,冷淡如冰,见他之时,心有所感,与他一话,方有今日之沉醉。
那时的傅忘机面上不显,但身心俱疲,心知自己活不了多久。后来沉醉出岛之时,他散尽功力,离了人世。
这种死法在蓬莱历代岛主中可算是好的了,就沉醉所知,历任岛主虽不过十人,但其中半数多是心碎而死,真正的心碎而死。
如此死法,怕是只有蓬莱岛之人会遇到了。
沉醉自信之处,便在于虽得不到什么真正比较,但他的长生之念却应该是历任岛主中最强的。
纵是没有心魔血誓,他对于长生的欲望也能让他入魔了。
他想长生,想得快要发疯。这世间美好之事太多,他怎能舍得百年后闭眼,再看不到呢?
所以傅忘机问他:“汝能持否?”
他回:“能。”
八年后又问他:“汝可悔?”
他笑着回说:“不悔。”
自然不悔,若是能得脱逃轮回,有何不能舍?若是不能,废尽百年也无憾。
醒挽真知他性情,特地拿了这婆罗花与他,希冀绊住他步伐,却不想这花怎么也不开。
沉醉也正为这花头痛,想起昆仑乃大荒清气汇聚之所,它处难及,其上经年雪水亦是灵气充沛,为世间难得清灵之物,若是能以昆仑之水浇灌婆罗花,不定能成。
想及不久前通过凤凰城送来的邀帖,可不就是个最好的名头?
主意既定,他打点行装,通知凤凰城。
一日后,沉醉乘船抱着婆罗花离了蓬莱,赶赴昆仑。
他算好了时间,也不急着赶路,只细心看护那盆婆罗花,见不得丝毫折枝枯叶。
这一路小心,等他到昆仑的时候,堪堪赶上了时间。
祁薄阳自叶抱玄去世时,便已接任了道主之位,此次大典,不过是公告大荒而已。
与醒挽真诸人相比,祁薄阳的年龄小得多,但他资质之佳无人能比,生生把年龄的弱势拉了回来。
虽说如此,但他的年龄仍是一大硬伤,此次继任大典,对于大悲寺与祚山而言,亦是一个试探的绝好机会。
池风歇早得了消息,与上次一样,在山脚处等候。
今日是继任大典,但原本邀请的人就不多,昆仑依旧是冷清寥落。
沉醉捧着一盆花的样子实在有些怪异,但池风歇事先便知道那必定就是传说中的婆罗花,虽说好奇,但也只是初时瞟了一眼。
与上次不同,没有祁薄阳的拖累,他们这一路走得极为轻松,只是沉醉仍得到了些许侧目。
幸好对此,他只一笑置之,并不在意。
继任之所,正是他当年与祁薄阳同去的天庭。
当年空空旷旷的白玉台上,风冷气清,正中摆了一个香案,沉醉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转眸便见了香案前的那个背对着他的身影。
无论是身形,或是衣饰,无不像极了当年的叶抱玄。
只是……不是。他想起十年前那个青葱水嫩的少年,几难想象对方会长成现在这模样。
“我来迟一步,倒是让众位好等。”沉醉抱着花,走完最后一格台阶。
他于白玉台之上扫了一圈,除了宣识色与露清饮,这大荒上的高手倒是来齐了。
二十五年前,他接任蓬莱岛主之位时,亦是如此盛况,甚至当年连宣识色与露清饮也未缺席。
祁薄阳转过身,面容年轻俊美,眉宇间一如当年叶抱玄的云淡风轻,黑白长衣掩映下,腰中悬着一把乌鞘长剑,他的视线在沉醉脸上微不可察地定了一瞬,方道:“沈岛主能来便好。”
少年当年俊俏的眉目,如今已经长开,那一双眸子更是漂亮得使沉醉不由多看了会。只是他看过便算,也不多言,直接走至众人间站定。
醒挽真看了眼他怀中的婆罗花,脸色诡异:“不想沈岛主把这花也带了来。”
沉醉未理他这话,反看向他身边的一个男子:“姚绿笙?”
这天庭之上,除他之外,全是一门之主,他出现在这里,显得十分突兀。
姚绿笙面容英俊,气度沉凝,道:“正是在下。”
“呵。”沉醉笑着向祁薄阳瞧去。
十年前祁薄阳誓要取姚绿笙与醒挽真性命,如今人在此处,他倒是十分沉得住气。
这大荒谁不知祁薄阳与姚绿笙的恩怨,沉醉那一话中的含义也是清楚明白。
楼沧海一身碧色长衫,清新俊秀,身边的凝括苍高冠博袖,身姿潇洒不群,他步至沉醉身边:“见得岛主一面实在不易啊。”
沉醉不出蓬莱,比之爱看美景的楼沧海自然难见许多。
“比不得扶摇天的逍遥啊。”他叹道。
凝括苍站在沉醉身侧,只笑不语,动作间表示了自己是蓬莱之人。
不远处站着个黑衣男子,站在这白玉台上,便如白纸上的一点墨迹,分外显眼。他五官普通,闭目靠在栏杆之上,双手抱胸不动不响,似乎对在场发生的一切都毫无所觉。
沉醉见过他一次,知道他是隐机阁的白日迟。
紧邻白日迟的是个黄衣男子,腰佩铁笛,垂眸作思考状,左手拿着一只刻满诡异符号的圆盘,右手五指在其上轻点,片刻不停,面容清秀,如文弱书生。
自沉醉说出姚绿笙这个名字后,他那本就跳跃迅速的五指动得更快了,变幻间成了一片虚影。
“哦,不知笛阁主算出了些什么?”沉醉瞧着那圆盘,笑问。
笛吹云抬眸,侧头看了祁薄阳一眼,正待说话,却被阻住:“不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