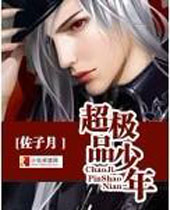莫欺少年穷 by: 廑渊-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哦,不知笛阁主算出了些什么?”沉醉瞧着那圆盘,笑问。
笛吹云抬眸,侧头看了祁薄阳一眼,正待说话,却被阻住:“不可说。”
众人望去,却是白日迟睁开眸子,死死盯住笛吹云手里的圆盘。
“不可说?”笛吹云停下手里动作,瞧向白日迟。
他与白日迟斗了多年,但对方尚是首次当面说出这样的话来。
白日迟本没表情的脸,竟然露出一个笑容:“今日在场之人,有谁是你能算出结果的?”
这话中意思,笛吹云却是明白了。
无论他算出的结果是什么,这在场之人都不会循着他的结果来做。既然如此,这算出了什么自然不可说。他与白日迟虽然斗得欢,但关系却还不错。
自说了一句话后,再未开口的祁薄阳手搭上剑柄。
在场之人俱都看向他,心知他这是要动手了。
醒挽真此次前来带着姚绿笙,不过是为了试探一下祁薄阳的深浅。
太虚道若要出手,首先对付的必是大悲寺,紧随其后的便是他祚山了。
他祚山与大悲寺关系不佳,与太虚道却也好不到哪去,他自然也要看看这新任道主的本事,再作应对。
姚绿笙早知自己性命十之八九是保不住的,却也不曾被吓破了胆。
他身担祚山明月峰峰主之职多年,自然知道何时该做什么。
祁薄阳手扶住剑柄,缓缓出鞘:“我先为人子,再为太虚道道主,世人都晓得父仇不共戴天,我自也记得。”
醒挽真不曾言语,姚绿笙却踏前一步:“当日之事,我并非凶手。”
祁楚死于油尽灯枯,他自然不是凶手。
祁薄阳轻笑一声,眉目间一扫之前的冷凝,颇见风流之姿,沉醉恍惚记得,当年那少年笑时似乎也是这模样。
他道:“我说是,便是。”
醒挽真终于出声:“继任如此重要的事情,见血可不是个好兆头。”
祁薄阳不为所动,便在这一语间,长剑已全部出鞘。
这剑虽还可以,但绝非什么名剑,只是当它被握在祁薄阳手中的时候,清华难掩。
醒挽真面容认真了些,身子隐隐挡在姚绿笙面前,覆在衣服下的身躯紧绷,随时准备动手。
天庭之上,风卷云舒,祁薄阳衣角被风扬起,长发掠过面颊,似乎见他轻叹一声,长剑也不见什么大动作,只一道冷光划过。
姚绿笙本已高估了祁薄阳,此时才发现远远不够。
他甚至未觉出杀意,便见胸口一点血印漫散开来,眼前黑夜笼罩。
醒挽真终于变色,强自忍住,许久方缓过气:“好剑法。”
在场中人也都忍不住侧目——这人的天资竟然可怖到这个地步?
若是正面对敌,祁薄阳自然不可能如此容易得手,只是谁都未料到祁薄阳动手如此狠辣。
沉醉也不由皱了眉。
他虽想过祁薄阳进步必定极大,却不曾想到过他会有如此进境。
当年他见对方资质好又年轻,前途无量,想及自己誓言无望,也曾动过杀机,只是并未动手。
如今虽然并不是不能敌,但他二人间的差距的确是小了。
祁薄阳收剑回鞘,一如之前的云淡风轻:“山主谬赞了。”
如此轻描淡写揭过前事,言行之间,他与当年那个少年早已是天壤之别。
这一桩事情就此不提,醒挽真也算是摸了底,虽有不甘,但只能暂息火气。
祁薄阳回身,祭告天地,完成继任大礼。
晚间之时,沉醉依旧抱着婆罗花,去寻祁薄阳。
进屋后他瞧见祁薄阳侧身站在窗边,其外是山巅云海,衣袍翻飞间,不染烟尘。
沉醉心中一动,见着那张冷面,想起的却是当年少年咬唇羞红的脸。
肌肤温热,腰肢柔软,当真绝佳颜色。
祁薄阳转身向他走来,步履间衣衫浮动,气质沉静。
“沉醉……”
第十九章:挥剑决浮云
祁薄阳当年唤他全名之时,屈指可数,且次次皆非正常情况。
如今他唤来,语气神态却是再自然不过,恍如二人不过是别后重逢的故友。
沉醉看着眼前与他一般高大的青年,终于明白,十年时间所能改变的真的太多。
屋内灯烛昏昏,便如十年前二人于边陲小镇独处之时,只是那个羞着脸请求不要抛下他的少年,已经不在了。
沉醉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对方唤他名字,他若是以叶道主回之,未免太客气了些。可若同回以名,又太过亲昵了……
“薄阳。”他道。
祁薄阳似乎笑了一下,伸手引他坐下,为他沏了杯茶。
沉醉将婆罗花置于一边,小小喝了口茶,想起十年前对面坐着的还是叶抱玄,而现在果然如当年对方所言,故人已逝。
“你在想些什么?”祁薄阳问。
沉醉搁了杯子,叹道:“物是人非。”
窗边如水月色映着他半边脸颊,原本稍嫌冷意的面容,显出几分温柔,眸子开阖间,却仍旧幽邃异常。
祁薄阳视线落在他面容上。
对于他们来说,时间虽然可怖,但也无法给容貌留下太多痕迹。如今十年过去,沉醉身上气息更加晦涩,显然功力又深厚许多。
他手中十指闲闲地转着空了的杯子,语气随意:“十年前,我未答应与你同去蓬莱岛,是因为……”
沉醉打断他的话:“十年前我那一问,不过是异想天开。就算你答应了,叶抱玄也不会放你与我走。既然如此,现在再说又有何意义呢?”
婆罗花肥厚的叶子泛着绿琉璃的光泽,他的目光在其上掠过,复又看向祁薄阳。
他之前所说的确不假,当年就算祁薄阳答应了,结果也不会有丝毫变化。
“虽然知道是真的,但听着可不舒服。”祁薄阳手撑着侧颊,漂亮的眸子注视着他,不放过对方脸上一丝微笑变化。
沉醉转头嗤笑:“多说无用。”
“怎会无用,”祁薄阳正身,“虽不知你当时是如何想的,但你废了两年功力之事却不假。在心魔血誓之下,尚能做到这个地步,你敢说,你不曾对我有一丝情意?”
他身子微向前倾,离沉醉的距离稍近了些。
沉醉向后靠去:“你是何身份,我又是何身份,说什么真情真意,未免可笑!”
祁薄阳伸手拿过他的杯子,放在面前:“你是蓬莱岛主。”
又将自己的杯子向前推去,与对方杯子并排:“我是太虚道道主。”
沉醉微眯了眼,看着他这一番动作,眼见两只小巧玲珑的杯子并在一处,倒有些和谐意味。
祁薄阳二指在那杯子旁轻叩:“你我身份相当,又有一夜春宵之情,实是再适合不过。”
如此厚颜之话,他偏说得淡然从容,不见丝毫窘迫,眼波流转间尽是一派风流意态。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出乎沉醉的预料。
真不知道叶抱玄到底教了些什么,竟然能让当初那个少年成了现在这无耻模样!
他看着对方那镇定面容,冷笑道:“太虚道与大悲寺之事,我蓬莱一系不会插手。所以,你不用这么急着将我俩绑在一起。”
祁薄阳似乎未料到他会如此反应,一时竟未作答,过了一会儿方出声:“你如何能说我是虚情假意?”
他眼色浓黑沉郁,透着哀切,似为沉醉无情话语所伤。
他如此模样,沉醉倒不知该说些什么,眼角瞥见手边那盆婆罗花:“此次我来昆仑,只是借你灵泉一用,之后我便回蓬莱。”
祁薄阳站起,走到那婆罗花之前,仔细观察了一番:“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婆罗花?”
沉醉不语。
祁薄阳回身拉过他的手:“灵泉借你又何妨?只是如此来去匆匆,你不觉得太过无情了吗?”
沉醉任他拉住手,也未推拒,听他这话,只道:“我有情无情,你不是清楚得很吗?”
“唉,”祁薄阳张臂抱住他,头搁在他颈侧,“我记得,你血是热的,皮肤温温的,摸着舒服极了。心跳也会乱,脸也会红,与常人别无二致,怎么可能是个无情人呢?”
沉醉暗自皱眉。祁薄阳虽然言语看着弱势,但从一开始,无论是动作或是神色,却一直处在一个极强势的位置。
这样的祁薄阳,对于他而言,实在陌生。
祁薄阳吻着他颈间嫩肉,间或道:“这十年来,你可想我?”
颈间细微的有些粘湿感,沉醉甚至能感觉到对方舌尖在他皮肤上轻巧划过,那极小的触感,到达心间之时,却成了一阵阵的酥麻。
他虽然七情淡薄,但也仍有感觉。自之前进屋时起,他见着对方如今这张长开的脸,便不由想起十年前那一夜。
一夜春宵之情……的确不假。
那时在他身下的少年,先前明明主动诱他,可到了床上的时候,却梗着脖颈一声不吭,只偶尔漏出几声轻吟,软软地便如猫叫,挠得人心上痒痒的,真想把他碾碎了吞下肚去,那他便再也跑不了了。
时至如今,他仍清楚记得少年光滑的肌肤,柔而不弱的细腰,笔直有力的长腿,还有那双泛着泪光的眼睛。
他道:“自然想。”
祁薄阳动作一顿:“你倒是……坦白。”
夜深风起,寒窗畔,他二人相拥而立,一时无话。
“我曾以为,十年可以让我忘了你。”过了许久之后,祁薄阳开口。
“可如今我却觉得我大概是猜错了,我明明知道你没有多少真情可以给我,但我却偏偏想信你一次。”
沉醉伸袖拂去桌上杯盏,哗啦啦地一片碎响,将他向后推去。
对方只看着他这动作,未有一丝相阻。
沉醉倾身以臂将他压在桌上,抬起他下巴,细细看着青年俊美的脸容。
祁薄阳面上一派平静,眼里透着些笑意。
沉醉也自一笑,再无顾忌,一手拉开对方腰间束带,低头吻上身下人的胸膛。
祁薄阳闭目拥住他,展开身体,无有抗拒,只随着他的动作,微微喘着气,值此时刻听来,分外动人。
眼见着二人身周温度愈高,祁薄阳终于忍不住在他耳边道:“……去床上。”
这桌子虽然够大,但未免太冷太硬了些。
沉醉拦腰抱起他,将他扔在床上,自伸手解了衣服。
祁薄阳撑起身子,朝他勾了勾手指。
他腰间束带本就被沉醉解了,这起身的动作更是使得那本就宽大的袍子褪了大半,当年青涩的少年躯体,如今终于成熟了。
沉醉心中一热,弹指熄了烛火,屋内顿时一片黑暗,只闻见低低的喘息声。
祁薄阳第二日醒来之时,伸手摸了摸旁边的位置,却惊觉空无一人,当时大震,起身看去,才见沉醉衣冠整齐地坐在旁边的椅上。
沉醉衣服的确整齐得很,连着头发也未乱上一分,祁薄阳身上却有些黏糊糊的,上身赤裸,吻痕密布,身后某处还有些不可言说的钝痛感。
他心下发觉有些不对。
当年他与沉醉欢好之后,对方温柔体贴,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可为何这次……
沉醉看也不看他,悠悠道:“祁道主。”
祁薄阳浑身冰冷:“你说什么?”
沉醉转头看他:“我说……祁道主。”
眼前之人面容冷淡,全无昨夜火热模样,祁薄阳怒极反笑:“若是比无情,我果然不如你!”
“无情?”沉醉笑容嘲讽:“我无情,你可真有情?”
“我……”祁薄阳欲言,却被止住。
沉醉低头,缓缓道:“当年我便与你说过,你若是想胜过醒挽真,当要寻得本心。叶抱玄教了你整整九年,以你的天资,怕是什么都学会了吧。昨日看你剑法,果然已臻至大乘,与醒挽真也可一较高下。这样的你,若说没有找到自己的本心,我却是不信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沉醉抬头,注视着他的眼睛:“我猜,你的本心与叶抱玄一样。”
“叶抱玄看着风轻云淡,全无烟火之气,实则心中执念甚重,此生大愿便是将大悲寺那群秃瓢给全捆了一起烧了,然后再扫平祚山。叶抱玄本可以撑上二十年,事实上他却只过了九年便去了。若非因为你实在合他心意,他哪里能够放心闭眼,将这偌大太虚道交与你?”
“你看,我只想求得长生,你想把这天下变成太虚道的天下。你我二人说起情之真假,莫不可笑?”
祁薄阳听了他这一席话,伸手抓了外衣披上:“真的那么可笑吗?”
“你要长生,我要太虚道站在最高处,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
沉醉道:“所以你诱我,得我蓬莱一脉助你,这事便再简单不过了。”
“这不可能,”他又道,“凤凰城与扶摇天自从当年脱了蓬莱,虽还听命于我,但也只护我一人,若是介入这大荒纷争,早与当初建宗目的相左。你这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