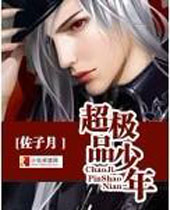莫欺少年穷 by: 廑渊-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沉醉那一幅锦绣不知是何材质所成,不仅奇长无比,且不沾火星,他三下两下,便将周边一尺内焰火俱都扑灭。只是火势太大,客店下又有助燃之物,大火不过停了片刻,便重又扑了上来。
祁薄阳小心护着婆罗花,眉头紧锁:“宣识色竟然用了火药?”
沉醉扬手,那一卷锦绣在空中完整展开,借着火光,才可见得那上面竟是绣了一幅山水水墨,从西北冰雪之地到东海孤岛,一样不缺,万里江山竟然囊括在了这一幅锦绣之中。
“你以为之前城中,尤其是这家客店,为何突然多了许多人?”他道。
祁薄阳宽袖盖在婆罗花上,以免其受到烟气熏染,闻言道:“这些我自然知道,只是……”他又说,“这山河图以极北冰蚕丝与极南火鼠毛绣成,耗费巨大,只是若非此物能避火,你身上又有避水珠,我是如何也不敢留在此处的。”
沉醉嗤笑:“便是能留下性命又如何?宣识色下大功夫引你来此,本就不为取你性命,这些日子我虽看似是在寻他,但其中关窍,你我都是知道的。我此前便问过你,如今在太虚道的究竟是何人?”
祁薄阳似有不解地反问他:“这个重要吗?”
“一直以来出现在古臧的都不是宣识色,他怕是已经带了人围了昆仑了吧。昆仑距此路途之遥,没个十天半月的根本赶不回。我倒不知你究竟留了何人在太虚道,竟然一点不曾着急。我只怕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到时候功亏一篑,太虚道千年基业毁于你手,看你如何收场!”
沉醉声色俱厉,祁薄阳却心情极好:“你这莫不是在关心我?”
眼见沉醉神色凝重,他也敛了笑意:“昆仑之上,我自有安排。此次古臧焚城,若我太虚道安然无事,只城内有一个百姓逃出去,说出了大悲寺焚城真相,到时纵然宣识色有通天手段,也难以挽回。焚城之举,宣识色实是太过冒险。”
沉醉却似不赞同:“并非太冒险,而是他等不了。此前你继任之时,昆仑一系尽数赴会,我也去了。昆仑本就势大,只可惜分支太多,近年看着似乎有整合意向,我蓬莱也是偏帮于你。待过个几年,大悲寺根本无法与太虚道抗衡。焚城之举,对于宣识色而言,是不得不为之。”
他低笑道:“当年他与我说,这大荒将乱,到时看着生灵涂炭,不知我是否心有不忍。可如今,却是他自己先动了手……世事难料,何必把话说得那么早呢,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第二十四章:云挂碧松枝
身处火海之中,四面俱是烈焰遮蔽,纵是有山河图暂时抵挡,也不知到底能支撑多久。
祁薄阳拂袖扑灭左近的焰火:“放心,此地还有我在。”
“我这山河图比你可靠多了。”沉醉道。
祁薄阳哭笑不得:“的确。”
那山河图纵横来去,山水之色愈发分明,看着灵动非常,不沾烟火,不愧是难得珍物。只是除了蓬莱之人,怕也没有人会做出这等暴殄天物之事了。
沉醉抽空问他:“你不告诉我太虚道是何人坐镇并无关系,可宣识色是否知道?天下间能正面宣识色,且不处弱势之人,除了你我之外,也唯有一个醒挽真了。莫说你找了醒挽真吧!”
“自然不是,”祁薄阳与他贴近了些,“宣识色对于何人留在昆仑,自然是知道的。只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沉醉心中敞亮:“莫非……”
昆仑积雪不化,天高气清,宣识色仍旧只着了一件单薄的雪白衣衫,赤脚踩着麻鞋,他站在风雪中向昆仑眺望时,如一座精心雕琢,却无有起伏的塑像。
他无论容貌还是身材,俱是顶尖,可眼目低垂间,气质生冷如寒石,苍白而缺失了颜色。
雪白的衣衫丝毫没有丝毫飘扬之态,如他的人一样古板而固执。
大悲寺众弟子站在他身后,缁衣却在风中猎猎作响,与宣识色的极静全然不同。
宣识色深邃如星子的眸中似乎浮现出些许遗憾:“重兆、涅仪、知微还有仲闲,竟无一人在我身边。”
他说完,僵硬的唇角竟然扯动了一下,闭目笑道:“这样……也好。”
“祁薄阳远在函川,如今这昆仑只余一个笛吹云……”他朗声道,“而笛吹云,有何可惧!”
身后弟子应声而和,面上尽是狂热之态,冷气在遇上炙热的肌肤时,被蒸腾成了一片白色雾气。
昆仑三宫之门,应声而开。
“我笛吹云虽为天机阁阁主,但也是昆仑之人。纵然不敌寺主,但也敢一试,心无所惧。”
循声望去,却是一腰佩铁笛的黄衫男子,站在阆风宫前,左手执了圆盘,另一手负于身后,临风而立。青衫的太虚道弟子在他身后连绵一片,原本的雪山霎那间成了一座青山。池风歇与霜月明侍立两边,神色平静。
他身形瘦弱,衣袂拉扯间,几欲凭风而去,可他站在离大悲寺一众百丈距离之外,全无一丝怯意。
宣识色开口,虽然二人距离稍远,但这话却丝毫不差地传了过去:“你笛吹云虽擅算天机,但天意岂能尽如人意?”
他仰头长长吐出一口浊气,身躯不见晃动,抬脚已跨前了一步。
这一步说大不大,说小也绝不小,可笛吹云见此却不由握紧了圆盘,全神贯注。
风冷雪寒,他握住圆盘的手指,白得近乎透明,却不曾松过分毫。
笛吹云外表看似文弱,但既然能够成为天机阁阁主,就代表他绝不是软弱人物。
他突然朗笑一声,伸手指着其下玄圃宫:“不知寺主可知我除了算尽天机之外,更擅阵法一道。若非如此,今日我也不会在此,不知寺主可敢一试!”
宣识色行步未有停止:“天机算数,阵道医毒,笑话罢了。笛阁主既然已经摆开了阵势,我有何不敢。”
昆仑山高三千丈,其上昆仑三宫,有石阶从山脚直达天庭,一共九千八百六十二级。
宣识色踩上第一级的时候,低垂的眼眸突然睁开,寒光凛冽:“左道!”出声如雷霆,连眼前的山风都为之一窒,撕裂了昆仑冰雪。
那一级石阶随着他这一句话轰然碎裂,成了一片石屑。
笛吹云左手小指微微颤了一下,却没有说任何话。
“左道!”
“左道!”
“左道!”
“通通都是左道!”
宣识色每走一步声音愈响,吐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如惊雷落于耳畔,脚边二丈方圆的砖石在这一话间尽数湮灭成粉,风过无痕。
笛吹云头微向前倾了一下,唇边挂了一丝血迹,低声苦笑:“果然还是不行。”
“功法、兵刃、异术,不过外物。人行于世间,身在、心在,万事足矣。”宣识色视线掠过破毁的阵法,抬头对笛吹云道。
笛吹云竟然笑了:“人生而有灵,通万物之情。山石土木,飞禽走兽,奇珍异草,或有用处,人皆可取来为己所用,此上天馈赠。我倒不知寺主,是如何有了这外物一说。为己所用,便是自己之物,将其归于外物,岂不大谬!寺主这番……是着相了。”
他的阵法造诣是大荒之首,宣识色这一路虽然看似轻松,内中杀机唯有他自知。
幻象勾心魔暗生,步步走黄泉险途。
若非宣识色于最前破了这些阵法,他身后的弟子怕是大半都能折在这里。只可惜他心智坚定,偏执成魔,诸多幻象或有勾动心绪,但不过动念间,便再无波动。
一言以蔽,这阵法对上宣识色这种心硬如铁之人,实在有些吃亏。
笛吹云早知这个道理,摆出阵法不过是为了将宣识色的心力耗去些。若以此为目的,这一路下来,倒也够了。
对方不紧不慢地拾阶而上,身后弟子亦步亦趋,周边草木砖瓦,俱为他身周翻滚气浪所摧。
他走的这一路,倒是把好好的玄圃宫毁了大半。
半个多时辰之后,他已站在了阆风宫前,与笛吹云相对而立。
“你……并非我的对手,”他看着笛吹云,视线又转过他身边的池风歇与霜月明,“太弱了。”
笛吹云搁了圆盘,脸上并无急色:“我的确并非你的对手……但……”
“加上我,寺主觉得可够?”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不可能!”宣识色难得神色惊异:“你怎么可能在这儿!你明明……”
他看过池风歇与霜月明二人,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来人跫音声起,于笛吹云身后转出。
他的嗓音殊无异处,如冰化于水,终为一体。
“你以此种手段算计我等,怎不许我们以同等报之?”来人道。
宣识色已然恢复平静:“能得你二人联手对阵,倒也不枉此行。”
那人缓步而行,身形容貌无一出众之处,偏偏他神容平静,眉目如水,气质沉凝。
笛吹云摘了腰间铁笛,叹道:“未料到有一日我会与你联手。”
白日迟不为他言语所动,只淡漠点头:“我也未料到。”
宣识色眼帘微垂:“若我没有想错,此时在隐机阁的应该是凉风生吧。”
白日迟一贯少言少语,笛吹云主动接了话:“在古臧的应该是寺主座下四贤之一的知微吧。”
话至此处,多说无益。
大悲寺弟子功夫扎实,内力比之江湖同龄之人更为深厚,而太虚道弟子剑法飘逸,身法极好。
两边弟子若是对阵,胜负只在五五之间。
笛吹云反手横笛,指尖在笛身上一弹,发出一声尖锐的颤音,直破云霄,震人耳膜。
宣识色眉头一皱,口中发出长啸,虽不及笛声刺人,却恢宏无可睥睨。
笛吹云功力不及他,眼见劲力将至眼前,身边剑吟声起,正是白日迟弹剑,堪堪破了宣识色这一招。
隐机阁当年本是从天机阁破门而出,功夫同源,比之太虚道关系还要近些。他二人虽然理念有差,但关系不算太僵,此次联手倒默契。
他们功力不如宣识色,但两两相合,也足够了。况且前边宣识色破阵一举,耗去许多心力,面上虽看不出什么异样,内里是真的虚了些。
宣识色不灭体刀剑难侵,只能以内力相逼,若是对上笛吹云与白日迟,却是鸡肋。
他二人本就不用什么刀刃,合了内力一齐攻去,不比对方弱上多少。
宣识色掌心泛着金色,身形移转间,架住二人招式。
他招式大开大合,抬手按掌,带起一阵风雪,以势压人被他做到极致。
笛吹云与白日迟力不及他,自然不愿正面迎敌,避开正面招式,只以小间挪移,耗他气力。
大悲寺与太虚道弟子早已杀成一团,剑掌相抵,时有鲜血飞溅。
池风歇与霜月明剑法高妙,胜过平常弟子许多,照此下去,太虚道的赢面要大上许多。
古臧城内,大火燃了半夜,不曾有丝毫弱势之相。
沉醉即便有山河图这等宝物在身,但内力耗费太大,面色隐隐有些发白。
身周炙热气息环绕,他额上已见了汗,唇色也淡了些许。
祁薄阳护着他那盆宝贝至极的婆罗花,见他这般模样,终忍不住将他自身后环住。
沉醉身形一顿:“你做什么?”
祁薄阳将婆罗花递回给他,自己却抽了沉醉手里的山河图。
沉醉笑道:“你该不会想帮我吧。你善于用剑,这山河图该如何用法,你可懂得?”
“我为何要懂?”
那山河图绕着二人围了几圈,严严实实地将二人裹在一起。
“这地方是小了些……沈叔叔就将就一下吧。”
岂止是小,沉醉怀中抱着婆罗花,却能明明白白感受到身后那只有一层衣衫阻隔的身体,热度肌肉弹性俱都一清二楚。
祁薄阳手紧紧环了他的腰,头搁在他肩上,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这法子其实不错,沈叔叔不会嫌弃我吧?”
山河图长度足够将二人包起来,只是一旦如此做了,身周焰火将近,没了可呼吸的空间,若是撑不过,真就等死一途了。
“若是你我一起死在这儿,倒是不错。”他又道。
沉醉嗤笑:“莫说你根本不想死,就是死也别拉着我一起。”
“沈叔叔这话真让人伤心。”祁薄阳道。
沉醉皱眉,推了推他的手:“松些,喘不过气。”
祁薄阳侧头贴上他唇,渡了一口气进去,方松了口:“这样可行?”
“多事!”沉醉说完,闭目敛了声息。
祁薄阳笑了一声,抱着他同样渐渐不见呼吸。
如此情势之下,也唯有龟息之术方能捱过。
相拥而眠,再无外物,的确不错。祁薄阳陷入沉眠时,最后想到。
浮晅大悲寺。
一顶四人抬小轿停在大悲寺门口,百千余人护在这顶轿子旁,身上气息个个悍然,显然并非凡俗。
醒挽真伸手撩开帘子,看了眼外边不见丝毫人气的大悲寺,不由笑道:“只有一个涅仪在,宣识色胆子未免大了些吧。”
他懒懒地挥了挥手,既然如